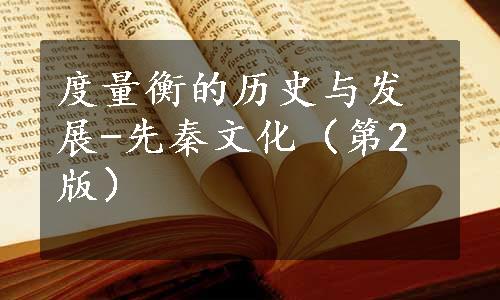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
人类对数的认识比对量的认识要早得多。在早期人类群体仅以野生植物和鸟兽鱼蚌作食物的时代,人们已感受到气温对肌体的侵蚀,而有了季节的认识和随季节迁徙的习惯,同时用数来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先民们不但学会了计数,而且逐渐地发现自然界存在着“量”。用数和单位来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计量”。中国古代,计量的称谓是“度量衡”。“度量衡”和关于年月、时日的时间计量、关于寒暑冷热的温度计量一样,是人类最早了解和应用的几个物理量。
人类大约是从天然洞穴里搬迁出来,靠自己的双手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时起,就开始进行测量活动了。原始人经历了约100多万年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从穴居山洞、构木为巢逐渐学会建造房屋,组织村落,开始了定居生活。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已密集着成百上千个母系氏族村落,半坡和姜寨遗址就是西安城郊、渭河之畔已被发掘而比较典型的古老居民区。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当时至少有居民四五百人。遗址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内排列着结构相似、大小相仿的房屋四五十间。我们测量了其中一座方形房屋的地基,每边长约1.6米。姜寨遗址的一座大房子地基,四边长约9.1米。这时期房屋多似锥形,用不同长短的树枝、树干做支柱,外面再用细碎的草和泥土抹上一层。这样,在建造房屋之前必然要考虑到每一根支柱的长短,现场不能一一找到合适的材料,人们便用手幅和肘来进行比较以帮助记忆;对于重要的长度,开始知道用棍棒来进行测量。半坡和姜寨遗址不少的房屋和建筑,都有一定的尺寸比例,这些可以证明,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已形成了早期的比较测量。
据考古发现,半坡遗址除了有许多房屋以外,还有一两百个地窖。这些地窖是氏族村民们的公共仓库,其中一个大地窖里发现堆积层达18厘米厚已腐朽了的粟。原来这些都是公社集体的储备粮,这些粮食由氏族酋长掌握,其中一部分待需要时再分期、分批地分配给大家,另一部分则准备有灾荒时作应急之用。
其实,对储备粮食的必要性,半坡村民也是经过长期积累生活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在收获的季节,氏族酋长把大家召集起来,把粮食按人数平均分配给大家。得到较多粮食之后,大家就不再愿意到外面去寻觅其他食物加以补充了。一旦这些粮食吃完,尤其是冬季来临,自然界找不到食物时,不少人因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先后死去。许多年代过去了,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能把所有的粮食分光、吃光,而应该有所储备。于是在收获的季节里,只能把一部分粮食分配给成员,其余的储备起来,平时以采集和狩猎来补充不足,待到天寒地冻,采集野果和捕捉鱼蚌十分困难时,再把集体储备的粮食分配给大家。
在过去分光、吃光的年代里,可以临时找来一件陶罐作为分配的工具和“标准器”,每人得到的粮食也能基本相等,粮食一分完,这个陶罐便失去作为标准器的作用了,下次分配时再临时找一件。然而,当人们有了储存活动之后,就要考虑到储存多少才能勉强度过寒冷的冬季,今年与去年相比,收获量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等等,这时就有保存一件相对稳定的专用测量工具的必要了。他们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把去年收获量记录下来,待第二年仍用同一个陶罐来测量,这样年复一年,终于总结出一些经验,知道应该分配多少和储存多少了。氏族酋长选择一个或几个容器,每年都用它来测量和分配粮食,这些器具便成为在一定范围内固定的专用量器。专用量器通常都保存在氏族酋长处,公社居民日常生活中似乎没有普遍使用的必要,又和大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器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什么法制性,只要大家承认它、遵守它也就行了。
在半坡陈列馆里至今还可以看到各种大小不一的陶罐、陶碗……虽然已无法确定哪一件曾作过当时容量的标准器了,但是可以设想,选择其中某一件作为分配的量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夏商周是我国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时期。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制度,夏代不但有了专门的军队,制定了刑法,而且还需要建立赋税制度。《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此外被夏朝征服和承认夏朝贡主地位的部落,大都对夏朝承担着贡纳义务。既然有贡赋,就必须对农业的收获进行量度,并且要求有统一的计量方法和统一的测量标准。收获如此,财产的划分也如此。少康逃奔有虞氏后,有虞君分给他“田一成,众一旅”。一成大约是十里见方的土地,一旅则是五百个农业奴隶。《夏书》中已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典”“则”都是法度,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由于赋税制度的需要,夏代不但有了度量衡器具,而且把度量衡器具置于王府,作为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度量衡器具的使用范围已打破了各个氏族的界限而由夏王朝统一颁发和管理。
西周是一个礼仪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即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王制,而许多制度的订立又都离不开度量衡,有了度量衡才能立信于民。《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听天下,立权度量。”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如内宰、大行人、合方氏等,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
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又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从《诗经》中可以知道,早在上古尧舜时期,周民族祖先对耕作技术就颇为擅长。至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迁徙至周原。他们来到周原后,先是开拓田畴、划分疆场,把土地分配给氏族成员去耕种,然后又兴建城廓,营造宫室,并设立各级官吏,把各部落人民分别组织到大小邑中,逐步使国家这一体制初具雏形了。周建国之后,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受到重视,被看成是天赐之圣物,在名义上属于周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土地的耕种者还是广大奴隶和农奴。为了便于管理,天子又必须把自己直接管辖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以采邑的方式分赐给大夫,大夫再以一部分转赐给家臣,这样层层领有土地的形式成为西周封建领主土地占有等级制的基础。《周礼》的篇头上往往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意思是说,周族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种土地划分的形式又可称为“井田制”,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级单位面积的名称、进位关系,组成了一个系统的专门计算田亩的计量单位制,例如一夫耕种土地一百亩(约合今28.8亩),九夫耕种九个一百亩,九百亩称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九个井为一成,面积是十里见方。从耕种一井的九夫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这种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的名称就叫夫、井、成、同,都是九进位。西周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此时丈量土地已经是比较准确地用丈尺来测量了。
西周是通过井田制来压榨和剥削奴隶的。井田制在商朝就开始施行了,至周代井田制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灌溉体系和比较准确的田亩制。对于奴隶主来说,井田制是分封赏赐和计算俸禄的依据,各诸侯国还要根据所分得田亩的多少向周天子缴纳一定的贡赋。周民族早在公刘时代已实行“彻田为粮”。田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耕种时则由一井农民在土地上“通力而作”,收获时则勿论公私都“计亩而分”。所谓计亩而分,就是把总产量依公私田亩数量的比例加以分配,这种方式,对统治阶级来说,可以防止农民耕作公田不出力的弊病,对农民来说,又可以避免把劳动时间过多地被强迫使用在公田上。这种“计亩而分”的赋税制,不仅要计算田亩,更要计算每年的收获量才能进行。《周礼》中记载:“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大意是说:天子向诸侯征收贡赋,设有专门官吏,用天子颁发的度量衡器具去收纳各种实物,而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往往发给他们相应的度量衡器,于是这些度量衡器便成了权力的象征,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权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征收赋税,因此,度量衡便成为对劳动者进行经济统治的工具。(www.zuozong.com)
春秋战国之前的度量衡,目前还很难勾画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概貌,只能根据一鳞半爪的资料说明它的产生和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器具逐渐完备。例如齐国的量器有豆、区、釜、钟,并且有法定的进位关系: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豆”原是盛肉或盛酒的用具。《考工记·梓人》:“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由于豆有一定的量,就逐渐用它作为量器的一个单位,后来演化为“斗”。“釜”是烹饪用的锅,适合于一家人的食量,所谓“因人食而制嘉量”,釜也逐渐成为量器的专用名词了。
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制造了小型衡器——木衡铜环权。目前所见的一套完整的环权系楚国遗物,全套共10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一铢重0.69克,一两为15.5克,一斤为251.3克,十枚相加约500克,为楚制二斤。这种精小的衡器是用来称量楚国“市”上流通的黄金货币“郢爱”的工具。197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金饰件,正面有精美的奔鹿和武士头像,背面都有记重刻铭,如:四两、十六朱(铢)、四分一(铢)等。这说明当时称量已相当精确。
这时期不仅广泛使用衡器,而且有了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战国时代的著作《墨子·经说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期的铜衡杆,正中有拱肩提纽和穿线孔,一面显出贯通上、下的十等分刻线,全长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每等分为一寸。形式既不同于天平衡杆,也有异于秤杆,很可能是界乎天平与杆秤之间的一种衡器,暂定名为不等臂天平。用这种衡杆称物,可以把被称物与权放在提纽两边不同位置的刻线上,即把衡杆的某一臂加长,这样,用同一个砝码就可以称出大于它一倍或几倍的重量。经过逐步发展,缩短重臂,加长力臂,就形成了秦汉以后的杆秤。
商鞅铜方升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制造了专门用来征收粮食税的禾石铜权;并且为了推行赋税制、俸禄制,消除政治、经济的割据,在“开阡陌封疆”的同时,在改革和扩大田亩制、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过程中,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规定“举足为跬,倍跬为步”、“步过六尺者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流传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方升一侧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另一侧刻“临”字,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有秦代加刻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方升据自铭容积为16.2立方寸,是先后发给“临”和“重泉”两地使用的标准量器。实测方升长、宽、高便可以计算出战国一尺长约合今23.2厘米、一升约200毫升。1964年在西安出土了一枚秦国铜权,自铭为“禾石”,经考证,秦一石为120斤,实测权重30750克,折算每斤重250.3克。从而可以确切地了解到战国(秦)度量衡三个基本单位的量值。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度量衡制度被后世所沿用,也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齐国也是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近代出土的齐国度量衡器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量器有子禾子铜釜和陈纯铜釜。它们上面都刻有铭文,以子禾子铜釜所刻铭文最详,大意是说:关口上使用的量器要以仓廪的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如果有人加大或减少它的容量,就要依法惩处。这段刻铭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度量衡管理条例,它记述了当时标准的校定和对违犯者处置的刑罚。
子禾子铜釜
此外,楚、韩、赵、魏、燕、中山等国也有一些度量衡器和刻有记述其重量、容量的各种器物,这些实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各国度量衡制度的某个侧面。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然而,在战国后期,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频繁,又有着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这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