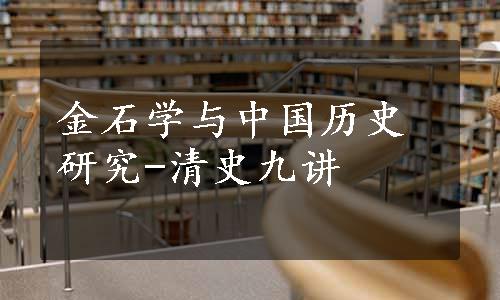
下面我们说说金石学。所谓金,是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石则指石刻碑碣的研究。我们之前提过的吴大澂就以金石学开创了小学新派。清朝最早关注金石学的是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顾炎武撰有《金石文字记》一书,主张金石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大有裨益。金石学之渊源虽然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但清代顾炎武对它尤为提倡。自此,人们开始依据铭文或碑文勘正典籍讹误,为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翁方纲热衷金石之学,对碑文逐字研究,不肯放过任何一处错误。王昶收集历代碑刻铭文,将其编篡成书。黄易遍访汉代石刻,并作拓本。阮元幕下的朱为弼、赵魏等人致力于编纂铭文。后来又有张廷济、刘喜海、张燕昌、翟云升等人出现。到近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金石之学尤其是铭文研究大有进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之前,青铜器的鉴定尚不发达。乾隆帝时著名的《西清古鉴》一书虽然水准很高,却也难免混淆真伪。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器物辨伪、铭文考证风靡一时。后来又有吴大澂和如今仍然健在的刘心源等人加入其中。我的朋友罗振玉也是金石学的名家之一。端方虽不做学问,却对青铜器兴趣颇浓,有为学者提供研究材料之功。端方是政治家,也很有学问。总之,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下边的倪模、初尚龄、鲍康、李佐贤四人都是古泉学家。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虽与经学研究没有太大关系,但古泉学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在陈介祺时大为盛行。这些人都留下了十分优秀的著作。
此外,金石学近年来又延伸出了许多分支,譬如古印学、玺印学等。玺印学经过演变,又有了封泥学。西方人在信封上封蜡;中国古代则用绳子卷好信,在绳结处用粘土压住盖上印记,称为“封泥”。由于近年来封泥大量出土,封泥研究也盛行起来。中国人起初并不认识这些出土物,后来才知道是封泥。
另外,近年兴起的还有罗振玉等人的殷墟甲骨学。中国古代经常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刻在上面的文字。这是金石学中最古老的东西,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02年我去中国时,还看到了1901年左右发现的甲骨。那些甲骨是在修铁路进行挖掘时发现的。近年来,罗振玉写了很多相关著述。甲骨学几乎成了他的独家学问。金石学延伸至甲骨学,可见其枝叶之广。而这些枝叶在学术上又各有贡献。譬如之前说到的,吴大澂研究金文开创了小学新派;再譬如随着古代器物与甲骨一同出土,礼学研究愈发盛行。总之,即使在今天,中国学问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
以上就是中国汉学的大致情形。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学派,但清朝的学问以汉学为主。整体看来,汉学历经变迁,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国势。这些学问传到日本,在日本更盛行也未可知。一切还不能断言。总之,清朝学问之繁荣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学问真正具备学术性也可谓前所未有。这是了解清朝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用了一天时间来讲。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注释】
[1]《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二十卷,作者和成书年代不详。8世纪末,全卷编纂完成,共收录四千五百余首和歌。—译者注
[2]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今文经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等。—译者注(www.zuozong.com)
[3]日本香川县旧称。—译者注
[4]疑为大西行礼(1870—?),日本政治家、实业家、藏书家,四国财界要员。—译者注
[5]日本一家专卖汉籍的书店,1861年开业,1954年关闭,在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当中颇具影响力。店主田中庆太郎(1880—1951)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广购汉籍,与中国学界联系密切。—译者注
[6]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大臣,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收藏家。著有《陶斋吉金录》等。—译者注
[7]明治中期,岩崎弥之助开始筹建收藏中日古籍的图书馆。1924年,岩崎小弥太继承父亲遗志,建成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藏书共二十万册。十二万册汉文古籍当中,尤以清末学者陆心源的五万册旧藏书有名。—译者注
[8]山井鼎(1690—1728),字君彝,号昆仑,通称善六,日本江户中期儒学家、汉学家,师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从事校勘,留下名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译者注
[9]根本武夷(1699—1764),名逊志,字伯修,号武夷山人,日本江户中期儒学家,师从荻生徂徕学古文辞,亦有志于诗文,曾校定《论语义疏》,著有《镰仓风雅集》等。—译者注
[10]皇侃(488—545),中国南北朝时期梁朝学者。梁武帝年间,任国子助教。他广泛收罗旧注,作有许多义疏,譬如《论语义疏》《礼记义疏》。—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