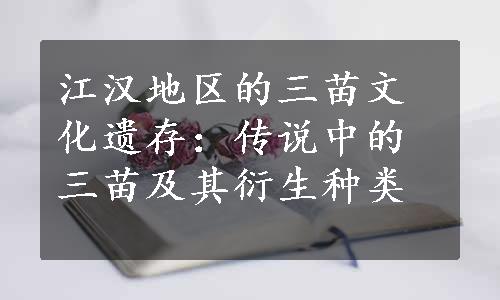
了解了楚文化产生的大致社会背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楚文化,还需要进一步追溯楚文化的源头。
楚文化诞生于江汉地区,成长于江汉地区,但它的主要的源头并不在江汉之间。旧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传说中的三苗。三苗,别称“有苗”或“苗民”,是一个庞杂的族系。三苗的“三”,恰巧象九黎的“九”,是说他们族类纷繁,部落众多。因此,三苗的文化遗存不止有一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晚的石家河文化,都有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远古的时候,江汉地区的部落流徙不定。在不同族类之间,此退彼进,是常有的事。反映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上,便是先后两种文化之间未必有内在的传袭关系。屈家岭比大溪文化要晚一些,但不能因此说大溪文化孕育了屈家岭文化,对于后来的楚文化,我们就更加没有理由说它是从石家河文化或屈家岭文化的母腹里脱胎降生的。
楚文化的主要源头,我们还是应该到楚人的先民祝融部落集团那里去寻找。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一点可以从楚国的祀典中找到确凿的证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因为鬻熊是楚君的先人,楚人又以祝融为始祖,所以楚人认为小小的夔国大逆不道,就举兵攻灭了夔国。由此可以想来,祝融在楚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记载说,高辛的火正是祝融。高辛就是帝喾,又叫帝俊、帝舜。火正是什么呢?火正活着时是火官的头领,死了就是火官之神。在传说中,高辛与祝融之间有君臣关系,这反映了两个分别奉高辛和祝融为始祖的部落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个主从关系给祝融的后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楚人在所有的古帝中特别推崇高辛。他们把高辛奉为宇宙的主宰。
历史上夏人曾与南方的三苗发生冲突,战争的结果是夏人前进了,三苗战败了,只好向后退。在这场战争中,祝融部落集团站在夏人一边,支援夏人,助了夏人一臂之力。夏人与三苗开战,祝融部落集团站在双方之间,除了认夏人为朋友认三苗为敌人,帮助夏人打败三苗以外,必然会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南北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时间约当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的后期,与夏代大致相合,虽然上承屈家岭文化,但含有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因此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实为受到夏文化影响的后期三苗文化。
因此,楚文化的主源不是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
夏代后期,殷人由东向西推进。他们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祝融部落集团既受到了殷人的文化熏陶,也遭到了殷人的武力打击。他们的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着,但是他们的部落渐渐地瓦解着,离散着。
自从有祝融这个称号以来,这个部落集团就一直受到强大的邻邦的威胁和制约。到了夏代和商代,周围全是强大的邻邦,他们处于四面包围的境遇中,分崩离析已经成了他们不可逃避的命运。祝融这个部落集团在上古民族流徙和民族冲突的旋涡中土崩瓦解了,这一点只要看看祝融八性在中国星散之势的分布就可以了解了。
在商代的时候,殷人称祝融各个部落为荆。荆是一种丛生的灌木,又叫牡荆。祝融各个部落分布在商朝的南境,所以《诗·商颂·殷武》中写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所谓南乡,本来是指大别山,桐柏山以北和伏牛山以东的中原南部,后来随着殷人的逐步向南开拓而同时向南延展。殷人向南开拓,荆人是首当其中。一直到了周代,殷人的遗民还对他们的先祖向南征战的业绩念念不忘。
汉水以东,住有三苗的遗民。殷人向南推进,越过了大别山、桐柏山,三苗的遗民受到了惊扰。慑于殷人的兵威,当地有些部落不得不迁往汉水以西去了。殷人的天文学水平,高于荆人的天文学水平。因此,在商代,荆人的酋长再也不能充任重黎、羲和那样显赫的角色了。商末周初,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mǐ)姓后人。他们已经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他们的酋长叫鬻(yù)熊。鬻熊很有政治头脑,他带领他的臣民背弃了渐渐衰落的商朝,亲附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周朝。《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在位时,有“鬻(yù)子”来拜见和投靠。这个“鬻子”就是鬻熊。《史记·楚世家》还记载说,鬻熊“子事文王”,就是以子爵的身份来服侍周文王。这“子”,就是周王朝给予归附的异族酋长的封号,是一种原始的爵位。因为鬻熊被周王朝封为子爵,所以鬻熊又可以称为“鬻子”。
鬻熊死于壮年,他的儿子熊丽继承他的位子,当了酋长。熊丽的孙子熊绎,在周成王的时候,被封在楚蛮之地,这才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楚国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地方偏僻,百姓贫穷,势力很弱小,地位也很卑下,还滞留在原始社会时期。名义上是个国家,实际上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他们的文化比周人的文化要落后得多。熊绎的国都也叫丹阳,但却不是在丹水之阳,而是在雎山和荆山之间,就是今天的蛮河中游接近上游的地方,也就是在今天的南漳县城附近。楚人怀旧之情比较浓厚强烈,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居,所以国都虽然迁走了,但名字还是没有改变。楚文化的滥觞期,从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开始,到东周和西周之交楚国将要兴盛的时候结束,历时将近三个世纪。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周成王把一块蛮荒之地封给熊绎,部分原因是周王朝土地面积太大了,这块蛮荒之地周王朝管不了。他把这块地封给熊绎,既是对熊绎占有这块土地的认可,也有画地为牢的意思,就是告诫熊绎,不能再侵占其他地方。熊绎的臣民就只好在雎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里耕耘、开垦,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水,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说的是生活清苦和居处荒凉。筚路,是一种车子,非常简陋,与民间的柴车类似。蓝缕,就是敝衣。“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说的是熊绎开国时艰苦奋斗的情况。“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说的是熊绎奔波于丹阳、镐京之间,为周天子效力。
熊绎为周天子尽的职责,主要有下列三项。
其一,是守燎以祭天。楚人崇奉火神,他们的酋长是正统的火师。为祭天而守燎的火师,要通晓巫术,善于做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派楚人的酋长做火师,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二是贡苞茅以缩酒。苞茅,就是灵茅。现在想来,一定是楚地所产的苞茅又多又好,以致于楚君有向周室贡苞茅的义务。《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管仲代表齐桓公责备楚国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句话译为现代汉语是:“你们上贡的苞茅没有送来,周王朝祭祀的苞茅供不上了,没有东西缩酒,寡人就为这个来讨伐你们。”管仲这里当然是借题发挥,乱找借口,但却堂堂正正。楚国的使者只好认错:“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这句话译为现代汉语是:“进贡的苞茅没有送上,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怎么会不供给呢?”缩酒的“缩”字,本作“茜”。“茜”字,上为茅,下为酒,恰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楚人的酋长在岐阳之会上,又管守燎,又管缩酒。楚君以熊为氏,但在楚器上,作为楚君之氏的“熊”一律写为“酓”。熊、酓二字,读音是相近的,所以可以通假,可以换韵。金文“酓”字,好象人饮酒的样子。那个时候,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对楚君来说,给周王室贡献苞茅是自己份内的事。
其三,是贡桃弧、棘矢以禳灾。楚人子革说:“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固然也是诉穷,说楚地物产不丰,但以桃弧、棘矢,共御王事,却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桃弧就是以桃木为弓,棘矢就是以棘枝为箭,都是用来驱恶鬼,除邪祟的,诸夏原来就有这个风俗。《左传·昭公四年》记鲁国的申丰说藏冰和出冰”。“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世的桃符、蒲剑、艾虎之类,作用与桃弧,棘矢相似。楚君向周室贡桃弧、棘矢,一则由于桃木和棘枝在楚地多有所产,是所谓方物;二则由于楚君作为祝融的后人不乏神秘色彩,他所进献的桃弧、棘矢大概被认为是特别灵验的。
很明显,熊绎这位国君实为酋长兼大巫。
丹阳,名义上是楚国的国都,然而没有城池,只是一个寨子,和后世所称的“棘围”很相似。北边有雎山,就是今天的主山塞;南边有荆山,就是今天的荆山,丹阳这个地方处于西边连叠的山岭和东边开阔的河谷之间。今天的蛮河,古时候称为雎水,从丹阳的中间由西向东流去。雎山这个地方,也许古时候山楂和猕猴很多,所以称为雎山。荆山,是因为这个山上长有很多的牡荆而得名。楚人的生活就依靠在雎山和荆山之间拓荒,这种生计是相当艰难的。
那个时候,周围是楚蛮,楚国处于中间。楚国的财力和兵力与楚蛮相比完全处于劣势。幸运的是,楚国历来生活在强大的邻国的夹缝之中,所以他们练就了困境中求生的本领,他们能够应付这样的生存环境。他们小心谨慎地处理着和邻邦的关系,而花大力气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由于楚人的先民长时期以来与华夏的先民交往,吸收了华夏先民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因此,与楚蛮相比,他们的文化素质显然占着极大的优势。丹阳一带虽然远离发达地区,可是一点也不闭塞。从新石器时代一来丹阳一带就是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交汇的地区。仰韶文化向南伸展,及于鄂西北。较晚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展,及于豫西南。更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伸展及于鄂西北。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靠近豫西南的鄂西北,便于楚人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容并蓄了华夏与蛮夷的长处。丹阳一带虽然属于草莱地区,刚刚开辟,但是它的自然条件对楚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西边有险阻,东边有原野,退可以防守,进可以攻取。荆山上有铜矿,荆山下有盐矿。楚国地盘虽然很小,人口虽然很少,但华夏的先进文明因素进入他们的国家,好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进了肥沃的土壤。
熊绎所承袭的基业,是鬻熊开创的。楚人感念鬻熊,奉祀他很殷勤很虔诚。鬻熊在商末周初是一位知名的酋长,很受周朝国君的礼遇,道教发源于楚国,兴盛于楚国,后世的楚人出于对鬻熊的尊敬和爱戴,就把鬻熊奉为道教的先祖了。周成王亲政以后,有人向成王说周公的坏话,周公只好跑到楚国去避难,后来流言得到澄清,周成王派人把周公接回去了。这样,熊绎在周王朝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由以上可见,初创期的楚国毕竟是很弱小的。如果我们打个比喻说,鼎盛期的楚文化是一只美丽的凤凰,那么,还在起步期滥觞期的楚文化就还只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风,一点也不必比鸟显眼,而且不会飞,不会叫,只能悄悄地栖伏在静静的幽谷里,谁也想不到后来它竟然会变成一只金凤凰,飞到乔木上去了。(www.zuozong.com)
楚人在雎山荆山之间,渡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惨淡经营的岁月,就显示由弱小转变为强大的势头。
熊绎传了五代传到熊。熊渠以胆气和勇力见称,有一则类似汉代李广射石饮羽的故事流传到后世。这个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楚国青铜治铸技术的提高。熊渠整治军备,成效卓著。他在江汉之间深得民心。当时正值周夷王统治时期,中原战乱频仍。熊渠趁机征讨蛮夷,扩大了楚国的疆土,从此就开始了对蛮夷文化吸收利用的过程。
当时与楚国相邻的蛮夷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周围是楚蛮,濮人和巴人在西南,扬越在东南。
什么是楚蛮呢?楚蛮,就是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楚国的东面,有邓、卢戎、罗,这三个国家呈纵向排列,熊渠时,楚国的力量还不够强,还不敢对这三个国家动用武力。楚国的南面,直到长江,是古漳水流域,当时除了偏东的权国以外,没有其他名见经传的国号,只有“江上楚蛮”——包括濮人、巴人、扬越的零散部落在内。楚人南征,可以从丹阳出发,东行经由今南漳县的武镇一带,折南进到今天的宜城县的李土当附近,然后长驱直下,沿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里的楚蛮较早地归附于楚国了。楚蛮给予楚人的文化影响,主要反映在某些陶器的形制上。但是熊渠在周夷王时大举讨伐的,主要还不是楚蛮而是濮人的庸和扬越的鄂。
庸是一个小国,位于今天湖北竹山县一带,居民以濮人居多,庸国和楚国之间,还有一些濮人部落。熊渠西征,在濮地不甚得手。扬越得名于扬水。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和长江。所谓扬越,就是扬水以东和以南的越人。《史记·楚世家》记载说,熊渠讨伐扬越一直讨伐到“鄂”这个地方。这里的“鄂”,在今天的湖北鄂州市境,是扬越的经济中心,原为鄂侯的领地,周夷王灭掉了鄂国,楚国人就乘虚而入。扬越给予楚人的文化影响,主要是供给大量红铜,从而促进了楚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红铜生产基地,很可能在今天的大冶县铜绿山一带,这一带就在鄂的南面不远处。那个时代战乱频仍,兵戈不息,红铜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就显得特别重要。熊渠就是受到了红铜的诱惑,才排除了自然和人力的各种阻碍,把自己的军队派遣到鄂地区。楚人一到那里,就开始了疯狂的掠夺,大堆大堆的红铜被楚人占为已有。楚人拥有了更多的红铜,他们的武器装备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显然,这一切都促进了楚国的兴起。
熊渠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庸,中子叫红,少子叫执疵。熊渠把长子封为王,第二个儿子封儿鄂王,第三个儿子封为越章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这三个王都在江上楚蛮之地。后来周厉王登上王位,熊渠害怕周王朝讨伐他,就把三个儿子的王号去掉了。向大约在江陵。鄂,就是东鄂,越章,大约就是今天的湖北秭归县。
《史记·楚世家》记载说:“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是熊渠为他封三个儿子为王找的借口。实际上,楚人在先秦民族结构中的地位很特殊,西周时既不是夏也不是夷,春秋时又是夏又是夷,直到春秋末期才正式与华夏认同。
西周末东周初期的时候,有若敖、霄敖、![]() 冒相继为楚君。若敖在位二十七年,霄敖在位六年,
冒相继为楚君。若敖在位二十七年,霄敖在位六年,![]() 冒在位十七年,加起来恰好半个世纪。后来的人往往略于霄敖不计,而将若敖、
冒在位十七年,加起来恰好半个世纪。后来的人往往略于霄敖不计,而将若敖、![]() 冒连称。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若敖,
冒连称。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若敖,![]() 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同书《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
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同书《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 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方圆一百里就是一同,方圆一千里就是一圻(yín)。土不过同,就是说土地面积虽有方圆数同但还不到一圻。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有方圆数百里。在若敖,
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方圆一百里就是一同,方圆一千里就是一圻(yín)。土不过同,就是说土地面积虽有方圆数同但还不到一圻。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有方圆数百里。在若敖,![]() 冒统治的时候,楚人虽然仍然在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地建设着家园,但已经拥有着方圆数百里的国土了。当时楚人进攻的方向还是以南线为主。
冒统治的时候,楚人虽然仍然在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地建设着家园,但已经拥有着方圆数百里的国土了。当时楚人进攻的方向还是以南线为主。
楚人及其先民依附于比他们强大而且进步的华夏及其先民,自然会吸收华夏及其先民进步的文化因素,年长日久,彼此的文化面貌就变得越来越接近甚至于极其相似了,这一点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滥觞时期的楚文化,从考古遗迹上看,与华夏文化没有明显重大的区别。只是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显露出它的特性和特色来。但是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那就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个主源,江汉地区要么华夏化,要么蛮夷化,不会诞生出一个楚文化来的。以长江大河为喻打个比方,主源与干流、支流有联系也有区别。论主源只需看长度,论干流、支流就不能不兼顾流量。楚文化的主源可以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
西周初年,楚国社会进步的速度还不快,楚人自立于周代民族之林的信心还不强。对华夏文化,他们由艳羡而效颦,还说不上有标新立异的勇气;对蛮夷文化,他们相识不久,相知尚浅,陌生之感和鄙弃之意未尽消失,还不大乐意吸受。他们刚露出一点试图熔合夷夏文化的苗头,但直到若敖、![]() 冒之世还没有进到别开生面的境地。
冒之世还没有进到别开生面的境地。
![]() 冒死了以后,
冒死了以后,![]() 冒的弟弟熊通杀了他的儿子,自己登上了王位,这时候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三十七年,自号为武王,武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就是文王。文王登位第一年,把楚国都城迁到郢,这时是周庄王八年(就是公元前689年)。
冒的弟弟熊通杀了他的儿子,自己登上了王位,这时候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三十七年,自号为武王,武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就是文王。文王登位第一年,把楚国都城迁到郢,这时是周庄王八年(就是公元前689年)。
楚国的郢都先后有好几个。这第一个郢都在今湖北宜城县境。这个地方可以控制汉水中游,北望南阳盆地,东临随枣走廊,南瞰江汉平原,西扼荆睢山区,是江淮之间的枢纽。楚国以郢都为统治中心,无论是窥伺中原诸夏,还是安抚汉阳诸姬,以及制驭巴、濮、蛮、越,都便于策应。
武王攻击消灭了权、州、蓼等国。文王继承武王的遗志,吞并了邓、申、息各个小国,使楚国的兵威到达了方城的外边。到了齐桓公开始称霸的时候,楚文王统治下的楚国已经强大起来了。
楚文王传了两代传到楚成王。楚成王开拓了更加广阔的领土,东边接近汝水,西边接近巫山。这个时候,楚国的领土已经有方圆一千里了。楚成王传了两代传到楚庄王,楚庄王确立了楚国的霸业。楚庄王传了六代传到楚昭王。楚昭王五十年,也就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两国的冲突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吴王阖闾与伍员、孙武等大举伐楚国,吴国的军队出奇制胜,长驱直入攻下了郢都。楚昭王弃都避难。
楚文化的茁壮期,开始于熊通继位,当时正是春秋早期的中叶,结束于吴国军队攻下了郢都,当时正是春秋晚期的中叶。楚文化的茁壮期,自始至终,大约经历了二百三十多年时间。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吴国军队从楚国撤离出来。第二年,吴国又大举进攻楚国,兵分两路:水路在淮水中游击败楚国的水兵,夺取了沈县(就是今天的河南固始县境);陆路在淮水支流汝水中游击败了楚国的败兵,占领了繁扬(就是今天的河南新蔡县以北)。楚国害怕呈国军队再次攻击郢都。把都城迁到鄀,但是仍然称为郢。这个鄀,并不是位于秦国和楚国之间的鄀国,而是楚国灭掉鄀国后所设的都邑,在今天的湖北钟祥县北部。
大约几年以后,就是楚昭王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503年——前492年)之间,楚国又把都城向南迁到今天的湖北江陵县境,还是称为郢。这个郢,就是现在的纪南城。楚昭王传了九代传到楚顷襄王。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将领白起攻破纪南城,楚国都城东迁。楚国以纪南城为首都,长达二百二十年左右。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了战国早期和中期,楚国在北面与国富兵强的韩魏角逐,总的趋向是楚国处于劣势,西南有巴蜀,但是巴蜀离楚国较远,又隔着千山万水,楚国对它们并不重视。虽然开辟了汉中郡、巫郡、黔中郡,但目的是防御,西北有号称虎狼之国的秦国。与楚国一会儿和好,一会儿开战,楚国始终不能得志。东面,楚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水兵和步兵一直打到东海之滨,步兵和骑兵多次出入齐鲁之野,然而战争频繁,建设缓慢。南面,楚人沿着洞庭湖的西侧和东侧,绕到南侧,继续开拓前进,一直到达五岭,因此,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是在江陵一带和今长沙一带。
纪南城的兴起,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开端;纪南城的陷落,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点。这个时期的楚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达到了最繁荣,最光辉的阶段。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善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和城市建设等,也欣欣向荣。经济结构方面,封建领主制的普及与家务奴隶制的延伸并行不悖。政治体制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和创造。旧有的县化大为小,新设的郡在县之上。全国各地都设有县,郡只是设于边疆。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哲学和文学的成就也很辉煌。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原,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
楚国的都城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以后,国势就渐渐衰退了。楚顷襄王传了四代传到负刍,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这段时期是楚文化的滞缓期。楚考烈王五十年(约公元前253年),楚国迁都到钜阳(今天的安徽阜阳县北)。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41年),楚国又迁都到寿春(今天的安徽寿县北)。楚国依据淮水中游,勉强维持着残破不堪的局面。还有长江以南的楚人,坚持了多年的抗秦斗争。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掉了楚国,从这个时候起,到汉武帝前期为止,大约一百多年,是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的时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