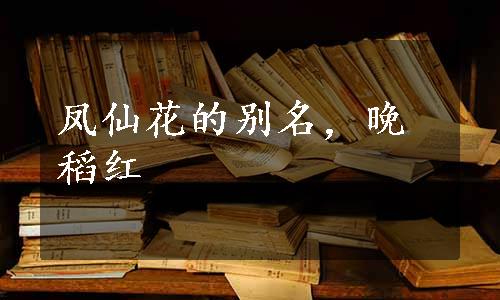
凤仙花又叫晚稻红。这个别致的称谓,似乎郭巨一带才有。不少东西,到了郭巨就被改头换面,比如“艾”,郭巨人喜欢叫作“青”。
为这个名字,我曾与张仿治老师有过商榷。在一篇写凤仙花的文章里,我写道:“凤仙开花总是在晚稻成熟时,因此叫作晚稻红。”其实没有人写过这个名字,我是根据郭巨的叫法音译而来。
张老师年轻时做过知青,干过农活,对农事颇为了解,觉得叫“晚稻红”不妥,因为凤仙开花一般在六七月,而晚稻成熟要在10月以后,两者时间对不上。张老师建议说,晚稻红与满堂红在土话里读音差不多,不如叫“满堂红”。我深以为然,于是听从张老师建议,把晚稻红改为满堂红。
有一次回家,和几位前辈聊天偶尔提及凤仙花,他们说,凤仙开花不是在晚稻成熟时,而是在晚稻种植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于是把“满堂红”又改回了“晚稻红”。
晚稻红,多富情趣的名字,我爱这名字有诗意。它的花期与晚稻同步,晚稻种下,它开花了,晚稻收割,它的花谢了,因此有了这别名。看起来,它离不开农事。这让我想到小时候,有时深一脚浅一脚跋涉于水稻田里,在田埂上经常会见到这种卑微的草本小植物,以一枝独秀的姿态,飘曳于饱满低垂的稻禾间。
至于凤仙本名,郭巨人倒不大叫,其实这名字更符合它的形象。它的花很像展翅欲飞的凤凰,在它花事繁盛时,如同有一只只小凤凰在枝头筑巢,亭亭玉立于丛叶间,令人想起“有凤来仪”的佳句。它的花开得相当有趣,往往一朵花还未凋谢,另外一朵便迫不及待地接上了,常常会出现成串开放的盛景。
它的叶子也有特色,不像其他花叶的圆润,而是修长的,形如剑刃。这种近似于自卫的形状,似乎预示了它对世人的不妥协,不讨好。这也有例可援,我妈妈就曾经在花盆里撒了几颗凤仙花种,期待来年夏天,能在院子里迎来满园花色。之后便是辛勤的养护,在精心浇灌下,这些凤仙倒是开了,然而花期只过去一半,便集体枯萎。瞧着那些原本笔直的不妥协、不低头的枝干,都匍匐在花盆边沿,我们心里多少有不忍。
与这些半途夭折的凤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家门外那条小路上的凤仙。小路两边的凤仙原本只有疏疏落落的几株,没想到几年过去,竟把整条小路都覆盖了,就像给小路穿了件花衣裳。(www.zuozong.com)
我曾观察过这些路边花仙子的生存环境。首先,这条路用水泥浇筑,不提供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土壤;其次,没有人会去浇水,缺乏必要的水分。除了那些悍不畏死的野草,按理说,没有植物愿意在此扎根。然而凤仙硬是从水泥夹缝里挣扎出来,并且呼朋引伴,召唤其他的伙伴一同前来。似乎在这里,它们找到了生存最好的天堂。这也证明了凤仙具有强悍的草根性,它不情愿被包养。它们喜欢无人理睬,喜欢自在开落。
但这只是它们的一厢情愿。历史上,它们受到过许多女人的青睐,上至贵妃娘娘,下至布衣裙钗。她们喜欢凤仙的唯一理由就是,它能用来涂指甲。在古代,这是一种天然的化妆品,很多娘娘们的指甲便是靠它染红的,比如杨贵妃,当她伸出纤纤玉指帮李太白磨墨时,那些指甲上涂的就是凤仙花。
凤仙花开时,也正值农事繁忙时,所以农家姑娘平日里很少涂指甲,只有到雨天不出工了,才会摘几朵凤仙来,把自己的心事一圈一圈涂在指甲上。
花开后,凤仙会结籽,成熟了,这些籽便四散弹落。小时的夏日午后,我在乡下闲逛,有时就会听到一两声清脆的弹籽声响,像一颗小炸弹的爆炸,声音很响,弹得很远,似乎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要把种子送到更好的远方。
我也像被弹出去的花籽,然而总是忍不住回头望,远处的故乡,也像一株夏日午后亭亭玉立的晚稻红。
· 凤仙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