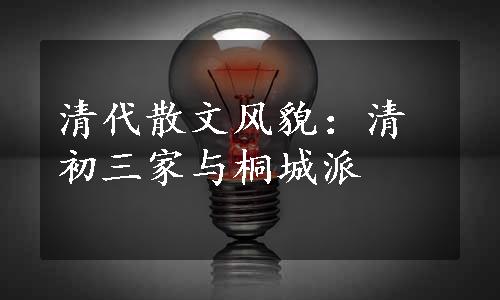
清代文章的风格也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最早出现的是所谓遗民文章,指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前明遗民所写的文章。他们是学者,又是反清复明的鼓吹者。在反清复明无望、清政府两面文化政策之下,他们只得潜心学术,研究古今政治得失,探源学术,辨证典章,因而作品多为政论和学术文章。文章真正能够代表清代前期特点的是所谓“清初三家”,即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他们的创作成就其实不高,但是其风格“接迹唐宋载道之文的传统”,适应了统治者崇儒佑文的政治需要,因而得到肯定。但是“清初三家”的文风则代表了从明末向清代转变的方向,也应该重视。
清代初中期文章以桐城派最具代表性。所谓桐城派,指的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领袖的清代主流古文流派。这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氏,因此以“桐城派”命名。桐城派早期“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做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古文理论”。[10]这一主张迎合了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因而受到官方的肯定。方苞之后,刘大櫆继承其衣钵并有新的发展,而到姚鼐,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姚鼐认为,义理、考证、文章是学问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必须兼备;他还认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面四个方面是“文之精”,后四者为“文之粗”,要求“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11]他还将文风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类,认为阳刚与阴柔因配合的差异而产生各种变化,产生不同效果,这方面论述对后人影响很大。姚鼐善于组织,他主讲书院凡四十年,门下弟子甚多。由于他的努力,桐城派势力大张,以后又有其门下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继承统绪,发扬光大,所以在整个清代的影响无可比拟。这既和统治者的推崇提倡有关,也与其作文有一定的规范的“熟套”[12]易于掌握有关。
晚于桐城派而起的阳湖文派,以张惠言、恽敬为领袖,不少人也是常州词派中人物,这些都与桐城派有明显不同。(www.zuozong.com)
清后期的散文,文学史家认为“主要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13]曾国藩并不讳言与桐城派的关系,他承认“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4]他企图通过继承姚鼐等人的桐城派思想来稳定、重构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社会现实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适应性的举措来修正姚鼐某些提法。比如,在“义理、考证、文章”三要素中加上“经济”(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以弥补桐城派空疏之偏颇,显示重视文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要求文章经邦济世。他还把姚鼐关于文章艺术方面的 “阳刚、阴柔”之说扩充为雄、直、怪、丽之美与茹、远、洁、适之美。曾国藩还主张文骈并用,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并在自己写作中加以贯彻。讲究文章的艺术美也是曾国藩散文理论的创新之处。
清末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体式。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干将,变法前后,他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时务报》主笔,发表大量鼓吹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流亡日本后又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政论,宣传变法,介绍西方制度与学术文化。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大气磅礴、观点表达淋漓尽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与当时的维新运动形势要求相适应的、适宜于报章刊载的接近于白话语体的文章体式,开了一个时代的文章新风尚,其影响是深远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