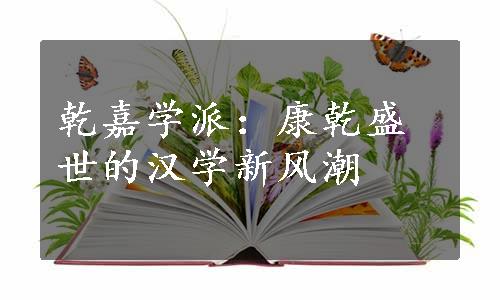
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为乾嘉学派时期。清乾隆、嘉庆年间是朴学发展的鼎盛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以维护清朝统治合法性为目的、以打击思想反抗为目标的文字狱事件。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学者们只有在故纸堆中去引经据典讨生活,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因而也称作“考据学”。朴学因其成熟、鼎盛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又被称为“乾嘉学派”。但这个时期的朴学,已经离开创始人的初衷。到乾隆纂修《四库全书》之际,几乎失去思想活力的考据之学成为“康乾盛世”的学术主流,乾嘉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主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与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如戴逸指出的那样,“清代汉学家整体的价值取向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偏颇烦琐,不食人间烟火,这不能不说是它的很大局限性”。[3]
嘉、道朝之际,思想文化界更加沉闷,但也有先觉者在沉闷的局面中发出有力的呐喊,提出了经世的观点和主张,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曲绝唱。如龚自珍喊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即在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后又一再增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之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刊行于世。《海国图志》是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李鸿章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中思想比较敏锐的一位人物。他长期担任军事领导和地方封疆大吏,后来又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长期的实际工作经历、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与各方面维新人士的交往等,使他的眼界比较开阔。他很早就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4]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两次上奏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南西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5]“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6]“千古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判断,显示出李鸿章等一些朝廷人士对于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是很清醒的。还有就是奉派出使欧洲的公使如郭松涛、薛福成等人,直接接触欧洲列强各国,感受到欧洲各国的制度和社会生活,他们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的思想也居于同时代人的前列。可惜在清王朝中,持有如此清醒忧患意识者实在太少了。但是即使如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只是主张研究儒家经典要通经致用,留心务实,注重在器物层面上考虑“自强求存”问题,并未从体制制度上考虑如何能够真正适应这一新的局面。但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朴学的学风转向了今文经学,乾嘉考据学走向衰落。学风的转变对晚清社会变革尤其是洋务运动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www.zuozong.com)
综上所述,可见这一时期乾嘉学派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乾嘉学派具有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逐渐地远离现实生活,学者们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特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上讲,在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局面:思想沉闷贫乏,但是皓首穷经、咬文嚼字的学术高度发展,成绩超越前人。同时,这一时期也萌发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文化潮流,为之后的洋务运动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