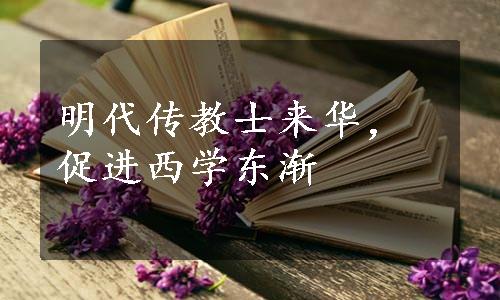
晚明之际,中国的东林清流倡导实学思潮的同时,西方也进行并完成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元代马可·波罗来华,于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游历中国17年,自称成为元朝官员。马可·波罗回国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游历见闻。尽管人们对马可·波罗在华游历的经历有些疑问,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神秘的东方大国富裕、繁华、文明礼仪以及风土人情的动人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激发了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巨大热情。
西学东渐是发生于晚明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源于西方的宗教观念、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西学东渐与传教士东方传教这一宗教历史事实紧密联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中国,也绕不开利玛窦神父这位在东西方都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利玛窦,本名Matteo Ricci,利玛窦是按照中国人习惯取的中文名字。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玛切拉塔。其父亲是一位药剂师,还担任过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声望的人物。按照这位父亲的安排,利玛窦的人生道路将和他一样进入仕途,当市长省长。因此,他将年满16岁的利玛窦送到罗马学习法律。但是从小就受母亲影响而信奉天主教的利玛窦,则希望献身宗教,把传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尤其崇敬方济各·沙勿略神父远东传教体现的献身精神和壮举。
方济各·沙勿略是西班牙人,耶稣会六位创会会士之一,被耶稣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用十年时间,步行传教,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传教。他最后的希望是来中国传教,并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登上中国广东沿海的一个叫上川岛的地方(今属广东江门市),只能在岛上传教,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一步,最后死在上川岛上。方济各·沙勿略拟在中国传教的活动失败了,但是他不畏艰难困苦,献身宗教事业的精神却深深感染了青年利玛窦。利玛窦通过方济各·沙勿略寄给欧洲教会的系列信件,感受到了在遥远东方传教的乐趣远远超过背诵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他从小立下的献身宗教事业的志向使他违背了父亲的心愿。利玛窦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耶稣会,罗马耶稣会新会员讲习所的范礼安神父接纳了他。从此,利玛窦就转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神学和哲学。按照余三乐先生的介绍,“罗马学院的哲学课程其实包括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其中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原理、音乐理论、透视学和测量法等。当时有的教材已经吸收了最新的科学成果,如地理学已经对西班牙、葡萄牙探险家新发现的大陆岛屿作了叙述,并在地图上予以标注”。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潜心研读期间,还深受其老师克拉委奥教授的影响。这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与著名科学家开普勒和伽利略有着很深的友谊和交往,他本人著有《几何学纲要》《天文学教程》等重要著作,还是《格里高利历书》的主要责任人。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著名的学府、名师的指导,尤其是自身刻苦的钻研精神,使利玛窦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学养,为他日后在中国传教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名耶稣会士登上了“圣路易”号航船,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之旅。他们是应耶稣会之召派往东方的。利玛窦等历尽千难万苦于同年九月到达印度果阿,1582年8月到达澳门。在澳门学习了一年中文、具备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最为基本的语言能力后,一个偶然机会,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到达了当时两广总督的驻地——肇庆。按照利玛窦的老师、当时耶稣会远东教务巡查使范礼安制定的传教策略,他们向地方官员表明,之所以来到中国,完全是因为“慕中华帝国之名”,没有其他目的。他们表示不会增加本地负担,只用本国人的捐款来维持生活。在以这套说辞掩盖传教的真实目的并赢得信任之后,经过肇庆知府王泮批准,他们在肇庆城东面购得一块土地,建起了住房,命名为“仙花寺”,院门悬挂牌匾曰“西来净土”。这些题词均出自肇庆知府王泮之手,多了一层保护色彩。利玛窦在肇庆仙花寺居住了六年,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三年后即可直接以汉语与任何中国人交谈交流,这为他今后的传教活动打下来极为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为了学习的方便,也便于西方传教人士掌握汉语,利玛窦和罗明坚还编撰了一部中葡文对照的词典。
语言障碍突破后,利玛窦等人广泛与中国官员和学者开展交流、沟通,以赢得进一步的信任。他请这些新朋友们参观他从欧洲带来的新奇物品,比如《圣经》、自鸣钟、棱镜等,这些物品中国人未曾见过,观者莫不赞叹称奇,尤其是那幅《山海舆地图》,给当时的中国官员和文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中,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天圆地方,中国处于那块方地的中央,中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中央帝国,而周边尽管也有些小国,那也只是一些未经开化的蛮夷而已。所谓外国也就是散落在大海之中的一些小岛而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说,那都是称呼周边未开化地区人民的。但是在利玛窦的地图中,中国仅仅是亚洲的一个部分,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南北美洲,在西边还有着数十个国家所在的欧洲。这个地图所体现的世界,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未知的世界,一幅地图就这样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也就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国家地理认知,从而颠覆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动摇了中央帝国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世界。
肇庆知府王泮本来就是一位地图爱好者,见到了利玛窦的地图后,他认识到这幅地图的价值,恳请利玛窦将之翻译为中文地图。这正好与利玛窦的想法相符。利玛窦知道,地图的翻译印刷,不仅可以在官吏和士人中为他赢得声誉,而且有利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也为他的传教事业带来巨大好处。因此,利玛窦积极翻译地图,在翻译中,利玛窦特地把欧洲地图中的子午线东移,把中国版图置于地图位置的中央。这是为了尊重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自尊心而采取的妥协措施,以达到降低士人对新地图的抗拒心理、加强传播效果之目的。
在肇庆住了六年的利玛窦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的干预,获得允许移住韶州,亦即现在广东的韶关。韶关被称为粤北门户,地处南北东西交通干道,便于利玛窦向内地发展。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是在韶关度过的。此后又到南昌、南京等地活动。在江西南昌,利玛窦脱下教士服装,换上了儒生装束,以一位“西儒”的身份沿途拜会官员。此时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地图经王泮刊印后分送官员,一些官员对这幅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广东南雄同知王应麟、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应天巡抚赵可怀等。赵可怀还在认识利玛窦之前就将从王应麟处获得的肇庆版地图刊刻在苏州城外姑苏驿的一处石碑上。在南京,利玛窦又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重新修订了世界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图》,由吴中明出吏部公帑刊刻,使之广泛流布,利玛窦的大名也随之不胫而走。
明朝自朱棣迁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利玛窦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仅在作为陪都的南京活动是不够的。因此,利玛窦总是在寻找进京面见皇帝的机会。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向万历皇帝献上大小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西洋琴等30余件贡品,并十分恭敬地奏上一本,叙述来华经历,表达对大明王朝的敬意和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同时也表达自己想定居北京,把西洋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贡献出来的愿望。
利玛窦无疑给皇帝带来乐趣,他奉献的西洋器物显然引起了万历皇帝莫大的兴趣。因此,尽管主管其事的礼部官员予以反对,但是利玛窦却因皇帝的接纳而得到在京居住的许可,并在一些官员朋友的帮助下,兴建了住所和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明朝廷还发给利玛窦等人俸禄,标志着明朝廷正式接纳了西方传教士。
利玛窦在北京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离不开徐光启。徐光启是上海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中。但在1604年那年的科举考试中一举得中,并被点了翰林,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北京,徐光启与利玛窦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为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共同奉献了心力。
其实,徐光启在北京与利玛窦相会,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早在十年前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徐光启随一位叫赵凤宇的主人来到韶关,任教于赵家私塾时,就在利玛窦韶关的居所中见到了肇庆版的那幅世界地图,被深深地震撼。尽管接见他的并非利玛窦本人,而是另一位叫郭居静的传教士,但是利玛窦的名字自此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中。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再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在南京拜见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西儒”。交谈之下,徐光启认为利玛窦是一位“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因为徐光启还要赴京赶考,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却奠定了跨越国界友谊的情感基础,也为日后徐光启成为天主教徒奠定了思想基础。果然,三年后的1603年,徐光启从上海到南京,因为利玛窦一行已去北京,徐光启再次拜访了罗如望牧师,连续八天听他深谈教义,然后受洗入教,罗如望为他取教名为“保禄”。
徐光启在北京靠近利玛窦教堂的旁边租了一套住处,天天几乎足不出户地与利玛窦谈宗教、论科学,心灵和求知欲获得了极大满足。在他为利玛窦编译的一本题为《二十五言》的著作写的跋文中甚至说,听了利玛窦的议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京合作一共三年多。这三年多时间是两位东西方文化科学巨人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伟大开端。在与利玛窦的交流中,徐光启得知,利玛窦一行实际上还带来了许多西方著作。这引起了徐光启的高度关注,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他向利玛窦提出了这一要求后,得到利玛窦的赞同。其实,利玛窦也想把这些著作翻译出来,使之在中国得以传播。此前利玛窦已经尝试了几次,但是都不成功。原因是中西文字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翻译起来难度很大,尤其是如果翻译不能理解所翻译的内容,要成功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徐光启是一位勤奋好学、勇于攻坚的学界精英,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也。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他还认为:“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 于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始了对《几何原本》的翻译。之所以选择《几何原本》翻译,是因为欧几里得这本著作,体现了欧洲数学当时的最高水平,也是一切科学的根基。同时,利玛窦在与中国人士的交流中,感到中国学者对于几何学并非全无所知,但是对于几何学原理尚未深研。徐光启也认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当以百家之用”。(www.zuozong.com)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始于1606年秋天,方法是利口述,徐笔录,成文后又反复修改,三易其稿,终于一年时间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有材料说,该书的翻译修改,还有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忭、赵可怀等部曹官员的意见建议;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等也提出过意见;此前与利玛窦尝试翻译过《几何原本》的瞿汝夔、张养默的文稿虽不成熟但也具有参考价值。《几何原本》前六卷于1608年在北京刊印出版,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是西方科学知识系统进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一部包含众多中西人士智慧的破天荒之作,值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利玛窦、徐光启翻译所据的《几何原本》是利玛窦老师克拉维奥神父的修订本,共十五卷。后面的几卷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如徐光启因父亲去世而离京守制,一去三年,而他于1610年12月15日回京时,利玛窦却已于半年前去世了。因此,翻译《几何原本》未成全璧。虽然有些遗憾,但是,这部著作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译稿当时确定的中文表达的几何学术语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对角线、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相似、外切、几何等,到今天仍被沿用。 而经由该书引进的数学证明的思路、方法,在中国数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几何原本》成功翻译出版,对于中西人士都是极大鼓舞。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完成后,立即合译《测量法义》一书。徐光启离京守制后,利玛窦又与李之藻于1608年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和《圜容较义》两部天文学著作,还合作完成数学著作《同文算指》的翻译。利玛窦自己的著作《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写作。徐光启还用《几何原本》的方法,重新研究解释中国传统数学。徐光启陆续著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著作。他的学生孙元化受到《几何原本》的启迪,连续写作出版了《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三部著作。到清代,这类著作更多了。
利马窦还有由他口述、徐光启笔录的《畸人十篇》。该书记录了利玛窦对徐光启和吏部尚书李载、礼部尚书冯琦、吏科都给事曹于忭、工部郎中李之藻以及吴中明、郭敦化、龚三益等人提出问题的回答。利玛窦按照天主教义解释和回答了中国士人提出的包括生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大量引用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加以辩难,宣传天主教理念,在那时的官员队伍和思想精英们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传教活动的开展。
1610年5月17日,利玛窦在北京南堂病逝。经过他的朋友们的努力,经万历皇帝批准,葬于北京城西阜成门外二里处的“滕公栅栏”。这是北京的第一处洋人墓葬。
利玛窦去世了,他和他的中外朋友们一起开创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在徐光启带领下仍在继续发展。利玛窦在世时曾经与徐光启规划过多种翻译项目。他去世后,徐光启继续与利玛窦的耶稣会同仁朋友们通力合作,继续开展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比如,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诸书。《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找水、取水、蓄水、灌溉、排水和水利工具制作图谱的著作,属于农业类著作,因此被收入后来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又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又切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对于水旱灾害频仍、以农立国的明王朝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意义重大。与此同时,熊三拔还在南堂亲手制造一批水利机械,吸引了京城官员们的关注,不少人还学习制作方法,自行制作,从而使这些先进机械由此得到推广。
《简平仪说》属于天文学著作。简平仪是一种“专以观测太阳运行为对象的简化形式的平面仪”“简平仪与浑盖通宪皆以平测浑者,而浑盖地盘随地更换,简平仪则只需以地平线测之,尤为便捷”。《简平仪说》和《浑盖通宪图说》的翻译出版,使西方天文学知识在中国得以流传,并逐渐深入地影响到朝廷历法的编修,影响到人们关于天的传统认识的改变。对于徐光启而言,翻译这些著作,也是他涉足天文学的开端,为他后来主持历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利玛窦利用西洋科学知识修订历法的意愿,经由徐光启等人持续不懈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得以实现。清初顺治年间《时宪历》公布实施,这是晚明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取得的巨大成果。虽然利玛窦、徐光启等人未及见到这一成果,但是他们的努力和巨大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时间、判断气候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规则。历法是农耕社会的产物,最初是因为农业生产需要按照季节来安排耕种、收获等农事活动,所以产生了最早的历法。历法需要精确,才能更好地指导农事活动。人们对于天体运行、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发展的,人们根据认识到的规律来制定历法,同时也根据规律来推定天体天象的变化。但是历法确定的日时和天象发生必须由天体、天象的实际运行状况来检验。如果发生偏移,与天体、天象运行的实际不相吻合,则说明人们对于天体、天象规律的认识不精确、不科学,这就必然引发历法的改革。但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的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根深蒂固,皇帝被称为天子,对天道运行理所当然应该了如指掌,因此天道运行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被视为皇家权威的象征、国家主权的象征;而一旦对于天象观测发生失误,则将动摇皇帝和朝廷的权威,所以历法是不能轻言更改的。换言之,历法改革如无充分理据,是很难做到的。
明代使用的《大统历》是在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基础上删定而成的。但是这个历法在实际施行中,所推测的天象与实际往往不合,却与利玛窦所推算的屡屡完全吻合。利玛窦在罗马的耶稣会大学曾经精心学习过天文学;早年在韶州时,他还自称天文学家,他制作的天文仪器也引起朝野人士的高度关注;后来在江西白鹿洞书院讲学传教时,他关于日食月食发生原因的知识,更是引起了聆听者的兴趣,也为利玛窦个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奠定了他“西儒”的地位。利玛窦到北京后,上奏万历皇帝,表达了参与历法修订的意愿,但未引起重视。利玛窦没有为此停止他的工作,反而加紧准备。他翻译了欧洲通行的《格里高利历书》,并和中国流行的历书相配合,简明扼要,引起身边许多朋友的兴趣,曾有人建议他将这一历书印出来,但是利玛窦却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他知道,未经朝廷允许,私自印制历书,“有遭罪倡乱之嫌”。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历书修订被正式提出,原因是当年十一月发生日食,钦天监所测时刻有误,但修历仍然被搁置。后经周子愚、李之藻、熊明遇等人推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礼部决定启动修改历法工作,并对修历工作作了分工:由邢云路、范守己研究中法,由徐光启、李之藻带领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研究引进西法。后因“南京教案”发生,修历无果而终。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初一又发生日食,钦天监的预测再次与实际天象发生偏差,新皇帝崇祯大为恼怒,同意时任礼部侍郎徐光启的建议启动修历。为保证修历的科学性,徐光启还组织包括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在内的中外人士共同翻译了137卷西方天文学著作,制造一批天文观测仪器,修历工作也稳步推进,任务得以完成,并经崇祯四年(1631年)、五年(1632年)、八年(1635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六年(1643年)多次日食验证,崇祯皇帝终于于1643年8月下诏颁行。徐光启未能等到这一天,他已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初八日病逝,他是怀着对于引进西方科学修历未竟的遗憾而离开的,终年72岁。徐光启病逝之前,上书崇祯皇帝,为修历相关人员请功,推荐自己的接班人,修历后续的事务是由他的接班人李天经完成的。
但此时明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丧钟敲响了。有明一代,新的历法推行终成泡影。由利玛窦、徐光启、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推动的这一修历成果,一直到清朝建立之初的顺治年间,才以《时宪历》之名推行,摄政王多尔衮还在历书封面上提写了“依西洋新法”,表明了对于西方科学的容纳态度。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由此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有清一代,汤若望、南怀仁等一代又一代传教士执掌清朝钦天监近200年,就是证明。
其实,当时在明朝传教的人除了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等著名学者之外,还有不少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据柳诒徵转引并改订过的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记载,当时在华传教的传教士已达65人,其中不少传教士还是由明入清的跨代人物。由于采取了范礼安制定的正确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和利玛窦等人“科学传教”方略,即以介绍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为先导、以崇仰中国文化传统为外衣、以结交各级官吏和知识精英为中介,传教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至明朝末年,信教华人已达数千人,其中宗室114人,内官40人,显宦4人,贡士10人,举子11人,秀士300余人。到清初的康熙年间,奉教人数已达到10余万人。西方各国传教士也为中国带来7000余部各领域科学著作,其中翻译成书共338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