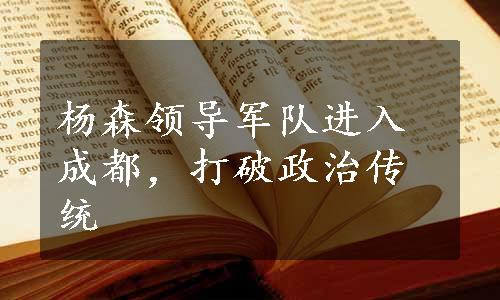
当杨森(见图7.1)于1924年2月带领他的军队从东门进入成都时,他对于这座城市已经有过一些了解了。虽然他是在四川一个农村里长大,那里距离川东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但在1905—1912年他却在这段新政的高峰时期首次住进了省城。〔8〕那时他刚好二十来岁年纪,便进入了军官速成培训学校,这所建立在成都的军校是为了给四川的新军旅充实军事人才。由此他对于成都的城市改革的第一波巨浪便有了清楚的认识,而这个城市改革的巨浪是由周善培和他的同僚们领先发起的。

图7.1 杨森(《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
杨在保路运动期间还只是成都的一名低级军官,他见证了1911年11月赵尔丰的行政管理政权的倒台。他在那场推翻蒲殿俊,以及推进尹昌衡夺权的骚乱中,是恢复城市秩序的军队中的一员。此后,杨森于1912年初离开成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到处寻找他的运气,最终因在1913年倒袁运动的二次革命中站错了队而告终,不得不去云南寻找避难所。当蔡锷的云南部队于1916年进军四川时,他便跟着他们一起回来了,并在四川军阀们那人才济济的一席之地迅速地脱颖而出。1916—1924年,他频繁地进出成都,参加军阀们的军事会议。会上四川的将领们试图谈判出持久的和平无果,却趁机在城市毕业的青年中招募随从和低级军官。
虽然杨森还从来没有过对像成都这么大、这么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城市掌权的经历,但是他在占领泸州,一个位于重庆以西,长江边上的小城市期间,已经为他自己建立了城市革新者的名声。在泸州时,他集结了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助手,他们中有一些人还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帮助杨森为他自己勾画出了一个城市改革者的新形象,命中注定要为四川创建出许多新城市来。他正是带着自己的这个新形象到达成都准备大干一番的。
然而,杨森在成都做出的第一个姿态,便是和成都的政治传统保持完全一致:他主持了成都每年一次的花卉节的开幕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的,晚清时期的花卉节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作用,当年的省政府官方努力将它转变成了一个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展览会,要求各县将他们的工农业产品送来展览。革命之后展览会已经逐渐衰败了,1920年的展览会,随着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大肆宣传,要促进经济国有化和联合抵制日货,又重新恢复了过来。整个1920年代,成功举办展览会成为四川军阀管理工作良好的一个标志。〔9〕作为成都的一名年轻的军事学校的学生,杨森必定参加过晚清时期的工业展览会。他在1924年和1925年主持过两届展览会,由于当时四川政治破碎,不可能与前面举行过的展览会相匹敌,成为影响全省的盛事。但是1925年举行的展览会仍然吸引了来自全省144个县份中的40%到50%的县城,送出了他们的产品参展。〔10〕
1924年的交易会开得顺风顺水之后,杨森将主要的金融财政支出用在促进一件更为新奇的事情上:那就是开展全市范围的提高文化程度的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都分会于1924年春天开始运作,它的资金预算大约为7000元,其中3000元来自杨森本人和杨的小学同学王缵绪管理的“市政公所”。全市有名的教育领导者带领12队人马,发誓要征召1000个志愿者,来为成都市数以万计的商店职员和体力劳动者开办夜校,使用的课本是由晏阳初[1]在他的国民运动中出版的《千字文》。1924年9月,杨森参加了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祝贺他建立了297个教学站,有10267名学生入校学习识字。杨将军引用了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指出大多数识字教育都不能长久的特点,他鼓励该促进会一定要将它的热情维持并进行下去。〔11〕
对于杨森来说,比平民识字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公民中大力推广体育锻炼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少城公园扩大,将其一部分改变成公众锻炼场地。少城公园自1910年建成,很快地成了成都市民文化的聚焦点。1913年,为了纪念两年前在保路运动斗争中牺牲的成都烈士,在少城公园里竖立了一块纪念碑,许多公众纪念会和示威运动都在这块纪念碑下举行。〔12〕不过,在杨森修建跑步道之前,这个公园主被许多茶室和餐馆的老顾客用作他们每日光顾的基地。1925年春天,杨森主持召开了一次卖弄炫耀的全省范围的体育运动会,他声称,这是自从晚清以来开先河的一次运动会。〔13〕他敦促成都居民定时锻炼身体,还发起对裹脚、留长指甲(不卫生,是一种懒惰的表现)、打牌(它们使身体壮实的人变得瘦弱不堪,而打球则使人身体强健),男人在公众场合不穿上衣(不文明),男人身穿传统的长袍(他们这样做,浪费布,而穿短衫使人运动自如,可以促进尚武的精神)〔14〕等现象的批判。
杨森管理成都期间,除了少城公园之外,增加的另一样东西便是通俗教育馆〔15〕,馆长是卢作孚。杨森占据泸州时,卢作孚在泸州也建立了一座类似的机构。卢和其手下设计了一个博物馆,收集了关于自然史、历史、农业、工业、卫生、教育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展品。还有一个动物园,一座图书馆,一个音乐厅和一些教室。〔16〕该博物馆展出来自全省范围的产品,都是来自1924年的工业展览会。除了提供一般的教育启迪之外,据访问学者舒新城所说,该博物馆是中国最好的博物馆〔17〕,它还用作理性打击民间信仰的场地。〔18〕杨森将一座寺庙给了一个外国人办的盲人学校用作教室,该学校人员对寺庙中的宗教雕塑进行了抢救,将其送到博物馆展览。〔19〕杨森另外一件用来打击“迷信”的武器就是19世纪中叶大肆破坏四川的反叛起义的领袖张献忠留下来的遗物——那块可怕的“七杀碑”(见第一章)。地方上的传说坚持认为如果这块“七杀碑”重见天日,会使灾难再次临头,因此它一直被放在成都县县长的衙门里,用东西给盖了起来。通俗教育馆成立时,杨森下令将此碑移至该博物馆。〔20〕该馆还招待了由学校团体演出的新式表演剧,以“改革成都的传统习俗”〔21〕。
少城并不是杨森情有独钟的一所公园,他还出资修建了一所中央公园,以清朝省政府总督的总部为基址。该座公园在杨森时代之后重新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他自己的住所是前满洲将军的司令部,在其附近,杨森占用了一所寺庙的地产将其改成公园。这座公园非同寻常,几乎是绿荫遍地,绝没有在别处无所不在的茶馆,明显地游人稀少,非常宁静。杨森还引进了植树节,这是最先由袁世凯引进到中国的,现在出现在了成都的日历上。杨森还在清明节,这是传统的纪念逝者的节日,主持了一次植树的纪念活动。〔22〕
少城的南端,也就是从前的旗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高档区,这使得它成为杨森眼中最为显著的目标——一个最具震撼性的,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计划的目标,他要重建成都。他将他的官邸和少城公园之间的那条路铺上碎石,然后将这种新的铺路技术在成都推广开来。杨森的拓宽街道以及铺平道路的计划,从他进入成都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离开,这是成都人民至今最为记得他的一件事。一群来自市政公所的工程技术人员,起草了一张该市街道的表格,将所有的街道划分等级,标示出每条街道所需要的宽度,并留出人行道的空间。他们决定从最为拥挤的地点开始:成都最为主要的商业区,是沿东大街一线,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东门,这里是要往重庆去的绝大多数人流,以及其他要往川东去的人流的必经之路(见地图3)。计划在报纸上公布了,受计划影响的街区的街正被召去开会,通知他们,负责向新建街道毗连的所有房产业主和租住户收集修建街道所需要的资金。〔23〕其结果是相当令人震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图7.2)和后面的(图7.3)复兴街的照片中看到。复兴街是计划中要拓宽的一条中心商业街,清朝所建的商业场就在那附近。
 (www.zuozong.com)
(www.zuozong.com)
图7.2 复兴街在拓宽前的街景(《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

图7.3 拓宽后的复兴街(《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
除了将原有的街道铺平之外,杨森还修了一条新的街道——春熙路。他希望这条路会成为他管理成都的一个象征。这条路就建在清政府按察使衙门的原址上。衙门前面的院子一直延伸到了东大街和清末修建的商业场之间。由于它与该市两个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毗连,原有的按察使衙门就成了杨森想要修建的这条模范现代街的必然选择了(见地图3)。1925年元月,新的道路修建完工,安装上了一块金属的纪念饰板。杨森邀请一位老学究为这条新修的路起名字,他选择了“春熙”(春天的光辉),这是引用了《道德经》第二十章里一句诗中的隐喻,说的是寻常老百姓的快乐。〔24〕春熙路的开通在成都的交通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它是这个有围墙包围的城市里第一条能够轻松通行人力车的街道。在杨森离开前,成都市里已经有好几十台人力车在运行了,不久,它们的数量就超过了老式的轿子。而这种老式的轿子是当时,那些不愿意走路,而又付得起钱的人所选择的最为主要的交通工具。〔25〕图7.4就显示了成都一条还未拓宽的街道,它塞满了人力车,两边还拥挤着电线杆子的景象。

图7.4 成都拓宽街道之前的一条主要街道的典型街景。在轿子和穿长袍的行人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人力车和电线杆(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多:目录编号:No.98.083P/25N.)
杨森修路的热情也延伸到成都以外,他的工程技术人员接到指示,要为成都和灌县之间全长55公里的路线画出一幅公路地图来。灌县位于灌溉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附近。曾经分别在1915年和1922年,就定下了要修筑这样一条公路的计划,但是每一次的努力都由于战争而终止了。杨森在他占据成都期间也未能看到这条公路竣工,未对其视察。因为他将主持修这条公路的权力授予了成都一个杰出的商人,然而这条公路的施工一直到它的政治上的发起者离开时仍然在继续,省内第一辆汽车能够沿着这条用土夯实的灌成公路开行的事是在1926年。〔26〕
除了他的文化项目和建设项目之外,杨森还给成都带来了第三种创新:一种政治风格,可以称之为“平民化的独裁主义”。他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单纯的、直言不讳的形象。他总是衣着随便地出现在公园里,每天将他的办公室开放两个小时,接待任何想要和他面谈的人。他重开了一间起始于民国早期的公共讲坛,他自己在讲坛重开的仪式上,面对一大群听众,站在一张桌子旁开讲了第一课。因为杨森走进讲坛时,身上衣着十分简单,还戴着一顶草帽,与会者都没有认出他来,因此无人起立。一家当地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他在这次场合的讲话解释了他之所以要恢复自1911年以来衰败了的这个公共讲坛,是因为他要弄清楚人们在想些什么,这样,当他实施他的管理计划时就可以直接面对他们了。
我若是坐着轿子在街上穿行,你肯定无法和我说话。如果我想要做成一桩事,我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却说它很糟糕,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一起讨论这桩事呢?这就是为什么要开这家公共讲坛的头号理由了。公共讲坛建立至今,就是为了让任何人,不管他是谁,都能到这里来发言,表达他的意见,对我进行批评。〔27〕
周善培1906年对成都居民所做的关于警察价值的讲话也许对于杨森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但是杨森这种规劝式的讲话内容和周善培的讲话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周善培的讲话,至少按它们发表的版本来看,强调了警察存在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而杨森,与之相反,则是完全着重在他自己作为一个关怀人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领导者的功绩上。
杨森对于他自己的平易近人和随和、无拘束的强调,是与他的一种明显的对纪律的强调方式相辅相成的,这一点他在1920年代中期进成都之间就已经拿捏得非常好了。1920年代早期杨森还在泸州掌权时,有一天他把一群当地的小学男生邀请进他的办公室,给他们糖果吃,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块小铜牌,上刻“不要娶裹脚女孩”的字句。他还坚持要求他们立刻把铜牌别在他们的校服上。〔28〕在泸州的一次运动会上,他将一百多个裹脚的女性观众集合拢来,命令一队年轻的士兵将她们带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给她们上了一堂课,命令她们扯下裹脚布,他把它们都烧了。〔29〕在成都,他在灯柱上和墙上钉上告示,上面写了一系列“杨森说……”的指示,按照他自己的文化改革计划指导人民应有的正当行为。“杨森说:要穿短衫,不仅可以节约用布,还能促进尚武精神!”就是其中一例。据近来在成都出版的一本杨森的传记所说,地方志的编写者声称,将军把这些指示看得比什么金玉良言都更重要——他们还声称他派了一队人上街检查,将男人穿的长袍下摆剪掉,发现如有人在公共场所没有穿短衫就抽打。〔30〕一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警察强迫全城的居民为杨森的植树节大会仪式捐钱,还命令他们亲临植树现场。结果实际上只有几十个普通市民掺和到学生队伍里,他们也是被迫来的。〔31〕杨森自己夸耀说,他骑马经过少城公园时发现了一群赌徒,他用鞭子给了他们一顿好打。他还回忆到当警察没有遵照他的命令,将街道上居民喂的猪清除干净时,他把站在人群前面的警察长给打了,尽管那人叫喊道他不该挨打呀,因为他是一个秀才。〔3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