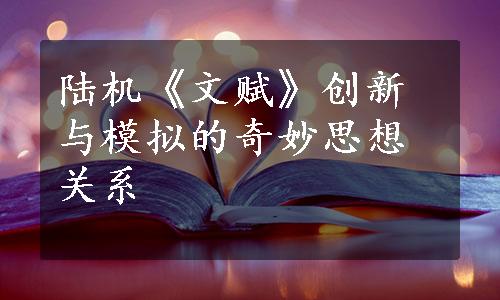
陆机在《文赋》里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下文又说:“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李善注说:“已披,言已用也。”又说:“言他人言,我虽爱之,必须去之也。”由此可见,陆机在创作上是“提倡创新,反对抄袭”(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二六四页)的。
奇怪的是,陆机自己的诗文却很少创新的地方,反而对前人的作品大力模拟。大家都知道他的《七征》模仿枚乘的《七发》,他的《辨亡论》模仿贾谊的《过秦论》,他的《演连珠》和《遂志赋》模仿班固的《拟连珠》和《幽通赋》,他的《谢平原内史表》模仿蔡邕的《让高阳乡侯章》。在诗歌方面,这种例子更多,如《短歌行》和《苦寒行》是模仿曹操的,《燕歌行》是模仿曹丕的;而拟《古诗十九首》的十二首,尤为突出。这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这里就牵涉到对于“朝华”和“夕秀”的理解。他主张力避前人已用过的“朝华”,而追求前人未用过的“夕秀”,那么究竟什么是“华”和“秀”呢?在我们看来,他是指作品的艺术技巧,特别是语言辞藻方面,而没有包括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内。试以《拟青青河畔草》为例:
靡靡江离草,熠耀生河侧。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再看原作: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牗。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里不但内容基本上一样,连句法也差不多;原作多用叠字,拟作亦步亦趋。陆机的工夫仅仅在于把“青青”“盈盈”改为“靡靡”“皎皎”,把“河畔”改为“河侧”,把“红粉妆”改为“妖容姿”,把“荡子”改为“良人”,把“空床”改为“空房”,等等。这样的“怵他人之我先”,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要抛弃前人的“华”而创造自己的“秀”,不过如此而已。
在陆机之后五百年,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说过:
假今述笑哂伏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榖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
李翱这里所举的例子,正是陆机所注意的地方。拿这一段来说明“谢朝华于已披”两句,我们觉得是很适宜的。不消说,这样对待创作,是走到舍本逐末的歧路上去了。(www.zuozong.com)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陆机“提倡创新,反对抄袭”,而应该指出他主张语言上创新,但并不反对内容上的抄袭。郭绍虞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说,“他认为意和词,宜创造而不宜沿袭,宜新颖而不宜陈腐”(上册第七〇页)。我们认为,在“词”上面,他的确主张“创造”“新颖”;但在“意”上面,他却并不反对“沿袭”“陈腐”了。如果在这句论断中删去“意”字,也许更符合于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实际情况。
陆机《文赋》有“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两句,李善注说:“言文之体必须以理为本。”因此,我们好像可以说他在这里能够“指出思想与艺术之间的主从关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二六四页)。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玮,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等等,好像只是陆机的主张的发挥。假使我们拿他自己的作品所犯严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对照来看,好像他是一个言行完全矛盾的人。
不过我们若要正确理解这两句的意义,恐怕不能孤立地只看这十二个字,而应该把全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陆机常常用“意”“义”“思”等字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用“文”“辞”“言”等字代表作品的艺术形式。两者常常并列,如:“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辞程才以效伎,意习契而为匠。”“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把这些地方综合起来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看出陆机对于内容形式主从关系的真实主张了。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每在二者并举之外,还要发挥几句,而这些发挥的话却总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例如在第一段里虽然说担心“文不逮意”,但他所谓“才士”的“用心”,却主要在于“放言遣辞”的“妍蚩好恶”。又如在“选义按部”一段中,虽然包含了“理扶质以立干”二句,但他反复阐明的显然在于“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以及如何“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等等,仍然不外乎表现手法方面。此外,在“辞程才以效伎”后边,他强调了“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而在“其会意也尚巧”下面,又提出了声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这类例子,实在举不胜举,因为几乎通篇都是如此。所以二者并列不一定意味着二者并重,他是有所偏重的。
其次,就全赋所论文章的优缺点和写作的甘苦看,陆机也常常着眼于艺术技巧方面。例如他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意思是说,在全篇作品中必须有几句特别能够惊动人的地方,来赢得读者的赞赏。这好比“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少数警句可以提高全文的价值。他又提出“含清唱而靡应”“虽应而不和”“虽和而不悲”“虽悲而不雅”“既雅而不艳”等等写作上的毛病,用音乐作譬喻,来说明表现手法上或语言风格上应该避免的缺陷;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了。有了“警策”,就瑕不掩瑜;如果不应、不和、不悲、不雅、不艳,就瑜不掩瑕。他反复阐明这些意见,可是很少论到思想内容方面。
最后,就陆机对于文学不同样式的写作特色的说明看,也可以知道他是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他把文学作品分为十类,对每类都有四个字的说明:“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批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里讲的,绝大部分是语言风格方面的事;涉及内容的,仅仅有“缘情”“体物”“相质”“博约”“精微”等处而已。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各种文学体裁在写作时所应注意的地方,主要不在于思想内容方面。下文所谓“禁邪而制放”,恐怕也不是指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情感,而是指表达思想情感的文辞。
从这里可以知道,《文赋》的总的倾向是把作品的艺术形式放在主要的地位,而把思想内容放在次要的地位。尽管他说“理”是“干”,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认为思想内容是创作的根本,反而用全副力量来解决“垂条”“结繁”的“文”。这和他在创作上的形式主义缺点,是一致的。真正确立“思想与艺术之间的主从关系”,还有待于刘勰。
关于内容究竟指什么东西的问题,陆机与刘勰的理解也不一样。因为牵涉到别的方面,这里暂时不谈了。
(原载《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