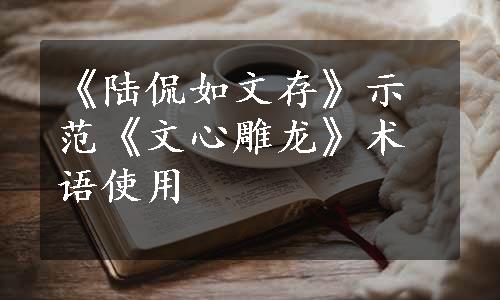
——书《释“风骨”》后
《文心雕龙》中有些常见的字,如“道”“性”“气”“风”“骨”之类,大都有专门术语的性质。对于这些字的解释,在学术界中曾引起不少的争论,这些术语之所以引起不同的理解,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刘勰使用这些字的时候,并不永远完全当作术语,有时只当作普通的字。即使当作术语用的时候,还有基本的意义和引申的意义的区别。如果我们混淆了一个字的普通意义和专门意义,就会发生误会;而专门意义中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异点如被忽视,也难于获得确切的理解。
试以“体”字为例。这个字无疑是《文心雕龙》中的术语之一。在这样的场合,“体”字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体裁,如:
全为赋体。(《哀吊》)
即议之别体也。(《议对》)
二是风格,如:
五则体约而不芜。(《征圣》)
则数穷八体。(《体性》)
这些是作为术语用的基本意义,此外还有引申的意义。在下列一段中,“体”字即不能作体裁讲,也不能作风格讲:
毛公述《传》,独标“兴”体。……起情故“兴”体以立。……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比兴》)
这里“比”“兴”二字,并不是诗赋一类的文章体裁,也不是典雅、精约一类的作品风格,而是一种抒情叙事的手法。这和体裁、风格有联系而又有区别,所以是“体”字做术语时的引申意义。
不过在《文心雕龙》中,“体”字却常常当作普通的字来使用。在这样的场合,它有时作为主体、要点讲,如:
声为乐体。(《乐府》)
此立赋之大体也。(《诠赋》)
有时又作为体现讲,如:
故体情之制日疏。(《情采》)宜体于要。(《序志》)
此外还有区分、分解的意义,如:
并体国经野。(《诠赋》)或体目文字。(《谐隐》)
如果把上引几句中的“体”字也当作专门术语而解作体裁、风格,那便窒碍难通了。
这一类普通意义与专门意义的区别,专门意义中的基本意义与引申意义的区别,不独存在于“体”字上,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字上。例如“道”字,有时作普通的道理、道路讲,有时则作为专门术语而指“自然之道”(就是客观事物规律或普遍真理) ,有时又引申而指能够体现“自然之道”的儒家圣人经典之道。又如“奇”字,有时作普通的奇异、奇怪讲,有时则作为专门术语而指作品中的奇伟的幻想成分(就是作者通过幻想而在事物正常样子之外所增加的动人的成分) ,有时又引申而指脱离实际、过分追求诡异的弊病。近来学术界的一些争论,如关于刘勰思想体系的问题(是唯物论的、唯心论的,还是二元论的) ,关于刘勰对浪漫主义的看法的问题(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 ,关于刘勰对《楚辞》的评价的问题(是褒多于贬的,还是贬多于褒的) ,等等,原因虽多,但对于“道”“奇”等字的理解上没有区别开普通意义和专门意义,以及专门意义中的基本意义和引申意义,也未尝不是关键之一。“风骨”之争似乎有类于此。
现在我们试就《文心雕龙》用字含义不同的不同类型,进而分析一下“骨”字的意义。
《文心雕龙》中用到这个字的,在上卷中有《宗经》《辨骚》《诠赋》《杂文》《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等篇,在下卷中有《体性》《风骨》《附会》《序志》等篇,一共有三十次左右。我们细细读了全书中用到这个字的全部文句,感觉到差不多有一半上下的场合,“骨”字只作为普通意义来使用,因而不能当作专门术语来理解。
且看下列几个例子:
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
甘意摇骨体(唐写本作“骨髓”) ,艳词动魂识。(《杂文》)
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太平御览》卷五九七引作“曝露”)矣。(《檄移》)
吹毛取瑕,次骨为戾。……虽有次骨,无或肤浸。(《奏启》)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风骨》)
这几个“骨”字,无论是和“魂”“肤”等字并举的,或者是单独使用的,都显然指人或鸟的骨骼,应该不致引起读者的误解。
在这样的场合,刘勰常常在“骨”字下加“髓”字或“鲠”字。连用“骨髓”两字的,有下列几个例子:
辞为肤根,志实骨髓。(《体性》)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附会》)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序志》)
这几个“骨髓”,能不能算专门术语呢?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它们之所以不能算术语,犹如“肤根”“神明”“毛发”等字不能算术语一样。这里作者只是拿人身上的骨骼作比喻,借以指事物的重要部分。因此,这几句里的“骨髓”二字所体现的意思,和“神明”相近,而和“肤根”“毛发”则刚刚相反,因为那是比较次要的事物(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卷六《体性》篇注二四说“肤根”当作“肤叶”)。
在这里,我们要附带指出三点:第一,如果我们拘泥于“事义为骨髓”一句,而认为“骨”字的专门意义就指文章的事义,那么我们对于“志实骨髓”一句,又将怎样理解呢?难道我们从这一句里再得出第二个结论,说“骨”字的专门意义又指文章的情志吗?第二,当“骨髓”和“神明”并用时,虽同指重要事物,但重要的程度却有区别。“情志”是作者蕴藏在内心而企图体现于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所以以“神明”(脑或心)为喻,显示比“骨髓”更重要。但是当“志”与“辞”对举时,便只须以“骨髓”喻“志”,就可显示比“肤根(叶)”更重要了。第三,全书中“骨髓”二字连用而能当作专门术语讲的,恐怕只有《宗经》篇中“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一句和《风骨》篇中“昔潘勖《锡魂》……乃其骨髓畯(峻)也”一句。这里所以在“骨”字下加一“髓”字,主要是为了和上文“洞性灵之奥区”及下文“相如赋仙……乃其风力遒也”相对称的原故。
连用“骨鲠”两字的时候,也常常不当作专门术语。全书中的例子如下: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树。(《辨骚》)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檄移》)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奏启》)
这里第一个例子拿“骨鲠”和“肌肤”对举,与上文所引《体性》篇以“骨髓”和“肤根(叶)”对举是同样的,也是借来比喻主要的和次要的事物,在这里只当作普通的字来使用,是非常明显的。其他两个例子中“骨鲠”两字的意义稍有不同,但是我们能否把那两句理解为“壮有事义”“事义得焉”呢?我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檄移》篇里,刘勰主要称许陈琳的“抗辞书衅”;而在《奏启》篇里,则主要说明东汉政治家的“嘉言罔伏”。不过我们也不能据“辞”“言”两字而说“骨即文辞”,因为这里实在不能当作专门术语。观《奏启》篇中以“博雅明焉”来和“骨鲠得焉”相配合,便知这里主要说明作家们的品学,而“骨鲠”则是比喻杨秉、陈蕃、陈琳的气骨高傲,借以赞美他们敢于向汉桓帝、曹操大胆指责,使他们的上疏和檄文能够写得一语破的,深中要害。
只有《风骨》篇的“蔚彼风力,严此骨鲠”中的“骨鲠”二字,才是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这里在“骨”字下加一“鲠”字,主要是为了足成四言的赞语,以便和上句“风力”相对称。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心雕龙》中所有的“骨”字都当作与“风”并举的专门术语,那么无论把“骨”理解为文辞,或理解为事义,恐怕都不大符合于刘勰的原意。在这些场合,干脆当作普通意义来讲,也许更合适些。
现在我们来探索一下作为专门术语的“骨”字的真正含义。廖仲安、刘国盈两同志《释“风骨”》说:(www.zuozong.com)
当以风骨论人的时候,风指神,骨指形。以风骨论人物画的时候,风指神似,骨指形似。以风骨论文的时候,风指文章的情态,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义,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骸骨。(《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第十页)
这一段结论性的说明,可以归纳为下列四条:
一、神→神似→情志二、形→形似→事义三、风→情志→神明四、骨→事义→骸骨
这里不免引起我一些疑问:第一,从人的神到画的神似到文的情志,这中间是有显著的联系的,但从人的形到画的形似到文的事义,其间的脉络就看不大清楚了。第二,以神明比喻风,是可以理解的,但以骸骨比喻骨,就有点古怪了,因为我们只能以甲喻乙,却不能以甲喻乙,却不能以甲喻甲。
以“骨”为事义之说,始见于十四年前刘永济同志的《文心雕龙校释》。他在卷上《风骨》篇的“释义”中说:
本篇所用名义甚多,如曰风、曰骨、曰气、曰采、曰情、曰意、曰思、曰辞、曰言、曰义、曰体、曰骸、曰力、曰藻、曰字、曰响、曰声、曰色。或比用,或互称,或迭说,或专论,纷纭满目,几虽寻绎其意旨。兹一一归纳而证释之如下:
舍人论文不出三准,已于《宗经》篇略论之。凡此诸名,统归三准,特以用异而名异,或以行文之邂复而名亦异。明夫此理,则名用虽繁,而条理自在。兹悉以三准归纳诸名如后:
凡篇中所用风、气、情、思、意、义、力诸名,属三准之情,而大要不出情思二者。
凡篇中所用骸、体、骨、言、辞诸名,属三准之事,而大要不出事义二者。
凡篇中所用采、藻、字、响、声、色诸名,属三准之辞,而大要不出声色二者。(第十五—十六页)
刘永济同志在这里所提的几项意见,有些是很好的:如说刘勰用字有比用、互称、迭说、专论等不同方式,如说《风骨》篇与《镕裁》篇的“三准”有联系,等等。不过我觉得如果把所有术语都一一分配到“三准”里边去,似乎不必。因为刘勰在提出“三准”之后,接着就说“然后舒华布实”,可见“三准”乃是预备工作,并不能包括创作过程中的一切环节。同时,以“骨”比附“三准”中的“酌事以取类”,也是颇有商榷余地的。
在“骨”的解释上,我觉得黄侃的“风即文章,骨即文辞”之说仍有参考价值。他的话虽不够圆满,但指出“风”属内容方面,“骨”属形式方面,却值得注意,这样和论人论画的“骨”,就显出前后脉络相承。而且《文心雕龙》中如《情采》《镕裁》《附会》等篇,都是就内容与形式进行分析,连标题两个字本身也都分别指这两方面。当然“骨即文辞”的结论还可以稍作修正。在这一点上,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注》卷六《风骨》篇的注四里有一段话说: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
这一段很可以补足黄侃原来解释不够圆满的地方。
《释“风骨”》痛驳黄侃,而于范、刘二同志之说一字不提。实际上,《释“风骨”》是申刘以驳范。我现在却有点信范而疑刘。
我的主要根据是《风骨》篇本身。试看这一篇中有关“骨”字的文句:
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昔潘勖《锡魂》,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畯也。
我想任何不抱成见的人,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骨”是文辞方面的最高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正面是“端直”、是“精”,反面是“肥”。更明显的是,刘勰在这里举了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做具体的例证。这篇文章在“事义”方面有什么出色呢?比较特殊的还是在文辞的“端直”上,尤其是作者学习典诰的语言,因而才引起刘勰的欣赏。范文澜同志在《风骨》篇注九说:
其事鄙悖而文足称者,练于骨之功也。……“畯”是“峻”之误。
“峻”是高的意思。如果说这篇文章之所以被赞美,是由于“事义”高明,恐怕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刘勰是否有撇开内容而孤立地谈论文辞的倾向。刘勰对于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是一贯十分明确的。在这里举“事鄙悖而文足称”的文章做例子,不过为了突出自己在文辞方面对作家所提出的特殊要求而已。
在《风骨》篇中,还有些地方是“风”和“骨”连用的文句,如: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蔚彼风力,严此骨鲠。
这里常常以“风骨”和“采”并举,因此引起怀疑:如果“骨”指一切文辞,为什么另外再说什么辞采呢?其实这只说明黄侃说法的不够圆满,但看了范文澜“推明”的话,就可以恍然大悟。既然“骨”并不指一切文辞,而只指“辞之端直者”,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和“采”并列呢?我们上文曾说,“骨”代表刘勰对于辞的最高要求,而“采”却显然不包括在这个最高要求之内的。刘勰对于“采”并不忽视,但只予以适当的重视,而不给它过高的地位。这个正确的主张,是贯彻在《文心雕龙》全书之中的。所以“风骨”与“采”并列,不但不能推翻范文澜同志之说,反足以证明他的“推明”的恰当。
《风骨》篇以外,“骨”字当术语使用的例子,还有下列文句:
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封禅》)
表以致禁,骨采宜耀。(《章表》)
而谀(《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作“腴”)
辞弗剪,颇累文骨。(《议对》)
“掣”训“制”(《释名·释姿容第六》说,“掣,制也,制顿之使顺己也”) ,要“掣靡密”和要“剪”“谀(腴)辞”的用意是相同的,都是因为不符合于“端直”的要求。而“骨”和“辞”“采”并举,则与《风骨》篇里以“风骨”和“采”连用完全一样,不烦赘说。这些例子一方面可以助证范文澜同志“推明”黄说的必要和正确,一方面也可看出“骨”不能指“事义”。因为在《封禅》《议对》等篇里牵涉到的具体作品,如扬雄的《剧秦美新》在“事义”上是无可称许的,而陆机的文章的主要毛病之一就是文辞不能“端直”。
不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作为专门的术语用的“骨”字,除具有基本意义(“辞之端直者”)以外,还有引申意义。例如下列文句:
洞性灵之奥区,即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
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檄移》
树骨于典训之区,选言于宏福之路。(《封禅》)
这里所谓“骨”或“骨髓”,即不专指作品的文辞端直,也不专指事义,而是泛指作品的主要因素或特征之类。所谓“极文章之骨髓”,就是充分理解或彻底掌握了写作的最根本的东西;所谓“有移檄之骨焉”,就是说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一篇具有檄文最主要的特征;所谓“树骨于典训之区”,就是把文章的主要之点放在儒家经典的学习上。这一个引申意义和上文所说“骨”字的普通意义有一定联系,不过那是用普通的骨骼来作比喻,借指某一重要事物,而这里则直接以“骨”作为作品本身的主要成分了。
总起来说,《文心雕龙》中用字有普通意义与专门意义的区别,而专门意义中又有基本意义与引申意义的区别。“骨”“骨髓”“骨鲠”等字的普通意义与引申意义的区别。“骨”“骨髓”“骨鲠”等字的普通意义是骨骼或气骨,其专门意义中的基本意义是“辞之端直者”,也就是刘勰对于文辞的最高要求(不是指一切文辞) ,其引申意义是泛指作品的主要因素或特征。这种解释不一定恰当,渴望读者指正。
(原载《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