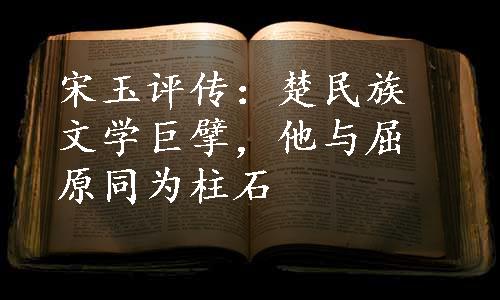
(公元前二九〇?年——公元前二二二?年)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杜甫《咏怀古迹》
宋玉——他与屈原同为楚民族文学的柱石。但是,二千年来,好像不曾有过一篇正式的传记,也不曾有过一篇专治他的作品的论文。所以这篇《评传》一方面传其生平,一方面评其作品,大约这是这种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现在我们先叙一叙楚民族及其文学的略史,先明白产生宋玉的是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地方。
楚民族在古代史上,似乎是个独立的民族。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未有科学上的证据诏示我们以前,自难妄下断语。然而我们从古代各种记载上推测下来,楚与周似无固定的君臣关系。中原诸侯对楚多存歧视之心,称楚多称“蛮夷”。我们随便举出《国语》上的几个例子:
(荣伯成劝鲁襄公别以楚师伐季氏说)若不克,君以蛮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获矣。(《鲁语》下)
(栾武子向范文子说)今我任晋国之政,不毁晋耻,又以违蛮夷重之!〔韦注〕蛮夷,楚也。(《晋语》六)
(叔向同赵文子说)楚为荆蛮,置茆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晋语》八)
(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注〕荆蛮,芊姓之蛮,鬻熊之后。(《郑语》)
(夫差向董褐说)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楚、秦。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吴语》)
(董褐对夫差说)今伯父有蛮荆之虞,礼世不续。(同上)
(董褐对夫差说)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 (同上)
这几个例子已够证明周人视楚为外国了。此外,楚国国情与别国迥异者,更是不胜枚举。就官制言:
楚官多以尹为名。(《左传·庄公十八年》疏)
陈、楚名司寇为司败。(《左传·文公十年》注)
我们若看顾复初的《列国官制表》,便知楚国特有的官职多着呢。又就言语言:
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左传·宣公五年》)
此外见于扬雄《方言》者尚多。方言不同自然不能就说是异族,然卫聚贤先生说西藏谓奶为谷,李济之先生说苗氏谓虎为于菟,那我们也可推想这确是与中原迥异的语言。又就服饰言: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左传·成公九年》)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国语·周语》中)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国策·秦策》五)
《左传》《国语》都注道:“南冠,楚冠。”《汉官仪》又说即汉之解豸冠,秦灭楚后以赐近臣,其特异可知。《国策》旧注以“楚服”为“盛服”,实误;观下文“吾楚人也”句,便知“楚服”犹言“胡服”。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知道楚民族是一个与中原不同的民族。
我们研究宋玉而推论及此,似乎词费。但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总该知道最难解决的便是屈、宋问题:这样震古烁今的大诗人,为何偏生于文化最迟的楚?如果我们把楚当作周天子属下整千诸侯国之一,这个问题自然难答。如果我们知道楚是一个与周为敌体的民族,则这一点便不成问题了。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楚文学的人,所当牢记在心头的。
这个新民族起源的历史,我们不很知道。一来因为代久年湮,书阙有间。一来因为楚民族强盛后,要依附于中原的正统。《史记·楚世家》所载黄帝到鬻熊的世系,当然不可靠,不过成王封熊绎于楚,事或有之。迟起的新民族常有受早兴的旧民族之封的,如辽之于宋,清之于明然。当时长江流域一带大约是很荒芜的,如楚大夫析父追叙道: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世家》)
其实这也不过是句门面话,他们并不甘心“事天子”。熊绎五传至熊渠,在夷王时甚得江、汉间民心,版图渐渐扩张到庸、鄂、扬、粤等处。他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 (《楚世家》)
遂封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熊渠十二传至熊通(与平王同时) ,命随人代请周天子尊楚未允,怒道:
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楚世家》)
于是自称为武王。这是楚民族向周民族宣告独立的正式表示。武王以后,日益强盛;四传至庄王,观兵问鼎,不可一世。当时周民族属下的诸侯,如息、谷、蔡、邾、申、邓、黄、 、赖、萧、徐、江、舒、弦、道、英氏、项、顿、毛、鄀、夔、庸、舒蓼、唐、舒庸、胡、许、陈、杞、吕、小邾、贰、罗、权、聃、蒋、沈、六、麇、不羹、房、*、郧、轸、绞、州、蓼、巢、柏、舒鸠、吴、越、鲁以及庐戎、群蛮、戎蛮、蛮氏等,无一不先后并于楚。故东周之世,实是楚民族的全盛时代。其版图之大,几包括现在的长江流域七省及山东、河南之半,而周民族则仅河北、山西、陕西三省与山东、河南之半而已;不但可以分庭抗礼,实有驾而上之之势。
、赖、萧、徐、江、舒、弦、道、英氏、项、顿、毛、鄀、夔、庸、舒蓼、唐、舒庸、胡、许、陈、杞、吕、小邾、贰、罗、权、聃、蒋、沈、六、麇、不羹、房、*、郧、轸、绞、州、蓼、巢、柏、舒鸠、吴、越、鲁以及庐戎、群蛮、戎蛮、蛮氏等,无一不先后并于楚。故东周之世,实是楚民族的全盛时代。其版图之大,几包括现在的长江流域七省及山东、河南之半,而周民族则仅河北、山西、陕西三省与山东、河南之半而已;不但可以分庭抗礼,实有驾而上之之势。
以上略述楚民族由小而大的历史,由此便知它的地位实最宜于文学的发展。一切大山,一切大水,几乎全在它的范围以内。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序例》里说:
楚,泽国也,抑山国也。其南沅、湘之交,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嶔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秦□江□□,皆此为之也。(侃按:原文“抑山国也”句在“其南沅、湘之交”句下,文意不贯,疑筒错,特移正。末句脱误不可读。)
文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很大的,所以楚民族的版图若永远不扩大,则它便不能成一独立的团体,大诗人也不会产生于它的境内,而它的历史也永远不能在这里占篇幅了。而且因为陈、吴、越等国并入版图,楚民族的文学又得到一种滋养料。这便是“巫风”。《汉书·地理志》述陈国的风俗道:
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匡衡传》也说:
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当时吴国地名也常有用“巫”字的。如《越绝书》:
巫门外冢者,阖庐冰室也。
巫 城者,阖庐所置。
城者,阖庐所置。
越国亦然:
巫里,句践所徙巫为一里。
巫山者,越 福——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福——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这可见当时“巫风”之盛。《商书》说明巫风的内容为“酣歌”“恒舞”二种,这二种都是文学起源的原动力。我们看了楚文学的发展,便可认识楚君扩张版图的重要了。
楚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与它的国势的强盛是平行的。见存作品之最早者为东周初年的“二南”。这与旧说相差太远,故我们虽不能在此处详细考证,然也有略加说明的必要。第一,我们知道“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原来“二南”是《诗经》的一部分,列入“十五国风”内。然自王质、程大昌以来,学者们大都承认“二南”的独立,承认它与《风》《雅》《颂》并列为四。第二,我们知道“二南”是东迁后的诗。旧说附会到文王身上去,然自魏源、崔述等人辞而辟之,学者们大都承认“二南”非西周诗;至于《何彼秾矣》之称“平王”,更是的证了。第三,我们知道“二南”的产地是楚。诗中言及的地名有江、汉、汝、河、南等,可见这几篇的确是今河南、湖北二省的作品,均在楚民族辖境内。根据上列三条,我们说“二南”是楚文学的始祖。崔述说:
盖其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读风偶识》)
“南方”之意义如何?
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说文》“南”下)
南方者,任养之方,万物怀任也。(《白虎通·五行》)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御览·时序部》六引《书大传》)
我们知道“南”“任”二字古通,“任”即“孕”字,有生长发育之意。所以“南”字同时也可代表“二南”的风格。章潢说得好:
诗之在“二南”者,浑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温柔之气,如南风之融物,而物皆畅茂。凡人之听其言者,不觉其入之深而感化育于其中也。
这一点便增高了“二南”在《诗经》中的位置。孔子曾再三恭维: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阳货》)
这实在是独具只眼。楚文学既有超越的“二南”作根底,则后来产生震古烁今的《楚辞》也何疑!
被后人称为《楚辞》的几十篇中,以《九歌》为最早。在“二南”与《九歌》之间,各种古籍里还零零星星地记载着几篇诗歌。固然有些不甚可靠,然即就西汉以前书所载的而言,尚有七篇,差为可信:《说苑》载三篇,《新序》《论语》《孟子》《左传》各载一篇。《说苑》所载三篇的时代最早。一为《子文歌》,见《至公》篇;一为《楚人歌》,见《正谏》篇。这两篇都是公元前七世纪后半期的作品,与“二南”差不多同时,所以形式方面完全与《诗经》一样。《子文歌》是一篇很呆板的四言诗,技术很拙劣。《楚人歌》分二章,只换韵,不换意,极似“二南”中的《麟趾》《甘棠》《驺虞》等篇,虽有些咏叹的意思,然终非佳构。在它们略后些(约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 ,便有一篇极佳的《越人歌》出世,也是《说苑》所载,见《善说》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译诗,与汉唐菆《莋都夷歌》及北朝高欢《敕勒歌》同为难得的名作。就技术上看来,它进步得多了。它的词句异常秀美,表情异常婉转。全篇体裁与屈、宋之作极相近,故更可注意。与这篇同时的是《徐人歌》,见《新序·节士》篇。全篇仅两句,是中国古代小诗之一,然命意浅显,乏婉转之致。但我们由此可知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楚民族的诗歌已完全脱离《诗经》的体裁,而另觅新的路径了。故屈、宋的成功是《徐人歌》《越人歌》两篇引出来的。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初年,又有三篇诗歌流传下来。其中有两篇是孔子在楚国所听见的。一为《接舆歌》,见《论语·微子》;一为《孺子歌》,见《孟子·离娄》。前一首表现南北思想的冲突,故《庄子·人间世》也载它,不过字句略有不同。后一首与《渔父》所记的歌词一样,我们尤当注意。还有一篇是《庚癸歌》,见《左传·哀公十三年》。这是一首讽刺诗,讥夫差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该诗形式方面与《孺子歌》一样,共四句,一、三句末有“兮”字,二、四句末用韵。《离骚》《九辩》大都四句一节,即是从这两首诗歌学来的。——这是楚文学从《诗经》变到《楚辞》的历程。
现在我们要谈《九歌》了。《九歌》之为屈原以前的民间祭歌,是二千年来学者的公论。只因王逸觉得这样便与屈原没有关系了,于是便说是经过屈原的润饰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不了了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九歌》产生年代必在公元前四八九年至公元前四〇三年之间,与屈原当然没有关系(《左传·哀公六年》说楚昭王不祭河,而《九歌》的《河伯》却是祭河的;昭王卒于公元前四八九年,故知《九歌》必作于此年以后:可参看拙编《楚辞》卷首《引论》。《曲礼》孔疏,《春秋正义》及《玉海》均言战国时通行骑战,而《九歌》的《国殇》仍言车战;战国始于公元前四〇三年,故知《九歌》必作于此年以前:可参看陈斠玄先生《楚辞各篇作者考》)。所以《九歌》的作者大约是一位(或几位)公元前五世纪的无名诗人。他(或他们)一定是平民而非贵族,因为《九歌》中言情分子占多数,与《周颂》及《郊祀歌》绝不相同,而与六朝乐府《神弦歌》却完全一样。《神弦歌》是民间的祭歌,没有贵族的祭歌那样庄重严肃,故有“郎艳独绝”“独处无郎”之句。我们拿各时代的各种祭歌来比较研究,便知《九歌》确为民间的祭歌了。全体包含十一篇,前十篇祭十个神,末一篇为前十祀所通用的“送神之曲”,恰如《离骚》之“乱”,《抽思》之“倡”,《佹诗》之“小歌”,《远游》之“重”,《九叹》之“叹”(此说为王船山所发,丁山阳、王壬秋及梁任公先生等都附和他)。就文学的艺术方面说,《九歌》有三种特点:一是词句非常秀美,一是理想非常高洁,一是表情非常真挚。这三个特点也可说是《楚辞》共有的特点。表情之真挚固为一切杰作所必具,然词句之秀美与理想之高洁,历代作家很少能比得上楚民族的诗人的。《九歌》对于楚文学的最大贡献即在此。我们当知楚文学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固有待于屈、宋之发挥光大,而《九歌》实开其端。屈原喜欢用美人、芳草之名,未始非《九歌》之所启示;故他写其忠君之思,而我们却不觉其酸腐。又如宋玉《招魂》之铺张扬厉,也可说是从《湘夫人》“荪壁兮紫坛”和《东君》“ 瑟兮交鼓”二段上学来的。总之,在《九歌》以前的作品如“二南”等,还未脱周民族文学的格式。《越人歌》以后方有新的发展,然皆零章断句,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也不是最成熟的作品。故楚民族文学开创的始祖终要推《九歌》。
瑟兮交鼓”二段上学来的。总之,在《九歌》以前的作品如“二南”等,还未脱周民族文学的格式。《越人歌》以后方有新的发展,然皆零章断句,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也不是最成熟的作品。故楚民族文学开创的始祖终要推《九歌》。
楚文学有了“二南”、《九歌》等丰厚的遗产,于是产生大诗人屈原。他一生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然因许多学者竭力研讨的结果,我们的智识渐渐地丰富了。简言之:他名平,字原,小名正则,小字灵均,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楚顷襄王九年(公元前二九〇年)左右。他是楚之贵族,幼年受充分的教育;“学而优则仕”,曾做过怀王时的左徒及三闾大夫。然而谗谄蔽明,方正不容,故一放汉北,再逐江南;深林杳冥,霰雪无垠,独处荒徼,郁郁寡欢,遂以五月五日自沉于汨罗。他的性格适得中庸之反——他既“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故在政治上大失败,在文学上大成功。这个因果关系的消息,我们可在他的作品中参透。他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二十五篇,然以存者考之,至多只有《离骚》《天问》及《九章》之半差为可信,余均后人拟作(参看拙编《屈原》卷首《评传》及《楚辞》卷首《引论》)。然即就《离骚》言,便是古代诗坛上唯一的抒情杰作。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优越的位置,是不用怀疑的。他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在他以前,无论是周民族或楚民族,许多诗歌的作者大都是无名氏;即幸而姓名未失传,其作品至多不到一百句,所以我们不易看出全部作品风格的真面目,作者的个性也没有深刻的表现。有之,自屈原始。二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二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作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从他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直到最近翻译西洋诗还应用他的体裁。“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二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竞渡角黍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令节,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一种福气,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
自他以后,楚民族的文学空气陡然浓厚。流风所被,遂产生一大群诗人。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汉志·诗赋略》载唐勒赋四篇,说是“楚人”;宋玉赋十六篇,说是“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景差赋未著于录,《古今人表》则有“景瑳”之名(“瑳”与“差”通) :此三人皆彰彰可考。不过景差之赋既亡于班固之时(朱熹以《大招》为差作,实误) ;而唐勒赋四篇又亡于王逸之时(因《楚辞章句》不载) ;只有宋玉的作品尚有存者,所以前人对于《楚辞》常以屈、宋并称。如以词喻之,“二南”如古乐府,《九歌》如唐五代小令,而屈、宋则南北两宋也。我们研究楚民族文学的人,于研究屈原之后,不可不连带研究研究宋玉。
怆怳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宋玉《九辩》
现在我们要替宋玉的生平做一个详细的叙述。如上文所说,这种工作是二千年来第一次的尝试。而且,我们对于宋玉的事迹也知道得太少。如今姑就我所知道的唐以前关于宋玉的记载,杂抄二十余段于后,以供参阅:
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楚相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能于我?”宋玉曰:“不然。昔日,齐有狡兔,尽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见指注,虽良狗犹不及狡兔之尘。若摄缨而纵绁之,瞻见指注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侃按:此为见存的宋玉传记材料之最早者。末段宋玉答语不甚可解,似有阙文。)
——《韩诗外传》卷七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楚威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邪?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鲸:凤鸟上击于九千里,绝浮云,负苍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粪田之 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侃按:《文选》所载《宋玉对楚王问》与此相似,不过“威”作“襄”,“邪”作“与”,“《阳陵》《采薇》”作“《阳阿》《薤露》”,“引商刻角”作“引觞刻羽”,“鲸”作“鲲”,“粪田”作“藩篱”。)
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侃按:《文选》所载《宋玉对楚王问》与此相似,不过“威”作“襄”,“邪”作“与”,“《阳陵》《采薇》”作“《阳阿》《薤露》”,“引商刻角”作“引觞刻羽”,“鲸”作“鲲”,“粪田”作“藩篱”。)
——《新序·杂事》第一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 ,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绁,则虽东郭
,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绁,则虽东郭 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绁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侃按:此条与《韩诗外传》相同,而文气较完备。)
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绁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侃按:此条与《韩诗外传》相同,而文气较完备。)
——《新序·杂事》第五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划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猿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慄,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势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
——《新序·杂事》第五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楚辞章句·九辩序》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
——《楚辞章句·招魂序》
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歌以永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
——傅毅《舞赋》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曹植《洛神赋》
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若东郭狻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韩卢之口;然在猎者耳。夫遥见而指纵,虽韩卢必不及狡兔也。若蹑迹而放,虽东郭狻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于王,为遥指踪而不属耶?蹑迹而纵绁耶?”友谢之,复言于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绝伦赴曲,国中属而和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也。”(侃按:此段似删改《新序》之文而成者。)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望朝云之馆。上有云气,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宋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昔者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暧乎若云,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浮如停,详而视之,西施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实为 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侃按:今本《襄阳耆旧记》无此条,引见《太平御览》卷三九九。《渚宫旧事》卷三所引与此略异。)
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于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侃按:今本《襄阳耆旧记》无此条,引见《太平御览》卷三九九。《渚宫旧事》卷三所引与此略异。)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侃按:自此以下至《高唐对》,旧说均认为宋玉自作,其实均系后人伪托,详下文。)
——《文选·风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
——《文选·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
——《文选·神女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文选·登徒子好色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侃按:此与上文《新序·杂事》第一所记相近,可参阅。)
——《文选·对楚王问》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
——《古文苑·大言赋》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
——《古文苑·小言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
——《古文苑·讽赋》
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钓者也,愿王观焉。”……宋玉进曰:“今察玄洲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
——《古文苑·钓赋》
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激楚》《结风》《扬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侃按:此实删改傅毅《舞赋》而成,参看上条。)
——《古文苑·舞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望朝云之馆。有气焉,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此是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侃按:此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拟潘黄门《悼亡》”李善注引《宋玉集》,与《渚宫旧事》《太平御览》所引《襄阳耆旧记》相似。)
——《高唐对》(侃按:此题乃严可均所加。)
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友人。友日:“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也。”(侃按:此见《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引,作者失名。)
——《宋玉集序》
据我的浅薄的学问,唐以前关于宋玉的记载似乎尽于此了。
我们看了上列的记载,便知道下列几件事:
(1)他是楚鄢人,冢在宜城。
(2)他与楚威王相问答。
(3)他为怀王小臣。
(4)他事襄王而不见察。
(5)他与襄王游云梦、高唐、兰台等处。
(6)他曾为楚大夫。
(7)他见楚相而待之无以异。
(8)他是屈原、玄洲、景差的弟子。
(9)他与唐勒、景差、登徒子同时。
(10)他识音,以赋见称,存十六篇。但是,这几件都是事实吗?且不说别的,即就年代而言,威王于公元前三三九年即位,襄王卒于公元前二六二年,他既历事威、怀、襄三朝,其年龄几在一百岁以上。则我们对于这些史料,应分别审定其真伪也明甚。
我以为现在对于宋玉的事迹与年代,只能大约假定一下。第一,我们先讨论年代的假定。这当以《招魂》的年代为中心,因为在宋玉的一切事迹中,只有这一点是比较的有物观的证据的。宋玉作《招魂》在哪一年呢?我从前在《屈原评传》里曾有一段考证,今录于下:
原文的乱辞里有这几句:“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庐江即今之青弋江,在安徽东南部(李兆洛说:“《汉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注:‘在歙县东,浙水出焉。’按:陵阳在今池州府石埭东北二里;庐江与浙江同出一山,浙江东流入海,庐江北流入江。然则庐江即今青弋江也。”读者可参看《李氏五种》内《地理沿革图》的附注,杨守敬的地图即从此说)。至于“南征”二字,前人大都以屈原放于江南来附会,却是大错的。原文下段里有这几句:“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此外还有许多叙打猎的话,可见这实在指国君自国都出行到南方打猎去(我想当时必有一楚君南猎不返,词臣哀之,为作此篇;惜古代记载存者极少,无从质证耳)。这一点便可证明《招魂》的出世不会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今先把楚国国都的地点和时期列表于下:
(一)顷襄王二十一年以前——郢都——即今湖北江陵。
(二)顷襄王二十一年至考烈王十年——陈城——即今河南淮阳。
(三)考烈王十年至二十二年——钜阳——即今安徽阜阳。
(四)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后——寿春——即今安徽寿县。
江陵恰在青弋江之正西,显然不合乎“南征”二字;淮阳与阜阳都在青弋江之西北,方向是合的,但距离太远;寿县也在其西北,方向已经合了,而距离又很近;故我以为《招魂》必作于徙都寿春后,方合于原文里的叙事。照此看来,他的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四一年)以后了。
假使他生于屈原自沉的一年(公元前二九〇年,参看我的《屈原评传》) ,到作《招魂》时年约五十左右。到楚亡时(公元前二二二年) ,他年已近七十,大约就死于此时了。这个生卒年代的假定,自然是纯粹根据常理来推测的,毫无其他佐证。然而与上列两种正史的记载——一是《史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一是《汉书》“宋玉……楚人……在屈原后也”——是非常符合的。那么他与威王、怀王有君臣关系,与屈原有师生关系,很易知道是后人的捏造了。至于他和襄王的关系,也不会像传说那么密切,因为到襄王末年他尚未满三十岁,而《高唐》《神女》等赋又是后人伪托的(详后)。
第二,我们再讨论事迹的假定。这一点可从《九辩》里钩出一些材料来。虽然《九辩》中有许多是模拟屈原的(见下文) ,然尚有大部分是宋玉自己的经历,较后人所记当为可信。这些可信的材料是:
怆怳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去家离乡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去家离乡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
从这二十几句里,我们知道宋玉是楚国乡下的一位贫士,远走京邑,谋一个位置,以图温饱。不料就职不久,便失职了,于是便潦倒终身。上文所谓“失职”的职,大约即《宋玉集序》所谓“小臣”,是否即王逸所说的“大夫”则不可知。做“小臣”是在哪一年呢?这里我们不能连带把宋玉作《九辩》的年代考定一下。这一种考定是很困难的,现在只能根据《九辩》的内容来推测。例如上列几句便可给我们许多暗示。不过诗句常有不可拘泥的,如《离骚》说“老冉冉其将至”,其实屈原那时年仅三十;又如《惜誓》说“惜余年老而日衰”,其实贾谊死时也只三十余岁。所以我们至多只能说《九辩》作于宋玉中年,年三十至四十岁(公元前二六〇年—公元前二五〇年)之间。他作“小臣”的年代,大约与荀卿至楚为兰陵令时(公元前二五五年)相近。
总之,关于宋玉的生平,只有下列几点我们认为是差近事实的假定:
(1)他生平与屈原卒年相近。
(2)他与威、怀、襄三王无君臣关系。
(3)他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
(4)他做过小臣,与荀卿仕楚时相近。
(5)他不久失职,作《九辩》。
(6)他作《招魂》当在楚徙都寿春以后。
(7)他穷得很。
(8)他卒年与楚亡时相近。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宋玉《招魂》
宋玉的作品的总数,我们现在无从考知。据《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他有赋十六篇,并未说及散文的著作。现在所存者,连真与伪,赋与散文合计仅十四篇。
王逸的《楚辞章句》载二篇:
(一)《九辩》;
(二)《招魂》。
萧统的《文选》载五篇:
(三)《风赋》;
(四)《高唐赋》;
(五)《神女赋》;
(六)《登徒子好色赋》;
(七)《对楚王问》。
无名氏的《古文苑》载六篇:
(八)《笛赋》;
(九)《大言赋》;
(十)《小言赋》;
(十一)《讽赋》;
(十二)《钓赋》;
(十三)《舞赋》。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时,扬去《舞赋》而加入一篇:
(十四)《高唐对》。
依我看来,只有《楚辞章句》里的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余十二篇都有伪托的嫌疑。对于这种嫌疑,我们在后边另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先就我认为真的二篇加以研究。
我们先研究《九辩》。
《九辩》与《离骚》同为古代诗坛上长篇的抒情杰作。通行本都因题名“九”而擅分为九章,亦有分为八章或十一章的,列表如下:
这种分章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这二百几十句合成一篇整个的长诗。理由有二:第一,全篇的“母题”不外因悲秋而发生身世之感,不如《九歌》每篇各祀一神;第二,《九歌》各篇另有标题,如《东皇太一》《云中君》等,而《九辩》则无之。所以我们主张取消分章。
《九辩》中感怀身世的诗句,有两种来源。第一是他自己的境遇,可以从古代记载里考知的。这一点,我们在上边已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必赘叙了。第二是屈原作品的影响。屈原在当日负有很大的声望,而他的自杀尤其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心和崇拜心。故他的作品一定是很通行的,宋玉自然不能不受他的影响。这一点,只看宋玉作品中抄袭屈原文句之多,便可证明了。今试把宋玉抄袭的地方和屈原的原文做一对照表于下,以便读者:
由此可知这两位大诗人相互的关系是很深的,并可证明宋玉对于他的乡先辈是很崇拜的。
然而就在这些题材与屈原相近的地方,宋玉也能解开屈原的束缚,而努力说自己的话。例如: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家离乡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
又如: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
又如:
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
从这些“自己的话”,我们很可窥见他和屈原不同之处。屈原是刚强的、激烈的。他遇着不如意的事,便说: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离骚》)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涉江》)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怀沙》)
这种高亢而近于咒骂的语气,在宋玉作品里是找不出的。他只有饮泣吞恨的无可奈何的话。所谓“温柔敦厚”,所谓“怨而不怒”,自然在此而不在彼。这是因为屈原是楚之同姓,休戚相关,突然被谗去职,远逐江、湘,自然悲愤不能自已;宋玉却是个穷乡僻壤的贫士,间关跋涉,谋个温饱,不料不能如愿,所以发之于诗歌。一个是失败的政治家,一个是落魄的文人。懂得了这个分别,方能了解《九辩》的内容,方能认识《九辩》的技术。
然而我们最该注意的是《九辩》中“悲秋”的部分。这是他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分,“宋玉悲秋”竟变成文学上的习语,亦可见他的魔力之大了。例如: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王夫之称这几句为“千秋绝唱”。这种“悲歌可以当泣”的气概,真是“千秋绝唱”。他又唱道: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雝雝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
在秋天的自然界里,他找得了自己,他了解了自己的命运。蟋蟀的哀鸣、鹍鸡的啁哳,变成了他的葬歌;草木的摇落、明月的销毁,变成了死神的启示。屈、宋并称至今,岂是偶然!
最后,我们讨论此诗的音节。我们分两方面去说明。第一是双声叠韵字。例如: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这几句几乎字字都有声韵上的关系。此外如“萷 椮”“形销铄”“中憯侧”以及“凄怆”“增欷”“从容”,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第二是重文。例如:
椮”“形销铄”“中憯侧”以及“凄怆”“增欷”“从容”,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第二是重文。例如:
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躣躣,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轾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
这两点都能使《九辩》的音节异常和谐,异常铿锵。
其次,我们再研究《招魂》。
《招魂》是古代诗坛上长篇的白描杰作,正如《离骚》《九辩》为抒情杰作一样。作者抓住了“招魂”的题目,恣意地描写一切可悲可怕可喜可悦的境地,衍成近三百句的长诗。旧说都误认为招屈原的魂,故处处附会到放逐上去。(朱熹又说招魂本死后之礼,“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如果屈原活到《招魂》产生之时,他年已一百多岁了!)我以为“招魂”即我乡所谓“叫火”。譬如有人病了,家人以为他的“火”(魂)吓散了,便由最亲近的人在夜深幽静之时,喊着病人的名字道:“某人归来!某人归来!”若病势严重,便特请巫觋为之,口中唱着有韵的词句。王逸说: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楚辞章句·招魂序》)
这尤其与我乡风俗吻合,因为“叫火”时也是以手做招徕的姿态的(家人“叫火”常手执扫帚,巫觋则另持别的器具)。听说这种风俗,北方便叫做“招魂”(“招”“叫”叠韵,“魂”“火”双声)。宋玉所作,疑即这一类巫觋所唱的歌词(楚民族“巫风”本盛) ;与荀卿依“送杵声”来作二百八十句的《成相辞》,是同样的情形。
全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不能复用”。这是全篇的引言,述招魂的原因的。起六句是借托被招者自述的话(被招者究竟是谁,我们无从考知;前人以为招屈原,是大错的。参看上文论《招魂》时代的一节,及下文论第三大段的一节)。接下便述上帝和巫阳的谈话,商议招魂的事: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谢之,不能复用。”(www.zuozong.com)
这段不是《招魂》精彩之处,但用神话来引到招魂上去,颇饶别致,似胜于《大招》那种直率的无味的叙述。
第二大段自“巫阳焉乃下招曰”至“魂兮归来,反故居些”。这是招魂的本文。这大段又分二小段。第一小段至“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止。这是分述楚国以外各处的危险,叫灵魂别混走。这描写共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天”“幽都”六部分,大都是近于神话的。例如描写南方道: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又如描写天上道: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纵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这些描写大约根据古代楚民族的传说,或者加上些作者自己的想象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屈原的作品的影响。《九辩》的来源是《离骚》,《招魂》的来源却是《天问》。第一,《离骚》中虽也有羲和、飞廉、丰隆等神,但都是有人性的,屈原能和他们相周旋;《天问》里的却都是怪物,正与《招魂》相同,例如: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第二,《招魂》字句常有与《天问》相同的,如“雄虺九首”“长人千仞”之类。第三,《天问》每句大都四字,《招魂》亦然。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从“魂兮归来,入修门些”起。这是分述楚国以内各种娱乐,叫灵魂快些归来。归来有精致的房屋: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屋,夏室寒些。
屋内有漂亮的陈设:
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
屋外有悦目的风景:
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
还有讲究的饮食: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粔籹蜜饵,有
 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还有妙龄美女来歌着舞着:
姱容修态, 洞房些;蛾眉曼睩,目腾光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
洞房些;蛾眉曼睩,目腾光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
还有种种消遣的把戏:
篦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
这种描写影响后世辞赋者至深。好的方面是铺张。无论哪一种描写总是“琐陈缕述,务穷其变态”(孙鑛语)。坏的方面是堆砌。他们的描写既是多多益善,所以最易犯这种毛病。几十个山名、水名、鸟兽名、花木名,莫名其妙地堆在一起,是辞赋家之通病。这种毛病之见于《招魂》——尤其是第二大段中的第二小段——者如下:
秦冓齐缕,郑绵络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
这几句里,名词似嫌太多。然而,小疵不掩大醇,像这样长篇的淋漓尽致的描写诗,总归是难得的杰作。在三千年的中国诗坛上,简直找不到第二首。我思索了许久时候,勉强举出《小雅》里的《宾之初筵》来相配,然而总觉得有些配不上;因为它夹杂了许多惹人生厌的议论,而《招魂》却是纯粹的描写。《豳风》的《七月》或者胜于《宾之初筵》,但它却与六朝乐府《月节折杨柳歌》同于描写田功之外兼有叙事抒情的分子。总之,你想在过去诗坛上找一首与《招魂》相似的诗,你一定要遇到失败的。在这里,我不能不向宋玉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一个纯粹的白描的唯一的杰作——《招魂》。二千年来的读者只知崇拜那伪托的《高唐赋》与《神女赋》,而不能赏识这篇“万中无一”(周德清语)的《招魂》,岂非怪事!
第三大段自“乱曰”至“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全篇的总结束,述国君自国都南行打猎之事;表面上似与招魂无关,其实即招魂之本事。什么“本事”?即我上文所说:“必有一楚君南猎不返,词臣哀之,为作此篇。”我又说:“惜古代记载存者极少,无从质证耳。”这一点,常有朋友们说是我的“臆说”。但是《国策·楚策一》明明有这么一段记载: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
这可与下列几句对看: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蒸……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这里情景之迫近,词句之类似,是很显然的。《楚策》下文有这样一段谈话: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
我们不能说这段谈话与《招魂》有何直接启示,也不是说这段记载便是《招魂》的本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上文所推测者并非纯粹的想象,是有成为事实的可能的。宋玉加这段乱辞,似有深意。我最爱末三句,以为非此不配结束这篇伟大的作品: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最后,我们再研究宋玉作品的韵式。
《九辩》的韵式共七种,《招魂》的共九种。其中有三种是它们所共有的,故实得十三种。三句成节的有一种:
四句成节的有四种:
五句成节的也有四种:
六句成节的有二种:
七句成节的也有二种:
其中,字之叶否,以清代学者们研究古音的结果而定(参看附录《古音录》)。“甲”“乙”等字是表叶与不叶的(甲与甲叶,乙与乙叶)。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赵翼《论诗》
如上文所说,宋玉作品之存于今者共十四篇,我认为只有两篇是真的,其余十二篇都有伪托的嫌疑。现在我们就要讨论这个嫌疑。
我们先讨论那十篇赋。
第一,这几篇赋不像战国时所能产生的。我们试撇开宋玉的十篇,试看周末至汉初的一百年中的赋的进化史。最早是荀卿的《赋篇》(共《知》《礼》《云》《蚕》《箴》五篇) ,大都是很幼稚的。试看这第一篇的第一段: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齐不均;桀纣之乱,汤武之贤。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乎参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可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宁泰。臣愚不识,愿闻其名。
这是说理诗的下乘。它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和《诗经》很接近,而与《楚辞》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他虽到过楚国,但那时年事已高;以一个负盛名的北方老儒到南方去,自然未必便受多大的影响。故我以为赋的起源当以班固“古诗之流”之言为妥。赋与辞的混合,始于贾谊。贾谊本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见《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 ,而他的境遇又与屈原很相似,时常寄居于屈原的故乡,故他的作品便袭荀卿的“赋”的名称,而用屈原的“辞”的形式。试看他的《吊屈原赋》说:
恭承嘉惠兮,待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窜伏兮,鸱鸮翱翔。
这种赋显然是屈、荀二人的作品的糅合(观“呜呼哀哉兮”句,便知贾谊学用“兮”字尚不如屈、宋之纯熟。司马迁、班固等人也称屈、宋的“辞”为“赋”,便为了这一点。然“辞”“赋”既为南北二文体名,则“好辞而以赋见称”句即为不词)。这时已较荀卿进步得多了,但同时又受了屈原的束缚,司马相如便进一步用散文的形式了。例如他的《子虚赋》里子虚向齐王述楚国的云梦道: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元厉,碝石碔砆。
这便是把荀、贾的作品“散文化”过,而仍保留其脚韵,有时连脚韵也没有。这一种文字不始于司马相如,例如晚周诸子及枚乘的《七发》便是如此的(无名氏的《卜居》《渔父》也是这一类的作品)。然而他们并没有称之为“赋”,作赋而用这一种体裁,相如是第一个。综上所述,可知赋的进化史可分三期:第一期代表为荀卿,那时尚未正式称赋(他只把《知》《礼》等篇合成《赋篇》,而无“知赋”“礼赋”等名称) ,形式方面完全与《诗经》一样。第二期代表为贾谊,他已正式称赋,但他觉得《诗经》式的荀赋不足达意,于是改用《楚辞》的格式。第三期代表为司马相如,他觉得《楚辞》的格式还不十分自然,于是改成偶然有韵的散文,而同时也不废贾谊一派的格式(如《大人赋》《哀二世赋》等)。自此以后,赋的格式不外此二种,而荀卿一派则中绝了,因为太不适用了。这个递变之迹是很明显的。我们再回看宋玉的十篇赋。他的赋是怎样的?他并不与荀卿一样的用《诗经》式,也不与贾谊一样的用《楚辞》式,他却与司马相如一样的用散文式(有时一篇中杂用《楚辞》式及散文式,但甚少)。以时代最早的宋玉,竟用出身最晚的格式!这一点,在文学史家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故我们不能不把这十篇的时代移后些,并且很大胆地说:假使它们确是宋玉所作,则这位“宋玉”绝不是战国时人。
第二,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十篇是战国时人作的,它们也绝非楚国的产品。它们大都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或以谈话本身作赋,或由谈话引出另一段文字。这些记载中说及襄王,必加一“楚”字。例如: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风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大言赋》)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小言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讽赋》)
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钓赋》)
楚襄王既游云梦。(《舞赋》)
只有《笛赋》是例外(然另有四伪证,详后) ,《登徒子好色赋》则无“襄”字: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
我们看了这几句,便不禁疑惑:宋玉既是楚人,何以赋中称襄王必冠以“楚”字?这一个疑问便引起我们研究古文学中称本国君主的体例。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里指出汉赋中称汉君的几处都不加“汉”字: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扬雄《甘泉赋序》)
孝成帝时羽猎,雄从。(扬雄《羽猎赋序》)
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立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
此外,我们还可补举几个例: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班固《两都赋序》)
故宣、成之世,论而录之。(同上)
同符乎高祖。(班固《东都赋》)
允恭乎孝文。(同上)
仪炳乎世宗。(同上。侃按:世宗即孝武帝。)
自孝武之所不征。(同上)孝宣之所未臣。(同上)
其余与此同例者尚多,不及遍举。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汉代的例子,不能借来证明周代的作品。那么,我们就举些周代的例子: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大雅·文王之什》。侃按:《诗经》中说及文王者凡三十八处。)
长子维行,笃行武王。(同上。侃按:《诗经》中说及武王者凡九处。)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颂·昊天有成命》。侃按:《诗经》中说及成王者凡二处。)
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召南·何彼秾矣》)
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士乎不与谋。(《左传·哀公五年》引齐国《莱人歌》)
我们看了这几个例子,便可以说:假使这十篇确是宋玉所作,则这位“宋玉”绝不是楚人。
第三,即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这十篇是楚人作的,但它们的著者也绝不是一个姓宋名玉的人。我们在上文说过,这几篇大都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这种记载显然是第三者作的。例如《高唐赋》说: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
没有成见的人如何能说这是宋玉自己作的!如果我们把上文所引扬雄《甘泉赋序》,依《高唐赋》而改成:
昔者,汉孝成帝时,客有荐扬雄文似相如者。
我们能相信这是扬雄的自叙吗?如果《高唐赋》真是宋玉自己作的,则当依《甘泉赋》而改成:
襄王与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
这一点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常识所能判断,可惜二千年来的读者竟都惑于旧说,习焉而不察!崔述曾经说过:
周庾信为《枯树赋》,称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马闻而叹曰……”云云。仲文为东阳时,桓温之死久矣。然则是赋作者托古人以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谢庄之赋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连、庄信其时近,其作者之名传,则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赋其时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则遂以为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考古续说》下《观书余论》)
这个怀疑是很不错的。这种假托是起源于荀卿。他的赋里大都是两个人的问答之辞,但究竟问答者是谁,却没有说明。这是文学技术幼稚之一证。贾谊便进步了,有主名了如《 鸟赋》便是叙
鸟赋》便是叙 鸟与著者问答之辞的(但他自称为“余”,与《神女》《登徒》之称“宋玉”不同)。但这种自叙的格式还嫌受牵掣,故司马相如便改用假名,如“子虚”“乌有公”之类。这也是文学技术的进步。最后,便有以历史的人物来借用的。但子虚、乌有公等名的假造是很明显的,人家看了,绝不会误认这赋即是子虚、乌有公做的。用了历史上的人物——这人物又是一个文学家——便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了。这误会大约可分三个时期。最初,《神女》《登徒》著者的朋友们,自然知道这几篇不但不是宋玉所自作,而且所记宋玉的谈话与事实也不是真的。略后些,便有人认这谈话和事实是真的,故傅毅便想用《舞赋》来续《高唐赋》。最后,如《文选》及《文心雕龙》便直说是宋玉作的。自此以后,宋玉便冒了千余年的名,而那位原作者却湮没到如今!然而文中自称“宋玉”,也适足以证明作者并不姓宋名玉。
鸟与著者问答之辞的(但他自称为“余”,与《神女》《登徒》之称“宋玉”不同)。但这种自叙的格式还嫌受牵掣,故司马相如便改用假名,如“子虚”“乌有公”之类。这也是文学技术的进步。最后,便有以历史的人物来借用的。但子虚、乌有公等名的假造是很明显的,人家看了,绝不会误认这赋即是子虚、乌有公做的。用了历史上的人物——这人物又是一个文学家——便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了。这误会大约可分三个时期。最初,《神女》《登徒》著者的朋友们,自然知道这几篇不但不是宋玉所自作,而且所记宋玉的谈话与事实也不是真的。略后些,便有人认这谈话和事实是真的,故傅毅便想用《舞赋》来续《高唐赋》。最后,如《文选》及《文心雕龙》便直说是宋玉作的。自此以后,宋玉便冒了千余年的名,而那位原作者却湮没到如今!然而文中自称“宋玉”,也适足以证明作者并不姓宋名玉。
以上三条是我认这十篇赋为伪作的主要理由。我们须知它们始载于《文选》《古文苑》二书,而这两部便不是可靠的书。《文选》所录如子夏《诗序》及苏、李赠答五言古诗等,均系著名的伪作。《古文苑》则编辑太晚(大约出宋初人手) ,故伪作更多,如峄山石刻、柏梁诗等都是。我们万不可上它们的当。
其次,我们再就这十篇赋本身分别指出伪证:先论《风赋》。其中有这几句:
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
刘大白先生指出,古音“酲”在青部,与“泠”“人”之在先部者不叶,又“灰”在灰部,与“余”“庐”之在模部者不叶,故断定为“汉代以后的人所伪托”。(《宋玉赋辨伪》)
次论《高唐赋》。此赋伪证有三。第一,王闿运说:
高唐邑在齐右,云梦泽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余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乱。(《楚辞释》附)
他这句本要完成他的谬说的(他以为《高唐赋》是宋玉述屈原连齐拒秦之策的) ,然我们可借以证明此赋为后人伪托,否则必不会把不相干的地名拉扯在一起。第二,篇末句说:
延年益寿千万岁。
这是汉乐府的滥调,例如:
千秋万岁乐无极。(《铙歌·上之回》)延寿千万岁。(《上陵》)
令吾主寿万年。(《临高台》)
益如寿……大乐万岁……增寿万年。(《远如期》)
延寿命永未央。(《郊祀歌·赤蛟》)
悲吟皇帝延寿命。(《吟叹曲·王子乔》)
万岁期延年。(《瑟调曲·艳歌何尝行》)
延年万岁期。(《楚调曲·白头吟》)
这便可助证此赋系汉人手笔。第三,刘大白先生指出赋中四处与古韵不合的:
(1)古音“石”在铎部,与“会”“ ”“厉”“
”“厉”“ ”“霈”“迈”“喙”“窜”“挚”之在齐部者不叶。
”“霈”“迈”“喙”“窜”“挚”之在齐部者不叶。
(2)古音“志”在咍部,与“蹠”之在铎部,“盖”“会”“蔼”“沛”“ ”“籁”“会”“气”“鼻”“泪”“瘁”“硙”“陨”“追”“益”之在齐部者不叶。
”“籁”“会”“气”“鼻”“泪”“瘁”“硙”“陨”“追”“益”之在齐部者不叶。
(3)古音“禽”在覃部,与“莘”“神”“陈”之在先部者不叶。
(4)古音“螭”在歌部,与“谐”“哀”之在咍部者不叶。此亦后人伪托之证。
次论《神女赋》。其中有这几句:
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似逝未行,中若肯首;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
刘大白先生指出,古音“备”在咍部,与“究”之在萧部者不叶,又“记”在咍部,与“首”“授”“覆”“究”之在萧部者不叶,故可证非宋玉作。次论《登徒子好色赋》。赋中一则说: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
再则说:
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
一再言“楚”,实与上文所说“楚襄王”同样可疑。今录前年论《大招》《招魂》真伪的一段于下,以供参阅:
屈原、宋玉都是楚人,但他们的作品里却从来没有一个“楚”字。即就《招魂》而言,它说“修门”,说“庐江”,说“云梦”,却不曾说“楚”;又说“《涉江》”,说“《采菱》”,说“《扬阿》”,说“《激楚》”,却不曾说“楚”;又说“秦篝”,说“齐缕”,说“郑绵”,说“郑舞”,说“吴羹”,说“吴歈”,说“蔡讴”,说“郑、卫妖玩”,说“晋制犀比”,楚以外的国名几乎说完了,却不曾说“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宋玉是楚人,故对于本国的地名、本国的歌名,都不说明,而对于他国的“篝”“缕”“歈”“讴”,则概加国名以示别。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然而《大招》便不同了。它一则曰“自恣荆楚”,再则曰“和楚酪”。三则曰“和楚沥”,四则曰“楚《劳商》”!在《大招》的著者看来,“荆楚”只与“代水”一样,“楚酪”“楚沥”只与“吴酸”“吴醴”一样,“楚《劳商》”只与“伏戏《驾辩》”一样。在《招魂》里,楚国的地位显然与他国不同。在《大招》里,楚国只是与“代、秦、郑、卫”同为诗人笔下的典故。(商务本《楚辞》卷首《引论》页四十八—四十九)
所以我们相信《登徒子好色赋》是与《大招》同为汉人伪托。
次论《笛赋》。此赋伪证有四。第一,赋中有这一段:
师旷将为《阳春》《北郑》《白雪》之曲,假涂南国,至于此山,望其丛生,见其异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
在这里,作者显然以宋意与师旷为同样的典故。然而荆轲刺秦王在楚负刍元年(公元前二二七年) ,宋玉时年已逾六十(参看上文) ,故宋意实是他的侄行,如何在他文章里用做典故呢?所以章樵说:
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后又二十余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赋宋玉所作邪? (《古文苑》注)
严可均也说:
按此赋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全上古三代文》)
第二,赋中又有这两句:
吟《清商》,追流徵。
《清商》为汉乐府之一种,如《平调》《清调》《瑟调》等,当时所谓“《清商》三调”(《宋志》)是也。为什么叫“清商”呢?因为如《魏志》说“《清调》以商为主”,故举一以概其余(后人大都以三调误入《相和》)。汉以后的诗中常常喜欢提起《清商》,如: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伪枚乘诗)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伪苏武诗)
所以“清商”二字不能见于宋玉赋中。其实这两句大约是从《文选·对楚王问》“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两句上模仿来的,然而作者不小心,把“引商”误作“清商”,于是便露出马脚来了。第三,乱辞说:
绝郑之遗,离南楚兮。
这与《登徒子好色赋》中“南楚穷巷之妾”句同样可疑。故游国恩先生说:
篇中有“南楚”一句,已经很可疑,何况出于可靠性极薄弱的《古文苑》?
第四,刘大白先生指出赋中四处与古韵不合的:
(1)古音“阜”在萧部,与“起”“右”之在咍部者不叶。
(2)古音“明”在唐部,与“存”在痕部不叶,与“生”“荣”之在青部者亦不叶。
(3)古音“楚”在模部,与“宝”“道”“老”“好”“受”“保”“茂”之在萧部者不叶。
(4)古音“靡”在歌部,与“手”在萧部,“欝”在屑部不叶,与“子”“齿”“起”“徵”之在咍部者亦不叶。
此亦后人伪托之证。
次论《大言赋》《小言赋》。楚襄王说:
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高卑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
刘大白先生指出“备”古音在咍部,与“伟”“贵”“类”“位”之在齐部者不叶,故亦后人伪托。
次论《讽赋》。《讽赋》前半篇模拟《登徒子好色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辞;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曰:“臣身体容冶,受之二亲;口多微辞,闻之圣人。”(《讽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受于师也。”(《登徒子好色赋》)
后半篇模拟司马相如《美人赋》:
臣尝出行……独有主人女在……中有鸣琴焉,臣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来排臣户曰:“上客,无乃饥乎?”……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又为臣歌曰:“……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玉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讽赋》)
(臣)命驾东来……有女独处……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玉钗挂臣冠……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美人赋》)
《登徒子好色赋》之不可信已如上述,则《讽赋》之伪托自不待言;而且竟抄袭到《美人赋》,那更是晚出之证(《美人赋》是否真出相如手,尚是问题)。
次论《钓赋》。《钓赋》的结构上,大约是从《风赋》脱胎来的。《风赋》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敷陈,《钓赋》则以“尧、舜、汤、禹之钓”与“水滨之役夫”并举为言,其模拟之迹是很显然的。而且其中有这一句:
昔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
这显然抄自《孟子》的: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焦循《孟子正义》列举后人袭用这两句的,如《史记·平原君列传》、《韩诗外传》、陆贾《新语》、褚先生《答张夫子问》等,均汉人之作;又有《荀子·仲尼》篇,则是伪作。故《钓赋》之为后人伪托,由此益可证明。
最后论《舞赋》。这显然是夺自传毅的。章樵说:
傅毅《舞赋》,《文选》已载全文。唐人欧阳询简节其辞,编之《艺文类聚》,此篇是也。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诺之辞,遂指为玉所作,其实非也。(《古文苑》注)
所以这篇的真伪,最是容易辨明。到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时,便干脆剔出了。
总之,这十篇赋,无论从哪一点观察,均可证实其为伪作。
其次,我们讨论《对楚王问》及《高唐对》二篇散文。
这两篇之入《宋玉集》,似乎起因于误会。《对楚王问》叙宋玉与楚襄王的谈话,与《新序·杂事第一》所载宋玉轶事相同(参看上文)。其体裁与《卜居》《渔父》相近,显然是第三者的记载,而被人误认为宋玉自己作的。古籍中这类记载甚多,如何能一起挤入《宋玉集》里呢!至于《高唐对》,内容与《高唐赋》首段差不多,不过字句微有不同,且多一段神女自述的话:
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
全文原见《文选》李善注引,称“宋玉集”,所以也许即《高唐赋》之异文。《渚宫旧事》有一段记载与此词句相近,云出《襄阳耆旧记》(今本《襄阳耆旧记》无此条) ,而《襄阳耆旧记》即系杂抄《新序》等书而成,所以也许为古籍所记宋玉逸事之一。这“异文”与“轶事”二说是比较合理的假设,都可证明非宋玉作,而严可均竟擅加“高唐对”之题,加入《宋玉集》内,真冒昧之至。
此外,上文论十篇赋的第二、第三两疑点,也可助证这两篇散文之为伪作。
现在我们对于伪托的原因及伪托的时代,要试探一下。
依我看来,伪托的原因可从两点去说明:
(1)文学的。我们须知辞赋假托于楚,是件很普通的事。如枚乘《七发》假托“吴客”与“楚太子”的谈话,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也假托“楚使子虚发于齐”之事,均可证,盖自贾谊采用《楚辞》的格式来做赋以后,赋与楚国便结了不解之缘了。
(2)历史的。云梦是楚之瑰宝(观《国语》王孙圉答赵简子语可知) ,楚君又喜欢遨游于此(《国策·楚策》屡载游云梦事,《招魂》乱辞亦言及之) ,故这些伪赋中一则曰“游于云梦之台”,再则曰“游于云梦之浦”,三则曰“游于阳云之台”,四则曰“既游云梦”。但为什么不托屈原而托宋玉呢?这也很容易明白的。屈原是一位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对于儿女闲情,似非所解,而宋玉却是位风流自赏的文人,又有一篇精彩绝艳的《招魂》流传下来,所以“红粉赠与佳人”,宋玉便得到意外的收获。
至于伪托的时代方面,《舞赋》本是傅毅的作品,其时代不待说,而《对楚王问》及《高唐对》本不能算独立的单篇的作品,其时代也不必讨论,所以现在只注意其他九篇伪赋。我们自然不能指出某年某月为它们出世的时代,如今只根据我们所能搜集的材料来断定最早不得在某时以前,最迟不得在某时以后:
(1)最早的限度。我以为这九篇出世的时代最早不得在公元前一〇〇年(汉武帝即位第四十一年)以前。因为从体裁上看来,它们一定在司马相如以后(参看上文)。
(2)最迟的限度。最迟的限度便不易断定。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自以《高唐赋》为最早,因为傅毅在《舞赋》里已说及了。次之便是《神女赋》,见曹植的《洛神赋》。再次之便是《登徒子好色赋》,阮籍《咏怀》所谓“倾城迷下蔡”大约指此。再次之便是《风赋》,晋代有湛方生、陆冲、李元充及王凝之等人拟作。再次之便是《大言赋》《小言赋》,傅咸有《小语赋》,昭明太子有《大言诗》《细言诗》,大约即仿此二赋。再次之便是《讽赋》,谢惠连《雪赋》所谓“楚谣以幽兰俪曲”大约指此。再次之便是《钓赋》,见《文心雕龙》的《诠赋》。最后是《笛赋》,《文选·洞箫赋》李善注曾引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文选》所载四篇为汉、魏人所伪托,《古文苑》所载五篇为六朝人所伪托,其余三篇则系后人误认。
我一方面怀疑人家认为真的十篇赋和二篇散文,同时却也有人怀疑我认为真的《九辩》和《招魂》。如今再辩明几句。
据我所知,怀疑《九辩》非宋玉作者有两起。一是焦竑:
《九辩》无哀师意,恐非宋玉作。(《文选旁证》引)
一是梁任公先生:
《释文》本何故以此篇置诸第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余篇皆屈原作,而中间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异也……故吾窃疑《九辩》实刘向所编《屈赋》中之一篇。(《要籍解题》)
其实《九辩》中诚然无“哀师”的意思,这本来是王逸的谬说,我们正好因此而推翻王说,更何能借王说以否认宋玉为《九辩》的作者?这种见解太好笑,我们也不必多辩了。至于《释文》的篇次,本不依作者的先后来排列的,如列《招隐士》于《招魂》前,列《惜誓》于《哀时命》后等,均可证。其所以次《九辩》于《离骚》之后、《九歌》之前,大约拘于《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及《天问》“《九辩》《九歌》”二句,所以变成第二了,我们并不能因此便认为非宋玉作。
怀疑《招魂》的却很多。他们主张送给屈原。这说始于明末黄文焕的《楚辞听直》,继以林云铭的《楚辞灯》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于是此说势力愈扩愈大,近人如郑沅、马其昶及梁任公先生等均为所惑。我从前曾列举他们的理由而加以解释,今录于下。
他们最重要的理由是:
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 (林云铭语)
《招魂》著者宋玉是屈原的后辈,故相传被招者即屈原;确否虽不可知,但已可证明“悲其志”一语是很讲得通的了。而且这种拈来的传赞,也绝不能当作铁证。此外,林云铭还提出两个疑点:
玩篇首自叙,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断非出于他人口吻。
若系玉作……亦当仿古礼,自致其招之辞,不待借巫阳下招,致涉游戏。(均见《楚辞灯》)
前一条理由是一个巧妙的遁词。他只举篇首、篇末,却把中间一段本文搁置不提了。这本文里用“君”字处是很多的,例如:
去君之恒干。
舍君之乐处。
君无上天些。
君无下此幽都些。
工祝招君。
像设君室。
侍君之闲些。
“自招”二字本来是很牵强的,何况又有这些“君”字来作反证呢?至于篇首的“朕”字及乱辞里的“余”字,本来是假托被招者的口吻。在本文里,他当然正式称君,本文以外便可不这样了(也许为避单调起见)。这种假托的例是很多的。《离骚》里女媭对屈原说: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这“余”字是代原为辞的,并非女媭自指。又如《九辩》说: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
这里两个“余”字便是著者代“有美一人”为辞的(《诗·卷耳》第二、三、四章里的“我”字也是如此)。这种例子我也不多举了。而且即使我们退一百步而承认这篇确系“自招”,则我们如何不能说是宋玉自招而一定要说是屈原自招呢?可见这一条理由实在是很薄弱的。至于他的后一项理由却更不能成立了:也许宋玉爱那么写法呢,我们如何能捉摸一个诗人的心理?近来郑沅又举出一条理由:
其中杂陈宫室饮食男女珍宝之盛,皆非诸侯之礼不足以当之。此岂宋玉、景差辈所能施之于其师者?故我们可说这篇是屈原招怀王的文字。(见《招魂非宋玉作说》,载《中国学报》第九期)
其实这只能证明被招者不是屈原,却不能证明著者不是宋玉。屈原能招怀王,宋玉何独不能? (其实这篇也非招怀王,因为文中只说南行打猎,而未说西行入秦。)最近梁任公先生又举出一条理由:
《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见《屈原研究》,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学灯》及《晨报副刊》)
这条理由未免太空泛了。试问:宋玉的文体与理想是怎样的?屈原的文体与理想又是怎样的?《招魂》的文体与理想又是怎样的?我们必须把这三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方能根据文体与理想来断定《招魂》的著者。然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实在是很困难的,故梁先生也就含糊过去了。这能使人心服吗?而且拿理想、文体来做考证的根据实在是很危险的。《离骚》的文体与《天问》不同,《天问》的理想又与《九章》不同(另详) ,然而不害其为一个人的作品。梁先生也承认它们同为屈原的作品(《屈原评传》页一三八—一四三)。
以上说明了黄、林、郑、梁等人所举理由的不充足。然而最重要的反证是《招魂》的时代。我们在上文已经证明这篇出世是在屈原死后五十年以后,故它的著者之为宋玉而非屈原,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以上一万字的“余论”,是讨论那十四篇的著者问题的。但一个人的学力是有限的,自然未必能使反对者闭口无言,赞成者称心满意。一切讨论这问题的文字总能遇到作者最诚恳的欢迎和感谢。
十二年十二月初稿,于北京。
十七年八月改定稿,于上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