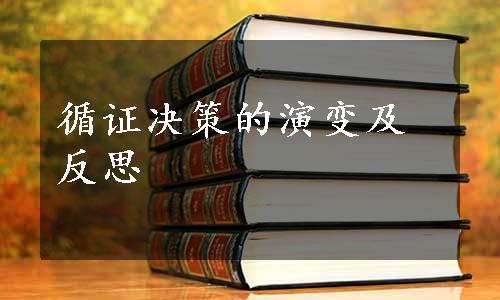
循证决策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反思与批评。现有的反思与批评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第一,循证决策是否真正可行?此争议首先涉及布莱尔政府是否言行一致的问题:英国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介入伊拉克战争,被学者称为“基于政策的证据”而非“基于证据的政策”。当然,批评主要来自学界,由于其管理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取向,循证决策受到来自后实证主义的批判,作为循证决策基石的证据也成为争议的焦点(王哲,2009)。比如证据是否无可争议?证据是否过于简单化从而脱离政治现实?是否所有研究成果具有同等质量足以构成科学决策的证据?实证研究是否给予对立观点同等的关切?实证研究费时费力,其研究结论对决策来说是否为时已晚(Davis,2000)?Mulgan指出,把证据置于决策的核心位置是一种误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受到学科视野的限制;决策不仅需要证据,而且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政策不仅要行之有效,还要看付出多大成本;循证决策取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但习惯和传统其实在发挥重要作用(Mulgan,2003)。可见,争议和批评的重点不是否定其正当性,而是质疑其可行性和真诚性。从理论上看,循证决策受到的批评和理性主义模型的命运相似。在诸多决策模型中,区分应然规范模型和实然经验模型尤为重要。传统理性主义属于规范模型,关注的是应该怎样做,而渐进决策模型、垃圾筒模型、精英模型等属于经验模型,是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因为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原则和规范本身,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理性主义模型备受抨击,但依然是各国政府决策的不懈追求。
第二,循证决策到底是一种理论模型还是一场实践运动?在国内屈指可数的相关研究中,循证决策更多被视为一种理论模型。郭巍青教授认为:“理性主义决策模型和反理性主义决策模型是政策制定方法论上对立的两极。在它们之间或者之外,至少还有两种重要的模型,一种是渐进决策模型,一种是循证决策模型,前者是从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环节,后者则是对理性主义决策原则的回归。”在他看来,循证决策代表了理性主义决策观念的东山再起,但又不是传统理性模型的简单回归,它在四个重要方面“刷新和深化了理性决策的命题”:1.强调“证据选择”,这比理性模型中的“方案选择”更为深刻;2.将知识运用视作复杂组织背景下的系统工程,将“渐进决策”模型和“垃圾箱”模型所主张的“行为者分析”和“制度分析”纳入考虑,因而是一个重要的进步;3.突出决策信息化、民主化和知识化;4.突出政策评估对正确决策的重要作用(郭巍青,2003)。(www.zuozong.com)
我们认为,循证决策不是一个着眼于规约或解释的理论模型,更多的是一种政策主张,或旨在提升政策有效性的“实践运动”。借用郭巍青教授的话:“不是课堂上的教学模型,而是一种‘政府主张’”。将其称为“实践运动”有几个理由:1.其倡导者是布莱尔政府,主要载体是政府官方文件,核心内容及构成要素侧重于实践应用;2.虽然提倡者区分了信息和证据并强调转换的重要性,但没有对这一区分和转换机制做出系统精致的理论分析,其主要精力在于为实现这一转换以及证据的有效使用构建制度保障和相应的机制。如果把循证决策定位于突出决策科学性和理性的实践运动,它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既非传统理性模型的简单回归,也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决策模型“之间或之外”的某种事物,而是传统理性模型的新发展。更准确地说,它继承了理性主义模型的理论逻辑和传统,但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发展和超越,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新阶段或者理性模型指导下的实践新趋势。
把循证决策更多视为一种实践运动,那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应该是其理论贡献,也不是它与其他理论模型的比较。循证决策继承了理性主义模型的理论取向和逻辑,其主要超越和进展表现在实践上。如果说它是一种新理念和新原则,其新颖之处并没有全面超越理性主义。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针对的特定情境、新背景下的特殊体现方式、不同的社会效果等,往往会赋予老的理念和原则以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新”的原则。因此,理解和研究循证决策,必须把它置于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必须深入了解它在政府改革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方式;着眼于实际应用的具体案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