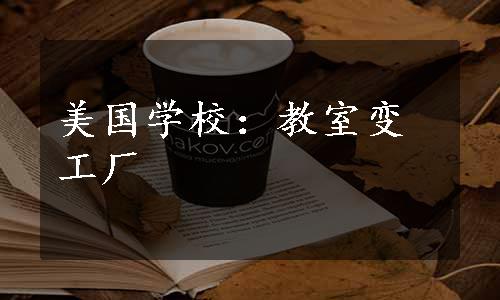
与给未来劳动力市场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观点同时出现的是,关于教学和课堂组织的新理论。在纽约市,学校建筑设计师斯奈德在20世纪上半叶设计了未来可能的标准化教室的方案:每排桌子将面向黑板固定在地板上,“1年级到4年级的教室安置48张永久性课桌,5、6年级教室安置45张;7、8年级则安置40张。”[74]拉里·库班在著作《教师如何教学:美国教室中的不变和变化(1890~1980年)》中预测在1920~1940年,79%的中学课桌会被固定在地板上。在某些特殊教室和幼儿园中,也允许使用一些可移动的家具,但是大多数教室中固定的课桌主要为了避免发出噪音和混乱。在更先进的学校体系中,例如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中只有19%的中学课桌是固定的,但没有数据说明该市小学的情况。纽约市1920年的情况是将近2/3的小学课桌固定在地板上,到1929年,可移动课桌只替换了200张固定课桌;然后在1930年,一项为期五年的项目开始启动,该项目要替换掉7000张固定课桌。当时,华盛顿特区1/3的高中课桌依然固定在地板上。[75]
上述三个城市的例子说明大多数学校只允许学生在课堂中极少地移动。课堂中的学生数量是决定教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小规模的班级可以更多地采用实验和灵活性的教学方法,规模较大的班级则更倾向强调课堂秩序和纪律。也就是说,较大规模的班级通常要求教师采取对学生控制性更强的教学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纽约市小学班级平均规模50名学生。到1930年,这个数字降到38,但是每个学校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当时至少有17%的学校平均班级规模在45名或更多学生。1923年,丹佛市60%的小学班级有30~40名学生,13%的班级规模在40名以上,27%的班级规模在30名以下。1934年,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班级规模激增。只有3%的学校班级规模在30人以下,33%的学校班级规模达到40人以上,64%的学校班级规模在30~40人。因为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体系是隔离的,所以根据学校种族构成不同班级规模也有所差异。1922年,白人小学的平均班级规模为34.3人,黑人小学的平均班级规模为37.3人;到1932年,班级规模分别降到30.8和36.1。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各种复杂且巨大的差异。1927~1928年,29%的黑人和白人小学班级规模都超过了40人。中学平均班级规模没有统计数据。[76]
这些班级规模和班级结构的统计数据,说明大多数教师很难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给学生大量的活动机会,但是允许学生移动的课堂确实存在。
19世纪80~90年代,人们熟知的赫尔巴特主义运动推行的教学法在美国最为盛行。该教学法源于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1776—1841)的学说。赫尔巴特主义运动主要的贡献是,制定适合于任何规模或结构的班级教学计划。但是,这种教学计划逐渐变成美国教育僵化的特征,因为它让教师受控于官僚体系。教学计划往往变成校长或督学随时检验教师教学活动的工具。而且随着教学计划的发展,也反映出教育过分强调秩序和计划性的概念化特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法能够满足固定环境中大班教学的要求。
当然,赫尔巴特主义运动者看中的不仅是教学计划;但是公立学校的课堂使得赫尔巴特学说最终简化为细致入微地做好课堂教学计划。一名美国著名的赫尔巴特学说采用者,查尔斯·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在其1895年出版的书中提出,赫尔巴特为裴斯泰洛齐教学法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德加谟认为,赫尔巴特接受了裴斯泰洛齐通过意义和客观实物学习的思想,但是,他认为裴斯泰洛齐教学法欠缺对知识如何进入学生头脑的思考。在“裴斯泰洛齐给赫尔巴特留下什么可做”这章内容中,德加谟提出裴斯泰洛齐教学法“没有说明心理同化是如何发生的,或者如何最有效地获得那些能够影响我们情绪和意志方面的东西。感觉是认知的第一阶段,但是同样重要的相关概念是领悟或心理同化。”[77]
在赫尔巴特学说中,心理同化和教学计划的组织的核心是兴趣。有人可能认为,兴趣通常导致儿童中心的教育。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兴趣学说认为只要学生有兴趣,就能最好地实现知识的吸收。兴趣可能源自知识或者与社会的接触。与知识相关的兴趣包括思辨的、经验的和审美的兴趣,源自与其他事物接触的兴趣,包括同情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兴趣。
根据赫尔巴特学说,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呈现与学生先前兴趣相关的材料。因此,根据学生兴趣发展阶段,适当调整学科内容并计划课堂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赫尔巴特认为孩子的自然兴趣说明应该在拉丁语之前教授希腊语。
赫尔巴特的教学计划包括五个步骤:(1)预备;(2)讲解;(3)比较和归纳;(4)总括或定义;(5)应用。预备是使学生回想起与讲授内容相关的以往的知识和兴趣。讲解要围绕与学生先前的兴趣和知识相关的内容组织。比较是演示新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之间的关系。总括是概括一节课的核心内容,形成一个抽象的定义。应用是将所得结论与其他经验发生联系。
维拉德·艾尔斯布里(Willard Elsbree)指出:“这简单的五步教学法,对美国1890~1905年的教学实践无疑产生了比任何其他心理学发现和哲学创造的结合都更为深远的影响。”[78]尽管赫尔巴特教学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正式地、认真地准备每日教学计划却成为美国教育的特征。较大的班级规模、固定的课桌与教学计划并不矛盾,而且每天的教学计划也适合基于等级制的严格控制、秩序和纪律的教学环境。
与此相反,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教学理论与标准化的美国课堂却格格不入。事实上,189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组织著名的实验学校时,所遇到的问题竟是找不到适合小组合作学习的课桌,因为所有的课桌都是为学生独立学习设计的且被固定在地板上。在实践中,杜威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兴趣、学生活动、小组学习与合作——这种教学方法建立在这样一种预设上,即学校必须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活和大型企业社会中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在杜威建成实验学校后,他希望开发出一套能够给学生展示知识的社会价值和知识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教学方法。其中一种教学方法是,通过小组合作活动发展学生的社会想象力。杜威将社会想象力定义为:“心理上建构人际互动现实意义的习惯,以及请教该做什么的习惯”。他早期的实验是于19世纪90年代,在一所高中道德课中进行的。杜威希望学生能够将道德与违反现实规则的问题联系起来。他给学生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间悲剧,然后让学生用社会想象力找到人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社会想象力是一种将独立观点和现实情况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他们原本意义的能力。杜威相信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反思自身及所处现实环境的本质的习惯”[79]。
这种道德教育方法还基于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杜威认为观念、价值和制度都源于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他反对人们将自己看做出自神明或代表某些理想的群体。他认为一个问题是:理想模式下的信仰,导致文明化进程受到了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他认为观念、价值和制度应该根据社会的改变而变化。实用主义这个概念,通常与这种学校理念有关,简而言之就是指人类应该接受那些能够最好适应现实社会状况的观念、价值和制度等。
人们因此可能容易理解很多20世纪的宗教团体反对杜威思想的原因。多数宗教团体认为,人类的行为应该受到上帝教义的指导,合理的价值观应该源自神的思想,但是杜威的哲学是不用上帝的教义,而用个体的能力解释自己的经验。
杜威认为,没有必要让学生了解知识与社会经验之间的联系,并且给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实践的机会。这就是他所坚信的:只有行动才能将社会想象力从信息转变为结果。一旦行动开始,社会想象力就变成了行动的判断力。他指出:“只有让孩子不断形成和检验自己的判断,他们才可能获得判断力。”因此,学校不应教授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提供可能产生这些概念的现实情境,而且必须给孩子在校内检验自己的道德和判断正确与否的机会。也就是说,学校必须成为一个体现真实社会关系的社区。[80]
杜威常说学校就是一个真实社会生活的社区。杜威希望利用这个社区,并将其变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这可以最好地帮助学生了解知识的社会价值。例如在实验学校中,通过幼儿园小朋友布置上午点心的桌子,教给孩子计数,孩子们通过将小朋友数量与餐具数量相匹配的过程,迅速地学会计数。
杜威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也认为现代城市的工业化生活并没有提供给孩子任何教授遵守秩序、勤奋与合作的社会情境。他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校这个社区学习过程中形成这些良好品质。1899年,杜威在其一系列“学校与社会”演讲中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系列演讲主要是为了回应对实验学校的批评而进行的。在演讲中,他强调工业化进程彻底破坏了传统家庭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生活让孩子“养成遵守世界的秩序、勤奋、责任感、做某事的义务感以及创造某些事物的习惯”。他认为过去的孩子可以学到这些习惯是因为大多数职业是家庭作坊式的。在工业发达的芝加哥演讲时,他提醒听众:“今天在座的各位回忆上一代、两代,至多三代,就能找到各种职业都以家庭作为中心的时代。”[81]
杜威的观点是,儿童应该同时经历和完全参与工业化社会的过程。通过这些社会经验,儿童能够形成道德习惯、勤奋与社会合作性,“但是感慨孩子们身上丧失了谦恭、崇敬和绝对顺从的好品质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是保留住当前部分好品质的同时,“也需要将生活的另一面引入学校——培养个人责任感和训练孩子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82]
实验学校中的活动就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互动的机会,从而实现有效学习并养成良好的社会习惯。学校中年纪较小的学生,活动围绕家务劳动开展。杜威认为,将共同的结果作为活动目标能够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氛围。4~5岁的孩子要负责给自己准备上午的点心,他们因此就需要讨论自己的家庭生活,随之探索市场、邮局及其他相关职业。参加筹建一家干货食品店的孩子们逐渐体验并养成了勤奋、责任心与社会合作性。在完成项目要求的同时,他们还学习了阅读、写作和算术。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参与更广泛的活动。6岁的孩子们开始接触农业活动。他们搭建了一个农舍和一个木制的谷仓,并且研究了气候和农作物的问题。7岁的孩子们开始学习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该学习任务在杜威学校贯彻始终,活动通常与孩子们的学习和研究相联系,例如,孩子们进行职业调查并且参与到类似纺织和建造熔炉的活动中时,他们就开始学习历史。
实验学校中学习历史的方法,反映了杜威关于社会想象力和社区的思想。学生们通过学习与其出生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思想、发明和制度,培养起社会想象力。他也希望这个过程能让学生意识到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一个社会就是一定数量的人们聚集起来,他们在共同规范的领域内活动,有共同的精神并努力达到共同的结果。”[83]杜威感到,过去美国确实有过社区,那是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生产过程的完整性,这使人们加入到一个贯穿着合作意识的社区中。他认为现代城市工业社会正在破坏这种社区意识和共同的目标,那么学校必须积极地促成它们的形成。在学校内的合作学习,社会想象力对学生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将所学的内容与产业的完整过程结合起来,并树立起分享共同社会目标的意识。
面对工业化的芝加哥的批评家们,1899年杜威指出:“今天有多少受雇者不过是他们操作的机器上的附属物!这对工人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恐怕大部分原因在于,工人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也无法深入思考所从事的工作中体现的社会和科学价值。”[84]1902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成立之前,杜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反映城市化的美国中真实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必须向工人解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智力与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必须揭示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85]
但是,很多教育者在课堂教学中实践杜威的学说时,都遗漏了很多他关于社会想象力和职业历史来源的思想。很多人认为,杜威就代表着小组活动、边做边学、将教材与孩子的兴趣结合起来以及课堂教学设计等。杜威的一些言论,如“各种教学相互发生联系的真正关键是孩子自己的社会活动”往往被用于证明分组教学和学校社会性活动的合理性,但是通常这些方法强调的小组统一性是完全与杜威的本意相违背的。例如,杜威认为动机和选择是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产生的;但是与其他教育者的观点一样,他并不认为个人的动机和目标应该与小组一致。杜威希望给个体行为以自由,而不是用小组中多数人同意的标准约束个人的行为。
作为向大众介绍推广小组活动学习的人,科林·斯科特(Colin Scott)在1906年组织成立了社会教育协会。斯科特推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组织课堂教学,因为他认为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而小组合作学习是社会组织中最有效的形式。他认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氛围与现代社会组织是冲突的,课堂应该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对将来要进入合作性社会的学生进行教学。
通过社会教育协会,斯科特将为合作性社会生活做准备的自治小组活动引入课堂教学。该协会的宪章指出:“教育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帮助孩子在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做准备,帮助学生成为社会有机体中一名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成员。”斯科特的自治小组活动的原则是:给学生选择自己的目标,组建自己的小组并进行自己的学习的机会。[86](www.zuozong.com)
斯科特举例说明这种方法。他首先向学生提问:“如果你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做且你认为有价值做的事情,你会选择做什么呢?”三名男孩儿立即选择做印刷。随后,他们组建了一个印刷小组,并开始为整个班级印刷各种资料。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将历史课堂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一些学生选择作为政府的印刷工,对历史的学习是通过一系列的法案和争论为线索。[87]
随着杜威实验工作的扩展及社会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人们越来越熟悉社会化课堂活动的观点。各种教育期刊上关于小组课堂教学的文章和书籍大量涌现,主题从算术练习的社会化到在自治小组中进行烹饪教学,等等。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迈克尔·奥谢和爱荷华大学的欧文·金教授带领下,社会教育的课程也开始出现在教师培训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rtrick)在他的班级上采用小组学习——他称之为“项目法”的方式教学。关于这种教学方法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1918年,之后就变得甚为流行并得到广泛应用。到1922年时,该书已经修订了7版。项目法的核心是克伯屈称之为“有社会性目的的行为”——只想产生对社会有用的结果的活动。克伯屈引用一个女孩儿化装的情境作为例子。如果一名女孩确实计划并尝试化装,这名女孩儿的社会目标所激励的化装行为可以看做一个项目。根据克伯屈的观点,有目的的行为是有价值的生活和民主的基本元素。“一个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活按照有社会价值的目标努力的人,能够立刻承担效率和道德责任。这样一个人正是理想的民主社会的公民形象。”在教室中,通过进行来自实际社会的项目,为孩子将来有目的的生活做好准备。[88]
克伯屈的项目法同样反映了很多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社会教育的观点:强调社会团结统一。他认为项目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他将道德品质定义为:“某人行为决策的倾向和针对群体利益的态度。”在课堂中,小组接纳或拒绝学生的行为,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当我们的同伴赞同或反对时,我们体验到的是几乎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或令人沮丧的烦恼……如果仅仅是老师强迫或反对,而其他同伴表示支持的话……小组的团结性在此得以体现——一致对外;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某些事情是对的时候……团结就不仅仅是一致对外了。”克伯屈认为,道德品质是在个人处于经常对群体要求作出回应时发展起来的。[89]
项目法、小组活动、社会化学习、儿童中心的教育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想象力等观点在教育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教学方法看起来最适合帮助学生做好准备,适应未来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和企业生活。当然,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教师都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这些教学方法的应用要根据师资能力、校园位置、班级规模以及课堂环境等因素。
虽然固定课桌、规模较大的班级不太适用社会化的教学方法,但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也就大班教学提出一些建议。作为哈佛大学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詹姆士(1842—1910)将他的两卷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年)压缩成一卷本的教师教材。该压缩本于1899年出版,书名为《在心理学基础上与教师对话:并在生活的理想上与学生对话》。桑代克(1874—1949)在哈佛研究学习时,得到了詹姆士的指导,并且将詹姆士的很多思想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他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之父”,因为他在1913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对教育的影响长达数十年。
詹姆士和桑代克的理论都受到“刺激—反应”及学习概念的影响。詹姆士提出的经典学习案例,即在《心理学原理》这本书的序言中,描述的一个伸手去摸蜡烛火焰的婴儿对“火”这个刺激所作出的反应。这个婴儿的手指被烫了一下,因此婴儿学会了“不去碰火”。詹姆士相信,将来这个孩子任何时候看到“蜡烛火焰”这个刺激时,其神经系统会唤醒痛的记忆,并阻止最初的“抓”反应,从而使孩子的手收回来。[90]
詹姆士认为,这个简单的情境启动婴儿习惯的养成和发展。他认为习惯的养成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只有每个人养成受约束的习惯,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
因此,习惯是社会巨大的推动轮,也是社会最大的保守力量。它足以让我们所有人墨守成规,能使富人的孩子不受穷人妒忌性反抗的伤害。它足以防止生活在最困难、最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的人们不会被那些生来是压迫者的人所抛弃。[91]
詹姆士将习惯的概念扩展到思维的过程中。当一个人思考时,头脑中总是有一套固定的思维体系。面临选择时,人们往往从固定的思维体系中选择一个行为。当然,个体往往是在习惯的特定情况和特定的思维体系中形成自己的观点。詹姆士认为,行为的选择是基于先前的刺激—反应的经验。詹姆士认为这套人类行为的推理过程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忽略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如果所有行为和选择都是基于先前经验判断得出的,那么个体就丧失了自由意志和对自己行为应承担的责任。从詹姆士最初的研究开始,这个问题就是行为主义的核心问题。詹姆士认为只要认为个体在思维体系中有权和有能力选择特定的事情,那就可以看做解决了这个难题。
尽管詹姆士从未倡导过任何特殊的课堂教学方法,但是他的心理学理论中,暗示通过练习和反复训练可以培养良好的习惯。爱德华·桑代克在将刺激—反应式学习融入他所谓的“关联主义”时,将这两条作为自己教学论的一部分。关联主义是指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桑代克认为人类所有智力方面的变化,都是某些基本法则对这些联系产生影响的结果。
桑代克所谓的“变革的基本法则”逐渐成为了他的基本教学方法。通常来说,他的教学法就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但是桑代克用一些方法证明了这些教学法的合理性,使之听似具有科学性。例如,他的基本法则——训练法则,指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与特定情境联系的反应越频繁或者越深入,将来越有可能发生反应。”他举了个例子,一个孩子正在思考“4加2等于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6。按照推测,如果这个孩子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那么他将会把这个问题和答案永远牢记心头。桑代克用更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这条法则:“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练习能够加强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系。”[92]
桑代克的第二条学习法则——影响法则指出:“针对某一特定情境作出反应的同时或随后给予的满意表示越大,将来重复这个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在孩子对“4加2等于几?”这个问题作出“6”这个反应时,如果给他一块糖果或一个微笑,正确的答案将会被强化。[93]
桑代克认为,教学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的科学:“用心理学术语来讲,教学艺术可以被界定为给予刺激和拒绝给予刺激,从而导致或防止一定反应的发生。”教师的权力表现在他/她能够控制刺激。桑代克将刺激分为两类:“直接控制”和“非直接控制”。直接控制下的刺激包括爱和恰如其分的表示,往往通过姿势、面部表情和言语得以体现;非直接控制下的刺激是学校和班级的外部物理条件。[94]
桑代克的梦想是将所有教学转化成科学的专业,因此所有教育者能够得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指导。作为一名科学的专业人员,教育者应该以科学的测量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实施控制。在桑代克的理论中,科学组织的测验是教育过程的核心:“对教师而言,对教与学的结果测验,就仿佛科学家验证假设……这是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不同先前经验和能力的主要方法。”[95]
与杜威一样,桑代克关于社会的观念与其提倡的教育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的关于社会的核心概念是测验和测量。他认为理想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社会角色是经过测验、科学选择的。他认为通过测验和测量将人分成不同类别,将会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因为个人的才智能够与社会的需求匹配起来。该理论使心理学家与学校成为人力资源分类决定的关键。
因为他的社会哲学是基于智力测验的,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测量,因此他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了民主社会和机会均等的思想。
桑代克相信智力是天生的,而且可以用测验测量出来。他将智力定义为,人们在刺激—反应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系的数量。“一个人的智力比其他人更高、更好或更多的区别并非在于他有一套全新的心理程序,而是他建立了更多的普遍事物之间的联系。”智力的这种定义使得对智力质量进行定量的测量成为可能。[96]
智力主要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环境塑造的观点,对社会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桑代克坚定地支持“天生论”与“教育论”的争辩中的“天生论”。他对智力测量的看法是:“这个理论认为在先天条件不同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来的思想联系或联结的数量是有差异的,因此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一些人的思想联系的数量总是比另一些人多。”[97]认为智力主要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也认同智力可遗传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往往最后推导出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结论。例如,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北欧人种比南欧人种的智力水平高。
固定课桌且规模较大的班级更适宜采用桑代克的刺激—反应、联系、奖励以及测量等教学方法,相反,不便使用社会教育者提倡的小组活动和社会化的教学法。显然,当一名老师可以在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时,他/她肯定更愿意采用桑代克的科学化的教学法。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教师乐于接受威廉·钱德勒·巴格利(William Chandler Bagley)在他的畅销书《课堂管理》中所鼓吹的课堂控制学说了。
在20世纪20~30年代,《课堂管理》是教师培训的经典教材。1907~1927年,这套书重印了30次。巴格利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养成能够满足工业化流水作业需要的好习惯,理想的教师应该是确保“在学生习惯养成的各阶段中都能完全‘遵守纪律’”,而理想的学校就是一切都只能遵循严格的规章行事。巴格利认为,一个课堂观察专家能够通过“在课堂生产线某个环节上教师的表现”迅速测量出教师的能力。[98]
他发现大家都同意应该让学生保持整齐的进步步伐,因此他建议采用兰喀斯特式(Lancasterian)保持队伍步伐一致的方法。他强调,应该训练学生按一定顺序摆放课桌,到黑板前固定区域发言或板书练习,按照规定程序离开教室,按照顺序到衣物寄存室领取外套。为了避免学生打断教学活动,他提出“应该训练孩子形成对某些常规的身体反应。”他建议,学生在休息时间去操场玩耍之前,先要排队使用厕所。他还督促教师训练学生形成对教师命令的注意:“通常,‘注意’这个命令应该成为引起学生特定身体姿势的刺激。”他提出,学生理想的身体姿势是:“脑袋挺直,眼睛直视教师,双手或手臂抱紧(前者更可取),双脚踏在地板上,立即停止其他所有作业或活动。”[99]
很多教师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班级教学,他们愿意接受巴格利的建议以维持课堂的秩序。作为当时最流行的课堂管理体系,这种方法是对桑代克教学法的补充,而与社会教育者提倡的教学法相去甚远。但是,老师在课堂中现实采用的教学法是非常灵活的。拉里·库班(LarryCuban)在1920~1940年对纽约市学校的课堂活动观察发现,小学中41%的课堂采用的是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混合的教学方法。完全的教师中心教学法占整个教学时间的27%,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占32%的教学时间。库班发现,在高中的课堂和教学中也有类似情况。他发现,那个时代丹佛市比纽约市更多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而华盛顿特区的教学方法更接近于纽约市。
库班对那个时期教学的研究结论是,教师根据所处的环境和各自的教育哲学,选择各种教学方法。问题是,这么多种教学方法往往是冲突和矛盾的,例如:很难协调或结合杜威与桑代克以及那些强调学生中心教育的教学方法。库班认为,那个时期的教师为相互矛盾的“效能、科学、儿童中心以及权威性等概念”所困扰,结果就成了“教师将这些相互竞争甚至矛盾的方法勉强凑合在一起,但是(我只能推测)对教学目标、课堂纪律以及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感到迷茫和不安”。[10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