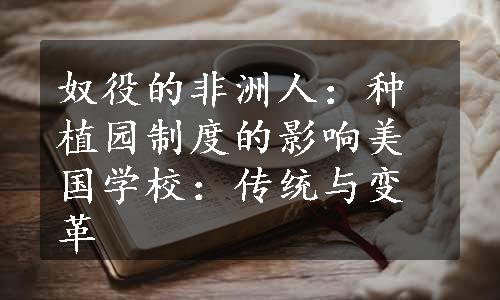
在18世纪,种植园制度开始从切萨匹克湾地区的烟草种植区向卡罗来纳的大米种植区,逐渐地向南部偏远的棉花种植区发展。种植园制度于12世纪起始于地中海的蔗糖种植区,这里的主人不仅使用白人奴隶,也使用黑人奴隶。这种模式被移植到了美洲的蔗糖、烟草、大米和棉花种植区,16世纪在巴西出现。所有这些农作物都可以由小农种植。与小农相对照的是,种植园制度涉及大批有组织的工人耕种大片的土地。这种类似工厂制度的种植园中心是所大房子,周围有工作间、谷仓、窝棚和奴隶的住处。种植园主向监工发布命令,监工则在工作间和田间指挥着有组织的劳动力。纪律和秩序是使得这种等级制度运行的关键。
与北部殖民地的奴隶拥有者不同,种植园主使用鞭打和其他残酷的惩罚来控制非洲奴隶。假如他们的惩罚造成了奴隶的死亡,南部殖民地的法庭不会控告种植园主。种植园主生活在不断的担心之中,担心他们的奴隶要么逃跑,要么起来反抗主人。他们相信残暴是控制的关键。
去文化(deculturalization)也被认为是使得非洲奴隶依赖于其主人的关键。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对奴隶的需求引起了奴隶贸易者深入非洲的内陆地区,强迫人们远离村庄和家庭。购买了一个非洲奴隶之后,种植园主们要做的首要事情是给该奴隶一个新的名字,以此剥夺他或她的身份。大多数新买的非洲内陆的奴隶不会说英语,所以种植园主和监工通常不断地重复某个名字,一直到非洲奴隶意识到该名字代表着他或她的新的身份为止。
去文化过程一直伴随着居住在类似于兵营结构中的新买的奴隶。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植园的新人经历着语言上的孤立。他们不可能与其主人沟通,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通常也无法与其他奴隶交谈,因为他们并不享有共同的语言。被奴役的心理创伤和被运输到美洲,加上更名和语言隔阂,使得新被购买的奴隶与其原有的身份、村庄、部族和家庭隔离开来。
种植园主很少提供有组织的英语教学。因此,种植园中非洲奴隶不得不创造一种沟通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被主人、监工和其奴隶同伴所理解。非洲奴隶还不得不创造一种互动的模式,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非洲文化背景,一直与婚姻、家庭关系、财产、儿童扶养、友谊和社会地位相关的传统文化类型相隔离。(www.zuozong.com)
去文化并没有导致种植园奴隶融入到欧洲文化中去。第一代成员带来了其非洲遗产的所有标志,其中包括发型、纹身和锉牙。当种植园主发现奴隶具备再生产的经济价值后,支持土生土长的非洲奴隶快速增长。像非裔美国人一样,种植园奴隶中的第二代放弃了其父母外在的身体上的记号,很少给其后代取个非洲的名字。其父辈的话语、姿势和语言形式都适应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关涉生与死的仪式也把非洲传统的做法和种植园生活的要求混合在了一起。
非洲奴隶与掌握其生杀大权的主人和随时对其施以酷刑的主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的文化风格。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奴隶无法受到来自法律机构的保护,使其免受主人的酷刑,主人可以强行和任何奴隶发生性关系。主人有权破坏家庭,从父母的身边抢走子女,并出卖他们。[48]
非洲奴隶中形成的口头交流传统,为弥补在奴隶制中的失落感提供了心灵的避风港。奴隶们在劳动期间、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时间、在宗教活动期间唱歌。他们歌曲的抒情性反映了奴隶创造一种文化的努力,这种文化是与非人的生存条件相一致的。在《黑人文化与黑人的自觉意识:从奴隶到自由人以来美国黑人的民间思潮》一书中,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总结说:“奴隶们的口语传统、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宗教观……至少潜在地构成了一种文化避风港,这种文化避风港能够保护其个性免受奴隶制某些最为糟糕的摧残。”[49]
艾拉·伯林(Ira Berlin)把这种去文化和文化转变的结果描述为并不是“同化到欧洲人的理想中去。黑人仍然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保持其非洲的生活方式,以及被白人观察家谴责为偶像崇拜和迷信的礼拜方式。假如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被引诱趋向于基督教的话,而老一代对它却没有多少热情。的确,非裔美国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导致了一些白人观察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非洲人和欧洲人在生活方式上没有调和的余地。”[5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