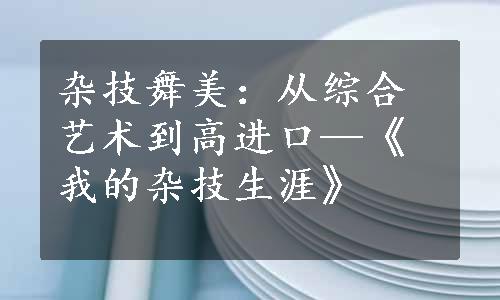
高进,1944年出生于上海,浙江萧山人。中国舞台美术协会会员,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杂技团二级美术设计师。1961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设计专业本科学习,1966年毕业,1968年分配到上海杂技团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工作。为《杂技园里百花开》《驯熊猫》《百戏春秋》《顶碗》《跳板蹬人》《驯象》《驯狗》《驯猩猩》《魔术师的约会》《变脸》《百鸟朝凤》《百戏春秋》等节目设计制作布景、道具、灯光及人物造型,多次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金奖。
采访人:高老师,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高进:我叫高进,1944年在上海出生,我的祖籍是浙江萧山。1961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念的是舞台美术系设计专业的本科。我们进校时正逢周本义老师从苏联留学回来,学制从4年改成5年,本来1966年应该毕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拖了两年,所以一直到1968年才被分配至上海杂技团,主要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工作。
采访人: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高进:我家庭环境还可以,5岁就开始上学。家里订有报纸,报纸上有些漫画、图画,我喜欢经常看看。小学二年级,也就是1950年的一天,学校发了一张白纸,说今天是图画比赛,全校每个人自己画张图,随便怎么画。我就画了一张,有一个大手,上面写着“不许动”,下面画了一个小特务,正在点燃地雷。这张图画交上去以后,得了年级第一名,奖励了我一副蜡笔。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绘画天赋,业余时间经常照着报纸画画,并形成了爱好。
我高中在光明中学读书,高二半工半读到工厂去劳动时,工厂老师傅问哪个同学会画画,我说我会。他就叫我去画黑板报、宣传画,我画的也得到了老师的称赞。所以高二的时候我就定了目标,我想如果一辈子搞绘画倒也是不错。高三毕业前,学校公告栏里贴了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我当时想考上海美专,但没有看到美专的招生简章,结果看到上海戏剧学院里有个舞台美术系,也是画画的,我就想去试一下,能考上就去,考不上就算了。考前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到图书馆去找怎么样画铅笔画的书,知道写生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些连环画,知道创作是怎么一回事。
戏剧学院考试时,考的就是一张写生,另一张是命题画,就是创作。写生考的是画静物。命题画的主题是“上海的早晨”。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画了一条小河,河上有船,船上放了一筐筐蔬菜,还有一个农民摇着橹把蔬菜运到上海,远处楼房和工厂的剪影衬在红色的曙光前。后来我进了学校看到这张画被评了一个五分,虽然我写生水平不怎么好,但是创作水平还行。
进戏剧学院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当时考的人不少。第一关初试后要到戏剧学院去看红榜,有点像看状元发榜一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第一关下来,留下了大概五十个人,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心里怦怦跳,既紧张又兴奋。然后就考文化课,我也通过了,接着就是到面试这一关了。面试我的是舞台美术系的党支部书记,他给我看了一幅冼星海在陕北采风的油画,我就讲了一讲,可能与主题内容比较吻合。接下来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就叫我回家等通知了。
我那天还在外面玩呢,回家后母亲说我被录取了,我完全没想到。我本来以为我戏剧学院是考不上的,因为我水平并不怎么高,自己心里没底。结果一下子录取了,高兴得要飞起来了。
采访人:学校教学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师和事情?
高进:当时整个学校的教学气氛很好,老师教学都很认真。我们的专业课老师有周本义、丁加生、陈景和、王挺琦,学院里还有闵西文、杨祖述、胡若思等很有实力和名望的画家。我们班主任丁加生老师从一年级一直带到我们毕业分配。当时他年轻,我们也年轻,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而且他很儒雅,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生气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同学……”,底下他就不说下去了。很遗憾,他已经去世了。
进戏剧学院前夕,学校寄来通知要买油画材料。我当时也没画过油画,就买了一本《怎样画油画》,还买了各种油画颜料、画纸、从HB到6B的铅笔。回来后临了一张列宾的《给土耳其苏丹王的信》里一个老头的肖像。因为我以前在工厂里面临摹过宣传画,就按照书本上讲解的步骤临了一张,一看蛮像的,自己觉得还不错,那时候自信心就慢慢树立起来了。初学绘画的人,学了一年以后自己觉得好像天下可得,但是三年以后就寸步难行。真正到三年级的时候,看的东西多了,觉得要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需要提高。尤其进了戏剧学院,看的书也多,图书馆里的外国画册,主要是苏联写实主义的绘画,我们常常借来看,对我影响也最大。
除了基础课,学校里还给我们安排了舞美设计、艺术欣赏、中国古典文学史、哲学以及戏剧理论等课程。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课外学习的机会,就是每个月能观摩戏剧和电影,青年话剧团、上海人艺和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我们基本都看过。所以我说进了戏剧学院,又能画画,又能看戏,那时候真是很开心。
采访人:从1961年进校到1966年毕业,正好遇到“文革”,当时毕业是怎么分配的?
高进:1965年冬我到嘉定锡剧团实习,基本上开始独立工作,搞了一个小戏,从设计到绘景再到体现。1966年4月份回学校,“文革”即将开始了。按理我们应该写毕业论文,搞毕业设计,接下来就是毕业分配。但“文革”一开始,这个步骤全部被打乱了。当时有一个杂技剧《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在杂技团参加舞台美术设计工作,还有一些表演系、导演系的同学参加编剧、报幕,音乐学院的同学搞作曲和伴奏。在我毕业分配以前,这个剧已经基本成型在演出了。当时上海杂技团“革委会”主任感觉到需要有舞台美术人员充实进来,所以主动到戏剧学院来要人。他只要一个,后来说分配两个,他说能来两个也很好,我们就被分配到上海杂技团了,也蛮高兴。
采访人:进了杂技团以后马上投入工作了?
高进:我1968年进入杂技团工作的时候,这个剧组正好在市革委礼堂演出。我一报到,他们马上就叫我去绘制幻灯片。当时幻灯片上的主席像颜色褪掉了,蓝天白云的蓝颜色也已经不蓝了,所以我进了上海杂技团以后就没有过渡,一下子就投入了工作。
后来运动就开展到剧团了,我们参加了剧团的运动,到交大集中进行斗批改,再后来又下乡劳动。就在这期间,外事任务来了,马上把我们从农村调上来,准备招待外宾的演出。“文革”十年,上海杂技团完成了不少重大任务,从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塞拉西皇帝、到中美建交前接待尼克松,我们上海杂技团都是主场。演出的上半场一般来说是民乐、交响乐,或者舞蹈、样板团的清唱,样板戏外宾听不懂,情绪就下来了。下半场我们杂技团的锣鼓一响,一看第一个节目,他们的精神就振奋起来了。到最后全体演员谢幕时,背景天幕上打了一个大标语,整场晚会的演出气氛就烘托出来了。
招待外宾的演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最后要打一条红色的标语,比如尼克松来的时候,就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候就要打“中柬两国人民友谊万岁”。这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标语,所以市委外事工作组很重视。我负责完成演出的幻灯制作,演出的时候必须要我去把那些灯片插好,因为换了其他人可能会把灯片插倒,插的时候是要倒过来插的,这样投影上去才是正的。如果不知道的人,把灯片正的插上去,打出来的投影就是倒的了。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幻灯机的灯泡,万一要用时不亮了就麻烦了,所以在开演前都要试一试,而且要准备好第二套方案。当时很重视这些事情,到最后一刻底下看的人也担心,我们也担心,希望不要有什么问题,万一有情况,就是政治事件了,所以大家都很仔细。
当然招待外宾就不能像《一月革命胜利万岁》那么演了,我们重新选了一些节目,《蹬伞》《顶碗》《转碟》《双人技巧》《倒立技巧》《爬杆》《古彩戏法》《单手顶》《水流星》,还有《大跳板》。在发掘这些节目的时候也是不容易,因为一下子又要把传统的东西搬上舞台,服装还是“文革”以前的服装,一看就很陈旧,于是整个剧目都要进行包装。
采访人:当时对哪些节目进行了包装,请您举例说说。
高进:在选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争论。比如像《蹬伞》,这个节目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演员躺在椅子上蹬一把传统的花布伞,服装也比较简单,有的同志就说这个节目太陈旧了。但是大家看了还是觉得这个节目蛮好,演员技巧也不错,最后还是让领导来审查。来审查的同志是外事组的,他看了以后说很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包装,演员个子比较矮,我们就在舞台上放了一个圆台子,上面是椅子,把大幕两边牵起来,搭成蝴蝶幕的样子。演员先是用脚蹬着伞玩耍,后来用脚一蹬,把伞蹬开了。观众看到的就是伞面,像车轮一样。原来用的花布伞比较陈旧,我们就改造了一下。伞面和伞里都画上了孔雀开屏的图案,很漂亮,而且孔雀的尾巴上面都粘上了亮闪闪的光片,伞转动以后灯光一打,闪闪发光,对节目而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所以整个节目就显示出时代特征。
周演吉表演的《蹬伞》,道具设计为高进
另外,《车技》节目原来的服装也是比较陈旧的,就考虑是不是改用运动服装。当时市面上都是红色运动服装,没有花色。后来考虑舞台演出总是要有些舞台色彩,增加美感,徐秀娣就想到可以改变材质,选用羊毛衫。我们就到羊毛衫厂去进行试样。羊毛衫厂有个样品车间,听到我们要去搞演出服装,非常配合,协助我们试制面料,试下来之后有一种叫四平空转的面料,颜色好看,又能织出装饰条纹,还不会变形。当舞台上十几个小姑娘在车上表现孔雀开屏的动作时,一个亮相一下子显得色彩缤纷,靓丽动人。这就是把舞台美术体现到杂技里面去,为杂技节目增添了光彩。
邱家班的班主邱胜奎是南派《古彩戏法》的代表人物,他能从大袍子里变出鱼缸、长生果,最后还变出一个小孩。我记得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他的徒弟姚振才说他会演,那怎么演呢?大家就开始集体创作。我们编排了新的形式,设置了蒙古草原的背景,就好像在蒙古包外面接待亲王一样。两个助演的小姑娘穿了顶碗舞的服装。我们把姚振才设计成一个拉马头琴的老头,戴着皮帽,穿着大袍,徐秀娣给他化了老年妆,还给他贴了胡子,用松香加酒精把胡子一根一根贴上去。这次节目编排也是开创性的,既包括了背景,又包括了人物造型、服装设计以及歌舞表演。
《古彩戏法》演出前有一个铺垫,舞台上有两个空的罗圈,先将罗圈向观众交代,然后再从两个罗圈里变出一盆盆糖果、糕点……演员就端着盆子一次次地跑到西哈努克面前献给他,然后再变出一个酒缸,用手拍上去还“当当”作响,敲了以后又变出一个杯子,当场舀了一碗酒,洒给观众看里面是有酒的。然后向上方拉出一根用10厘米宽的纸条盘成的纸柱,一直拉到很高,接着拍散后洒在舞台上,五彩缤纷。纸条是请造纸厂切割好的,拿来的时候是一盘白纸,我们把纸染成彩虹一样的色彩。接下来从毯子里变出一个金鱼缸,里面有鱼,最绝的是变出两只活的小羊羔。《古彩戏法》的改造也很成功,整个气氛很符合迎接贵宾的场景。演出结束,西哈努克亲王到舞台上跟每个人握手,我也跟他握了手,他还送了一块金牌给姚振才。
当时演出主要是在中苏友好大厦里的友谊会堂,在舞台背景的设计上,我们考虑到杂技比较适合广场演出,所以就画了些蓝天白云等空旷的景色,包括有一些以衬托表演为主的吊景,还做了一个公园花坛作为挡灯片,主要的布景内容还是在幻灯片上体现,幻灯片就投影在天幕上。友谊会堂的舞台空间比较大,所以那个幻灯距离要缩短到最小的极限。(www.zuozong.com)
采访人:这些包装为杂技舞台增色不少。
高进:是的,这得益于在剧团实习工作的经历。在剧团体验生活的时候,从设计到绘景,包括所有的细节都是要我们自己独立完成的。当时布景画好以后要把布景剪出来,都是自己剪的。所以到杂技团工作,对工作内容还比较习惯,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完成。
上海杂技团原来也没有什么舞美班子,除了我们进团以前有一个年长的美工。他是广告公司来的,负责帮演员在服装上加一些图案,以及负责道具工作。我们去了之后添加了综合艺术的一些元素,强调了设计,根据每个节目的主题进行设计,赋予节目一定的意境。
高进设计的演出海报(1985年)
采访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杂技团也接到了同样重要的演出任务。
高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演出获得成功,基本上奠定了上海杂技团招待外宾演出的基础。之后一些重大的招待任务主要是由我们上海杂技团担任,包括1972年尼克松访华。整个舞台、灯光都是由我们上海杂技团负责的,舞台装置都是由我们去完成的。每场演出之前我们先要到友谊厅去装台,所以工作量蛮大的。除了灯光,演员还要去走台,因为这个舞台比较低,其实不是太适合于杂技演出。但是为了招待外宾,演员也克服了一些困难。最适合演的可能还是像《古彩戏法》《蹬伞》《转碟》《扯铃》《车技》这些节目,小节目比较好,但是大节目比较提气氛。《车技》节目在舞台上转一圈,舞台效果很好的。
演出前一天,我们整个团全部集中到浦江饭店。第二天,我们就坐专车来到友谊剧场。当时我在后台看到美国专门派来了电视转播车,周总理提出这个牵涉主权问题,所以外交部跟美国方面协商,虽然转播车是他们的,但是这段时间的转播权是我们买下来,再交给美国播出。这样,既保存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又把任务完满地解决了。那一台演出的确是比较严肃,整个舞台上大家认认真真地演出,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采访人:1973年上海杂技团出访欧洲,这个契机使得杂技舞台艺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进:1973年,上海杂技团又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上海市市委(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组织牵头到欧洲的巡回演出。为了这个巡回演出,专门把整个杂技团集中到文化广场,住在那里,练功也在那里。我们准备舞台道具、画布景等工作也都是在文化广场完成。经过这次访欧演出,杂技在舞台上通过运用综合艺术来表现的形式基本上成形了。
我记得当时还请程十发老师帮我们画海报。我专门去跟他沟通,他拍了《转碟》的照片回去,先画了小稿,再画了正稿送审,审查以后觉得国画的白色背景气氛不够,后来又请越剧院的黄子曦老师和人民艺术剧院的杜时象老师做了修改。我跟程老师说,你的画后来又改了一下,他笑着说蛮好,这是合作。当时程十发的处境还比较困难,能够接到这么一个任务,他也非常高兴。当时邀请了杜时象老师来帮着一起完成设计任务,我到人艺去画了一些布景,周柏春、姚慕双、袁一灵还在人艺舞美工场劳动,他们就帮我一起剪柳树上的一片片小叶子以及松树上的松针。所以,整个布景上又有挂景,又有网景,还有幻灯,这次任务是经过多方协助才圆满完成的,这是“文革”期间到欧洲的一次重大的外交政治任务。
采访人:第一次全国杂技会演,上海杂技团的节目在舞美方面有哪些突破?
高进:1975年,第一次全国杂技会演的时候我们把溜冰节目挖掘出来了。这个节目原来是法国杂技团1956年到上海演的,我小时候还去看过这个演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溜冰》和一个造型节目。造型节目就像我们的《柔术》一样,主要表现健与美。演员身上还擦了橄榄油,用彩色灯光投射着好像一座活的雕塑一样,很美。另一个《溜冰》,以前没有看见过,当时朱复正就到那里去学习了。它跟冰上的溜冰不一样,以前叫旱冰,是四个轱辘的溜冰鞋。朱复正和他的学生徐文静在圆台上表演,内容跟法国杂技团的表演差不多。
全国会演的时候徐文静再带她的学生李月云一起演出,她们俩像姐妹一样。这个节目中我们就加进了一些元素。考虑到溜冰的季节是冬天,而且两个少女像花朵一样美丽,所以我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采用毛主席的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中的诗意,取材数枝梅花作背景,天幕前还挂了朵朵雪花。原来表演用的圆台上放了一些玻璃杯作为道具,里面放了红颜色的水,后来换成了从玻璃厂定制的冰凌雕塑。她们在圆台上表演时就绕着冰凌旋转,所以一开场,雪花、梅花、头戴滑雪帽的少女、冰凌就构成了整个“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意境。1975年在北京会演的时候,当舞台大幕一打开,台底下就出现了轰动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以前杂技演出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艺术表演,有些外地杂技团可能连舞美创作人员都没有,而上海杂技团已经有了幻灯,再加上舞美元素,整个舞台表演就提升了艺术层次,从单纯的技术表演变成综合艺术的表演。
所以后来外地杂技团都到上海杂技团来学习,把我们整台剧目全部学习过去。演员很忙,我们服装道具人员也很忙,要接待一个个外地剧团。他们有些拍了照片回到自己团里制作,有好多还是我们上海杂技团帮他们做好,帮他们送回去,因为有些服装面料外地没有,所以服装组的任务也很重。
反正“文革”期间我们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从设计到体现,都要按照节奏工期来完成。有同志说,杂技不需要什么包装,也不需要什么布景。其实不然,每一个节目就是一台小戏。同样一个节目《顶碗》,如果是蒋正平的老师邱涌泉演,他是一套服装,到蒋正平演又是另一套服装,背景也要变,换了蒋正平的学生演,又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节目,但是换一个演员就是另一套服装、另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每个月就像车轮打转一样,这个节目完成,那个节目又跟上,其实是没有空的。
“文革”当中由于形势所迫,杂技团一直在舞台演出,但是舞台演出使得许多技巧性节目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大跳板》,最多演四节人,再上去就碰顶了;还有高空节目,必须到杂技场才能够表演。舞台演出有它的局限性,也有优势,即舞台综合艺术能够得以发挥。
“文革”结束以后,杂技团又开始重视技巧,发展技巧了,演出主要场地又回到杂技场。到外面巡回演出基本上是借用当地体育馆,除了演出服装和灯光是必需的,灯光大多以照明为主,布景就没有了,所以舞台布景综合艺术这一方面开始衰退。
高进创作的熊猫表演年画(1982年)
采访人:1996年杂技剧《百戏春秋》上演,这台戏在舞美方面有哪些亮点?
高进:《百戏春秋》中比较出彩的几个地方,一个就是演出前奏,观众进入剧场可以看到一道金色的画天幕。我是按照百戏春秋主题画的,上面的图案是汉朝的杂技百戏,有《顶碗》《串圈》这类节目,有些星星闪闪发光的。原来剧场大幕就不用了,开闭就用这道幕,再配上音乐就好像进入了远古时代。下半场穿越时空,开场时一束追光投射在大自鸣钟的钟面上,有个小丑,时针随着小丑的身体转动而走动,“嘀嗒,嘀嗒,当当当”。灯光渐明,舞台上跟着钟响慢慢进入现代场景。下半场主题叫“都市春秋”,一开场是《独轮车》《溜冰》这些节目,其中还有一段比较梦幻的串场节目。当时在幻灯上加了只薄薄的水缸,水缸里放了些小鱼,灯光一亮水缸暖和了,鱼就在里面游动。这个投影就打在天幕上,有一种电影的幻象感,观众蛮轰动的。当时还有个魔术节目,两根魔棍会在空中跳动,带有些舞蹈色彩,这个背景比较出彩。最后谢幕时,满天金花飘落下来,十分灿烂。我利用转轴,在当中放了些金银彩色纸屑,滚桶一转,全部洒下来了,所以等到谢幕时也有些彩头。
《百戏春秋》这台戏是一出从编剧、导演、音乐、舞美设计到呈现都比较完整的舞台杂技剧,从创作初衷、演出编排到舞台感染力都有别开生面的效果。所以根据这个剧本后面演化出的《东方夜谭》《都市春秋》,最后发展到《时空之旅ERA》,实际上基本思路还是从穿越的角度出发,把整台杂技节目串联起来。当然每台节目导演不同,演员不同,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
采访人:回首这几十年的舞美工作,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高进:因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我进了杂技团,最后到要退休了,又回到了一个杂技剧《百戏春秋》,有剧本、编导、作曲和舞美加入,是一场比较完整的舞台剧,也算是一个轮回。
杂技走到现在,慢慢成为一种以杂技剧的形式进行表演的综合艺术,观众不再单纯追求惊险和刺激了,开始注重一种完整的艺术感染力。《ERA时空之旅》能够演到现在,经久不衰,与它本身的表演形式和综合艺术的参与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加入了多媒体以及灯光体系以后,广场杂技被融入崭新的时代空间当中。
(采访:柴亦文 整理:柴亦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