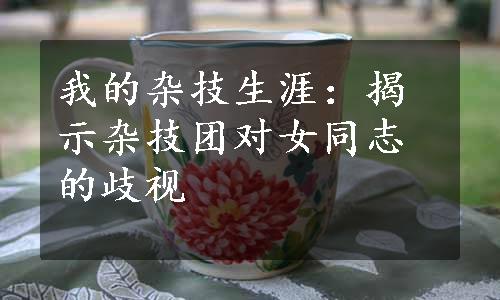
朱建平,1935年出生,上海人,国家一级演员。1942年加入邱家班学习杂技,1951年随邱家班加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主要作品有《晃板》《晃球》《造型艺术》《驯虎》等。1953年随上海文艺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1956年随团赴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演出。1960年《晃球》在上海青年文艺会演中获奖。1963年开始演出《驯虎》。1983年3月,带着节目《驯虎》赴北京和内蒙古、太原演出,引起轰动。后到上海马戏学校任教,1982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荣获“上海市园丁奖”。
采访人:朱老师,您几岁去的邱家班?
朱建平:我去的时候年纪很小,大概七岁都不到,什么事都不懂,父亲把我送过去,就在人家家里住着。七岁能学什么?太小了。等长大一些了,就一点点开始练杂技了。邱家也没有什么大人,有两个儿子,一个练杂技,一个不练,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姑娘,加上我一个,就我们三个人在家里练功,拿顶、下腰、压腿,一开始就是练这些基本功。
采访人:请您讲讲小时候练功的情况。
朱建平:邱胜奎老师负责我们的训练,他很严厉。我们在苏州一个公园里面练功,公园的后门有一个大厅,我们就在那里练倒立,他规定了倒立的时间以后,就到茶馆去喝茶了,到了时候他就回来了。日子一长,我们就能估算得出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一走我们就下来了,一看时间要到了,我们再上去。等他回来看到我们一个个都倒立得蛮好,还挺高兴的。但是时间一长,被他发现了,因为倒立这么久,你们怎么没有累的感觉?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发现就挨揍了。哪有小孩这么听话的?大人不在还老老实实地练,不会的。后来我们就不敢了,因为要挨打的。这样子一点一点地锻炼出来,等大一点以后,逐渐练成节目了,就慢慢地开始演出了。那时邱家班在苏州专门演堂会,就是老人过生日、年轻人结婚、小孩出生或者过周岁,请我们去演堂会。
采访人:邱胜奎老师他平时演出吗?
朱建平:他是表演“古彩戏法”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到了上海,在国际饭店演出。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成形了,比方说有《板凳顶》《滚杯》《地圈》。《滚杯》是一种柔术节目,四肢、额头、嘴,托着由许多玻璃水杯摞成的水晶塔。《地圈》就是将圈竖着叠起来,大家以轻巧的穿越技能,在圈中进出往返,表演各种动作。后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成立,他就带着我们一起加入了杂技团,当时有不少人,邓家班、邱家班,还有李殿起、李殿彦、王玉振,申方明、申方良兄妹四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建团的时候大概五十人不到。团长是文化局派过来的潘全福。
苏州邱家班时期的朱建平
采访人:到了人民杂技团,训练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朱建平:到了人民杂技团可以混合搭配了。比方说我的节目需要一个男孩,他不是邱家班的,而是王玉振的徒弟刘君山,我们就可以一起配合训练和演出,节目更加精彩些。
采访人:您那个时候主要是演《晃板》?
朱建平:主要是《晃板》,《晃板》这个节目好像是到了杂技团才有的,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节目,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这个创意。下面是一个长的圆筒,一块板放上去,底座站在板上,人要保持平衡,我头顶上面站一个人再表演动作,两个人还不能掉下来。后来日子长了,就变成三个人了,一个底座,两个尖。
采访人:《晃球》跟《晃板》名字听上去差不多,是一回事儿吗?
朱建平:不是一回事。晃板的下面是一个长的圆轱辘,要晃也就是两边晃。晃球就是一个球,四面都会动,一不行就会滑出去,球上面再要搁块板,人还得站住,这个难度就高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提倡艺术创新,尤其杂技表演,我们也看了外国的杂技节目,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杂技团的节目,借鉴他们的东西,在里面加一些自己的技巧。田双亮在国外看到过这个节目,他跟我说,你可以试试。我们说晃板已经不容易了,晃球难度更大。
1951年建团初期的《晃板》,底座为朱建平,尖子为刘君山
采访人:您是怎么练的?
朱建平:只有多练,先扶着东西练,要摔也就是在原地摔,不会摔到很远。因为我有晃板的基础,有腿部力量和平衡感,时间长了就站住了。
练好站稳了以后,我上面还要再加一个人,两个人就更困难了。因为我脚底下是个球,本身就在晃悠,上头再站个人,既要掌握上面的平衡又要掌握下面的平衡。《晃球》这个节目当时只有上海杂技团有,别家没有。中国杂技团只有《晃板》没有《晃球》,因为难度太大。你要把难度再发展上去也很困难,所以只有两个人表演,我和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杂技团已经有学馆了,我把学生叫过来一起演的。《晃球》这个节目在1960年青年会演时就得了奖。
1960年上海青年文艺会演节目《晃球》,底座为朱建平
采访人:1953年您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前线演出时有遇到危险吗?
朱建平:我是1953年3月去的,在朝鲜待了八个月,到年底停战以后回来的。我们大概是属于第三批去朝鲜的,我和刘君山两个人搭档表演《晃板》。我们晚上就睡在防空洞里,那个时候人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害怕。有的时候外面飞机在轰炸,志愿军都坐着不动,我们也照常演出。后来说不行了,飞机轰炸太危险了,就停下来不演了。
采访人:1956年您参加出访东欧的演出,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
朱建平:那次演出我们去了差不多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他们先来中国访问演出,然后中国艺术团回访。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为之前飞机出过事故,所以艺术团没有坐飞机而是坐火车。等到我们的演出任务基本要完成了,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正好在布达佩斯停下来休息,中国外交部就把我们带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在那里碰到了上海京剧院的出访队伍,是周信芳院长带队到莫斯科演出,我和我爱人在苏联碰的头。那会儿我们俩刚结婚,刚结婚一个礼拜就出国了,结果在苏联又碰到了。
采访人:人民广场的大篷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
朱建平:1958年我们开始在大篷演出,训练也在那边。如果人民广场第二天有游行活动,那么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马上就要把大篷拆掉,第二天游行完了再搭,是蛮累的,而且都是我们演员自己装台。有的时候拆完了没地方睡觉,只能躺在地上,游行完了马上就要搭起来,晚上还要演出。春节的时候最多一天演了五场,早上起床,把一天要吃的东西带好,那时候也没有食堂给你做饭,挺艰苦的,但是没人喊苦,也没有人提条件,一个都没有。
采访人:您什么时候开始驯兽的?
朱建平:好像是1955年,先驯狮子,后来驯老虎。那时候提倡创造新节目,有人建议是不是驯点动物,领导说好吧。最早是驯狗、驯猴子这些小动物,然后就想驯大型动物。因为大型动物只有西郊公园有,杂技团跟他们商量第一批先驯狮子。狮子小时候像猫一样大。我驯动物之前已经有一个女同志在驯了,但是缺一个帮手,领导就把我调过去帮着她一道驯。“文革”期间就不让搞了。“文革”以后,我的搭档被调到外地杂技团了,剩我一个人没法演了。我师父说你到学馆来当老师吧,你不懂我教你。我说我不当老师,我当老师不行。后来团长说驯老虎没人,你去吗?我说去就去吧,就那么一句话,我就到动物组驯老虎去了,那时候我已经46岁了。
朱建平驯狮
采访人:之前您驯过狮子,再驯老虎,是不是比较容易上手?
朱建平:驯狮子的时候主要是配合别人,这次驯老虎是我一个人单独完成,以我为主了。从西郊公园拿来的小老虎,我把它慢慢养大。开始我到西郊公园去跟它们熟悉,公园里的饲养员把它们牵出来,我每天到公园里和它们玩,熟悉了以后,我就带回杂技团开始训练了。它们刚拿来时就一点大,两只小老虎,都是我们自己喂的,动物园会告诉我们给它们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小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就像养个小猫小狗一样,大了以后不行了。
采访人:它们跟您亲吗?
朱建平:亲的。亲归亲,但是人总归要防它一手,毕竟是老虎,它咬你一下蛮厉害的,它是咬着玩的,但是你受不了的。跟我最亲的那只老虎就是峰峰,比较温和,所以我演的喂老虎吃饭、跟它亲嘴什么的,都是跟峰峰演的,它还会跟我撒撒娇,舔舔我。另外一只老虎凯罗就不行,脾气坏。(www.zuozong.com)
采访人:您是在慢慢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性格差异的吗?
朱建平:接触时间长了就熟悉了,晓得哪一只老虎脾气比较好,你教它学东西学得快,它脾气好你也容易跟它接近,你越跟它接近,它也越跟你亲近。
采访人:老虎“跳圈”“踩球”,这些动作是怎么训练的?
朱建平:饿的时候驯它,驯的时候棍子上插一块肉,看见我有肉它就跟我走,今天让它坐在凳子上,坐好了我给它吃块肉,它要吃就要听指令,形成条件反射。
采访人:训练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措施吗?
朱建平: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我们手里就是一根鞭子,还有一根电棒。不过电棒一般不用的,你用电棒它以后看见你就害怕了,就不听你的了。
采访人:您给它指令它能听懂吗?
朱建平:时间长了它听得懂,你喊它名字它也晓得。一喊它名字它头就回过来了,跟养小猫、小狗一样,老虎就是比较凶,实际上也一样的。
采访人:我们看到您和老虎表演的“衔肉喂虎”,觉得非常惊险。
朱建平:我把肉叼在嘴里它会过来舔掉,有一次它咬到我的下巴,虽然没有咬破,但毕竟是这么尖利的牙齿,万一它一用劲,会把我的下巴颏给咬掉的。所以后来这个动作我就不演了。
采访人:您和老虎相处中还有什么小故事吗?
朱建平:有一次峰峰发高烧演出,高烧很厉害,也不吃东西了。还好演出前就发现了,它病得都起不来了,后来要上场了,它好像知道自己要注意形象一样,一下子打起精神来,很感人的。演完以后,我跟兽医两个人都陪着它,守了它一晚上,给它打针。第二天好了还照样演出。
1984年9月7日上海《文汇报》报道朱建平表演“衔肉喂虎”
朱建平和老虎峰峰
采访人:您拍电影还受了伤,这是怎么回事?
《老虎钻圈》
朱建平:我受伤是在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导演要我驯老虎跳圈。我手里拿了个大的圈,让老虎从圈里跳过去,拍完一条,导演说再拍一次,没想到出事情了。跳第二次的时候,老虎用劲用小了,它可能觉得够不到对面的台子,半空中想借个力,我的头正好在它爪子下面,它的爪子一搭我的头,我眼睛附近就被抠了一个洞,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马上把老虎关起来,把我送医院。它只是想搭一下借个力,但是人给老虎搭一下哪儿受得了。它这个爪子平时是缩在里面的,非常尖利,要用劲了就会伸出来,它轻轻搭了我一下,我就进医院了。那时候到医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出门就有汽车。那时候没有车,我们单位对面有一个食堂,是用买菜的车把我送到广慈医院的。
采访人:有没有后怕?
朱建平:我们习惯了,受点伤没什么,你也不能怪它,左一遍右一遍地让它跳,跳太多了它也累的。
采访人:后来您缝了多少针?
朱建平:缝了26针,用眼科针缝的,比较细,而且医生缝得很好,基本上没有落疤,现在看不出来,痊愈了还是照样演出。
采访人:您还有一个“扛虎”的动作,老虎体形那么大,又很重,怎么扛呢?
朱建平:让它站在两个凳子上,我跑过去,从它肚子这里一扛。它的两个爪子靠过来,它的头在这儿,舌头还舔我手呢。
采访人:您还参加过消防类节目的演出,请您介绍一下。
朱建平:主要是爬大绳,还有用一根竹竿,人站在竹竿两头,后面的人用力推,前面的人手撑杆子,然后脚蹬墙上到楼上去。我们先是去淮海路嵩山路的消防队去体验生活的。有一次他们出任务去救火,我也参加了。还有一次在外滩的演习,在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和对面的一幢大楼之间拉了一根绳子,然后爬过去,挺惊险的。南京路上好多人在看。我们有一根保险绳就钩在绳子上,要是摔下去就会吊在空中,可以保护我们掉不到地面上。那时候杂技团不拿我当女同志用的,当男的用的。我不像一般的小姑娘娇滴滴的,干活都很细致的。
朱建平表演“扛虎”
采访人:后来您离开舞台去做老师了?
朱建平:80年代我还在演,后来因为年龄关系,我就去教学生了,当时成立马戏学校,正好缺老师,我就去了。
采访人:您们小时候训练挨过打,新社会肯定是不能打学生了,但是学生不认真学怎么办?
朱建平:现在的学生肯定不能打的,不好好学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杂技这门艺术还是很吃功夫的,但是我的两个学生还不错,条件也好,比较好带,很听话,也很聪明。开始练不好也没关系,慢慢练,多练几次就好了。后来她们都改行了,不过逢年过节她们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
(采访:柴亦文 整理:李丹青)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