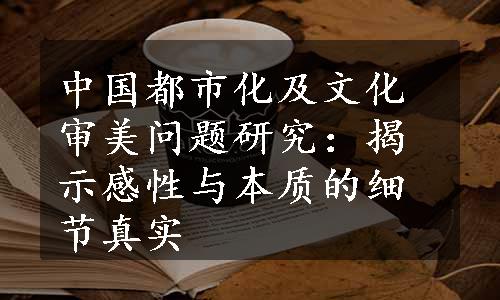
从文本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的角度,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叙事与思考,主要集中在南京、杭州、扬州与苏州四城市。要想深入了解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书写的价值,首先需要对古典江南城市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在总体上表现为政治型,以历史上的北方都城与重要军事城市为代表,它们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最重要的基础与核心,同时也再现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深层结构与主体框架。与北方城市不同,推动江南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主要是城市经济功能,这是我们在以往江南城市研究中取得的基本认识与判断。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深的矛盾,对于政治型城市而言,其首要功能在于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以有效地稳固其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因而传统政治中心一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经济型城市的规模与实力。而经济型城市则相反,其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因而在城市性格上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由此可知,江南城市自始就生存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夹缝与矛盾中,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的矛盾及其相互缠绕关系,是江南城市社会建构与文化生产始终无法摆脱的“命运的魔咒”。一方面,由于主体政治机能的不发达以及现实中政治军事资源的相对不足,因而无法成长为真正的政治中心成为江南城市普遍的命运与气数。另一方面,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国家政治等方面有所建树,使得“欲罢不能”和“欲说还休”一直是江南城市在古代中国的深层矛盾与困惑。在“政治主导下的经济城市”这一基本定位明确之后,与之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可以表述为,由于江南城市与北方政治中心的远近关系与亲疏态度不同,因而后者的影响又直接表现为前者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城市性格与精神气质。像这样一些细部的差异与只有微型叙事才能把握的文化特征,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即使没有被完全地忽视掉,也基本上是不受重视的。因为,“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为核心的实证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人口、空间等‘硬件’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6]与之相反,正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才使这种最感性、也最本质的“细节真实”大白于世,并为人们重新认识与研究江南城市社会提供了新的资源与独特的人文学术语境。
与北方和中原文化浓烈的政治色彩与实用价值取向不同,江南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整体氛围在于:“这是一片过于柔软的土地,本身就不适合铁石心肠的政治家来耕作和培植。”[7]但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密切关系,任何政治家也都不可能放弃这块“嘴边的肥肉”,因而,对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江南城市,既需要在现实世界中竭力处理好与北方政治中心的关系,以便在弱肉强食和虎视眈眈中获得苟且偷生的机会,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被扰乱和破坏了的内心世界重归平静,即通过精神生产与价值观念的改造达成对现实命运的理解与接受。在这两方面,南京与杭州是典范。南京与杭州(诸暨)最早分别是吴国与越国的都城,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称霸一时、与北方列强相拮抗的光荣历史。由于“是非成败转头空”等原因,最终都选择了“不谈政治”的诗性生活理念,这是它们作为江南城市的相同之处。由于地理、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江南诗性文化的同一框架下,两者在内涵上又表现出微妙的差异,并被“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的现代作家捕捉到文字中。
以杭州为例——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就是婚丧生死,一大半也重在仪式。丧事人家可以出钱去雇人来哭。喜事人家也有专门说好话的人雇在那里借讨彩头。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无非是为了一个架子,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弄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郁达夫《杭州》)
以南京为例——
七、八年前,湖里几乎长满了苇子,一味地荒寒,虽有好月光,也不大能照到水上;船又窄,又小,又漏,教人逛着愁着。这几年大不同了,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但长堤宛转相通,却值得走走。湖上的樱桃最出名,据说樱桃熟时,游人在树下现买,现摘,现吃,谈着笑着,多热闹的。
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似乎人迹不多。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楼相仿佛,但窗外的景象不同。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山下一片滴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若许我再用画来比,这怕象王石谷的手笔了。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你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窗外的光景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一上楼便什么都有了。夏天去确有一股“清凉”味,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又可口,又贱。(朱自清《南京》)
对这些文字进行细读不难发现,除了共同的热闹、快乐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南京更有一种“于游戏中自有谨厚之气”,[8]这是一种经过更大的风雨、见过更大世面才有的烈士暮年的苍凉与超然世外的寂寥,它不易流露出来,也不易被外人所察。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城与政治中心的关系还有深浅之异。杭州基本上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等于从根本上剔除了城市固有的军事与防卫功能,因而更容易臣服于现实的安排与命运的摆布。古代如此,如法国汉学家描述蒙元入侵前夜的杭州:“没有理由说此一时期乃是纷扰的时期?……大多数人并未被这一重大的历史灾变所动,除非有朝一日他们亲身卷入其中。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手执权柄、其爱国心又强到足以使他们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优哉闲哉。”[9]现代依然,“杭州号称天堂,自然有构成天堂的条件,首先是它交通经济地理的重要,扼钱江的咽喉,是浙东平原丰富产物的集中市场。它的地理形势为兵家所必争。但是在历史上却又没有经过许多剧烈的战争,平均起来,承平的日子多,这就大大的有益于居民的安逸感。杭州人通常都喜欢‘耍子’,这风气要追溯到历史上奠都偏安时期,当时政治风气,以及生产的条件都对享乐有利,于是就成为一种习惯般的流传下来。我在‘一二八’时候曾经住在杭州,熟习了城厢生活情形,许多高大旧式住宅中间,曲折的穿插着许多街巷。这些高大住宅中居住人依附什么为生活,我不能明白地知道,但是生活的悠闲从容,却是令人羡慕的。”(任微音《雨丝风片游杭州》)
与杭州的“低眉顺眼”不同,南京是那种不甘就范的“失路英雄”。首先是地理环境不同,杭州一马平川,大海阻断了东方的退路;南京不仅有长江天险,还有“龙盘虎踞”的防守条件,正如诸葛亮当年在清凉山感慨“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南京在自然条件上完全有可能雄霸江东半壁江山。其次,从城建史的角度看,南京一开始就是军事中心,大约在2500年前,吴王夫差以南京为作坊开始制造青铜兵器,称为“冶城”。大约在22年后,卧薪尝胆的勾践灭吴,继续于此制造兵器,改称“越城”。与杭州等江南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商业经济活动不同,南京则是以一种国家兵工厂的方式登上中国城市舞台的。再次,从城市文化上看,杭州的文化构成比较简单,越地一带的江南文化是其要素与核心内容;南京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要冲,其城市文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远比普通江南城市突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香君与苏小小的差别,两者尽管都是流落风尘的女子,但她们在政治态度与抱负上却截然相反。以普通市民为例,杭州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堪为以细腻著称的江南文化精神的典范;南京人则素以“大萝卜”自况,“它的本义是说南京人的朴实与缺心眼,这与操着吴侬软语、做事认真细致的苏杭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们假想中像苏州评弹或者越剧《红楼梦》中那样的儿女温情,在南京文化中不仅不存在,甚至还是南京大萝卜们经常嘲笑的对象。”[10]这些可与现代作家的书写构成一个“阐释学循环”,一方面,作家的感觉、情绪、心理与审美表现固有的模糊性,借助这些对城市历史与传统的“文化研究”可以获得知识上的明晰性;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与准确地理解了不同江南城市在形态与结构上的差异,才能发现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书写所具有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价值。
由于地缘、移民与文化的影响,南京自然有浓郁的江南文化韵味,但它在来历上与杭州等城市却判然有别。在江南城市群中,南京是最政治化的一个。但由于每一次的努力与挣扎均以一部金陵痛史为终结,因而逐渐积淀出了十分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气质。一方面,与江南城市相似,南京不断地经受着从文明中心到政治边缘的历史驱逐,但由于不同于普通江南城市的自然条件、城市规模与政治地位,使南京很难像杭州一样以“西湖虽好莫题诗”严格自律;另一方面,与北方都城相似,南京不断遭到战争的考验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由于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使它很难像北方都城一样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因而又总是要与国家机器发生重要关联并一次次卷入政治旋涡的中心。罗素曾说:“德国哲学思想中的许多仿佛奇特的东西,反映出一个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剥夺了它那份当然势力的精悍民族的心境。”[11]对于南京也是如此,既不可能脱离政治中心太远,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因而,它精悍的心境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参与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这给南京带来的是一种内涵更加复杂的城市精神与文化性格。与一般的江南城市相比,南京总是多几分由于政治风云而积淀的苍凉与悲壮,同时也因此而多了一些超越于“吴侬软语”之上的厚重与大气,其根本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如南京人有一句最喜欢的口头禅叫“多大事”,“所谓‘多大事’,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或者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时候人们想不开,被各种欲望或者感情所困扰,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年轻、资历浅、不够成熟,没有经过惊涛骇浪或者暴风骤雨的人生洗礼。而在经历了真正的人世沧桑之后,其实人们所表现的常态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南京文化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代表。”[12]由于这种历史积淀与灵魂深处的底气,与杭州的真快乐与真逍遥不同,在南京看似快乐、中庸、热闹的江南外观下,深藏的是一颗充满悲辛、孤傲、慷慨之气甚至于绝望的灵魂。要理解南京城市精神与文化性格,《儒林外史》是一个不可能绕开的文本,特别是最后一回描绘的那幅惨淡的士人画面,也可看作是现代南京城市命运与气数的最好写照。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闻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之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扬州在现代已相当衰落,这与它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地位是严重不相称的。这座在隋唐时期即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市”,其繁华的商业城市景观,大约只有北宋都城汴梁可相提并论。扬州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恰好印证了芒福德关于“城市是磁体”的观点,即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在它还没有任何东西可容纳之前,它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它就毫无生命可言。”[13]同时,也正应了柏拉图《法律篇》所说的,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14]一旦城市最基本的磁体功能衰退,丧失了对人口、资源与资本的吸引力,一个城市离它解体的末日就为时不远了。对于扬州而言,如同许多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一样,一旦城市的交通与商业功能衰退,各种寄生性的文化服务与消费产业凋敝,原来纷至沓来的大量城市人口与富可敌国的财富随之四散而去,“门前冷落鞍马稀”则是十分自然的结局。如果说扬州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江南运河的开凿,那么,导致其衰败的原因则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古运河的取代。现代作家尽管不直接研究城市兴衰,但同样以诗性智慧的方式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做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www.zuozong.com)
在交通因素的背后,扬州兴衰还与城市性质相关。如同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一样,古典中国的商业城市也是最缺乏保护的,一旦其实用价值丧失,就不会再有任何政治资本投入其中,这是人们感叹“扬州衰败何其速也”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作为城市繁荣直接制造者的商人也不无干系,他们只会享受城市,而不可能为城市的兴衰,以及他们投入大量财富创造的城市文化负责。这既与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也与这一阶层的普遍素质有关,前者使他们无力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城市资源的调配,以挽救或减缓城市衰退的命运或步履,后者则可归结于他们只是一群附庸风雅的文化消费者,所以最可惋惜的无疑是扬州文化的凋敝与衰亡。如果举一个例子,最有意思的是丰子恺先生。因为教孩子读《扬州慢》词至“二十四桥仍在”,他再也按捺不住对维扬“烟花三月”与“十里春风”的冲动,并决定立刻带着孩子们去寻访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但实际情况是——
到大街上雇车子,说“到二十四桥”。然而年青的驾车人都不知道,摇摇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却忠告我们:“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你们去做什么?”我不好说“去凭吊”,只得撒一个谎,说“去看朋友”。那人笑着说:“那边不大有人家呢!”我很狼狈,支吾地回答他:“不瞒你说,我们就想看看那个桥。”驾车的人都笑起来。这时候旁边的铺子里走出一位老者来,笑着对驾车人说:“你们拉他们去吧,在西门外,他们是来看看这小桥的。”又转向我说:“这条桥以前很有名,可是现在荒凉了,附近没有什么东西。”我料想这位老者是读过唐诗,知道“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他的笑容很特别,隐隐地表示着:“这些傻瓜!”
车子走了半小时以上,方才停息在田野中间跨在一条沟渠似的小河上的一爿小桥边。驾车人人说:“到了,这是二十四桥。”我们下车,大家表示大失所望的样子,除了“啊哟!”以外没有别的话。一吟就拿出照相机来准备摄影。驾车的人看见了,打着土白交谈:“来照相的。”“要修桥吧?”“要开河吧?”我不辩解,我就冒充了工程师,倒是省事。驾车人到树荫下去休息吸烟了。我有些不放心:这小桥到底是否二十四桥?为欲考证确实,我跑到附近田野里一位正在工作的农人那里,向他叩问:“同志,这是什么桥?”他回答说:“二十四桥。”我还不放心,又跑到桥旁一间小屋子门口,望见里面一位白头老婆婆坐着做针线,我又问:“请问老婆婆,这是什么桥?”老婆婆干脆地说:“廿四桥。”这才放心,我们就替二十四桥拍照。桥下水涸,最狭处不过七八尺,新枚跨了过去,嘴里念着“波心荡冷月无声”,大家不觉失笑。(丰子恺《扬州梦》)
实际上,直到今天,关于二十四桥到底是二十四座、第二十四座,还是指二十四桥风月,依然是一个有待发微的文史之谜。而最可叹息的是当代人复制的二十四桥,仅以二十四根栏杆表示,不仅设计理念通俗,建筑风格与气势也无可褒奖之处。
与总想成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一心一意过小日子的杭州,以及不知明朝梦醒何处的扬州相比,最像江南城市的还是苏州。不仅因其在明清时代就已发展为“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15]以及它在当代长三角都市群中依然占据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规模与空间资源、自然环境与文明水准、个体的物质欲望与审美需要相互协调与平衡,因而苏州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或者说很好地体现了芒福德“城乡文化和谐是城市的灵魂”的理论。在芒福德看来,“人类的文化发展在超过了新石器时代所到达的水平之后,有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敞开的——走村庄之路。或者走城堡之路:或者,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一条是共生(symbiotic)之路,另一条是掠夺(predatory)之路。这并非绝对的选择,但它们的确通向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前一种是自愿合作,相互适应的道路,包含了广泛的交流和理解:其后果将是一种有组织的联系,具有更复杂的性质,较之于村庄社区及其周邻地区地带居于更高的水平;后一种则是一种掠夺性的控制之路,它通向无情的剥削压榨,最后到达寄生性的生存方式:这是扩张之路,充满暴力、斗争和忧虑,它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集中和榨取剩余资料’的工具”。[16]芒福德还特别指出,“第二种形式……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进程”,是城市文化功能的严重受损,直至走向解体与衰亡的主要原因。而理想的城市社会无疑应是城乡环境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或者说,一个城市继承与保存的乡村资源与文化越多,其在更大的程度上也就守护了城市的本质与灵魂。这可以通过比较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加以深入认识。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习俗。”[17]而现代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使自身逐渐退化为一个展览权力与商品的巨型陈列场,其本质上是“人工改良的物质外形往往最终包含着一个失败的、精神衰弱的城市”。[18]
对苏州而言,尽管城市化进程开始得很早,但与西方现代城市在发展模式上有很大区别,在中国农业文明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双重背景中,不仅它的城市化进程从未与乡村生活方式产生严重的对立,同时其新兴的城市文明与文化传统也是水乳交融、相互和谐的。苏州园林及其特有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最杰出的代表。“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不是因为苏州园林在规模与豪华上超过了北方的皇家园林,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城市政治与经济功能的新城市空间,并为大自然和古典乡村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保留了足够的地盘,使一种多元化的江南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在空间生产上作为政治与权力的延伸,还是延续自然景物与心灵的自由,是江南园林与北方园林的根本区别。
北方园林,我们从《洛阳名园记》中所见的唐宋园林,用土穴、大树,景物雄健,而少叠石小泉之景。明清以后,以北京为中心的园林,受南方园林影响,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自然条件却有所制约,当然也有所创新。首先对水的利用,北方艰于有水,有水方成名园,故北京西郊造园得天独厚。而市园,除引城外水外,则聚水为池,赖人力为之了。水如此,石,南方用太湖石,是石灰岩,多湿润,故“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多姿态,有秀韵。北方用土太湖、云片石,厚重有余,委婉不足,自然之态,终逊南方。且每年花木落叶,时间较长,因此多用长绿树为主,大量松柏遂为园林主要植物。其浓绿色衬在蓝天白云之下,与黄瓦红柱、牡丹、海棠起极鲜明的对比,绚烂夺目,华丽炫人。而在江南的气候条件下,粉墙黛瓦,竹影兰香,小阁临流,曲廊分院,咫尺之地,容我周旋,所谓“小中见大”,淡雅宜人,多不尽之意。落叶树的栽培,又使人们有四季的感觉。草木华滋,是它得天独厚处。北方非无小园、小景、南方亦存大园、大景。亦正如北宗山水多金碧重彩、南宗多水墨浅绛的情形相同,因为园林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正与诗画相同,诗画言境界,园林同样言境界。北方皇家园林(官僚地主园林,风格亦近似),我名之为宫廷园林,其富贵气共存,而庸俗之处亦在所不免。南方的清雅平淡,多书卷气,自然亦有寒酸简陋的地方。因此,北方的好园林,能有书卷气。所谓北园南调,自然是高品。因此,成功的北方园林,都能注意水的应用,正如一个美女一样,那一双秋波是最迷人的地方。(陈从周《园林分南北 景物各千秋》)
在陈从周先生的论述中,除了清晰可见的南北园林之差异,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南北文化、审美趣味在园林建造上的相互渗透与取长补短。而其在深层与齐鲁伦理人文与江南诗性人文的对立互补原理是一致的。
伦理人文与诗性人文分别代表着中国民族两个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有了江南文化中的诗性主体,“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才开始获有了一个坚实的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均衡:一方面有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有了这种可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使得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了它们的自由。”[19]
这也是南北园林在相互取长补短之后可以相互辉映甚至是平分秋色的根本原因。
由于越来越彻底地遗弃了古老的乡村文化,现代城市严重败坏了人们希望在城市中过美好生活的夙愿。对当代江南城市而言,迅速的城市化、大城市化过程,在给这一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现实矛盾与精神生态问题。如2007年发生的无锡蓝藻生态灾难与长三角城市普遍存在的奢侈消费倾向,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苏州的传统城市空间与文化功能已有不少变异,一些现代城市的坏习气也在某些方面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想拍一张全景,要想绕开作为现代生活标志性风景的电线杆就很不容易。但与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苏州城市化的代价又是最小的。如它的旧城区保存得相对完好,如它的市民与前工业化时代依稀相仿。这是今天在苏州还可以重温“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旧梦,以及普通中国人在这里能够找到家园感的根本原因。
“阿要白兰花啊——”,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
“阿要白兰花啊——”,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陆文夫《深巷又闻卖米声》)
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褶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余秋雨《白发苏州》)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人想到古人对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埃及都城波拉美西斯的描述:“居民的生活美好;当地的田地中好的东西应有尽有;它每天都有食物和各种供给,池塘里有鱼,湖泊中有水鸟。草滩上长满绿茵茵的青草;河岸种植着椰枣树;沙地上长满西瓜……谷仓中满盛着大麦和小麦,简直堆上了天。园田中有食用的蒜和葱韭,还有莴苣,果园中栽植了石榴、苹果、橄榄和无花果,甜酒赛过蜂蜜,城里的运河中生长着鱼,这些鱼以荷花作食料……居住在城中十分快活,听不到有人抱怨。”[20]
这也许可以说明,美好的城市生活从来都是相似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