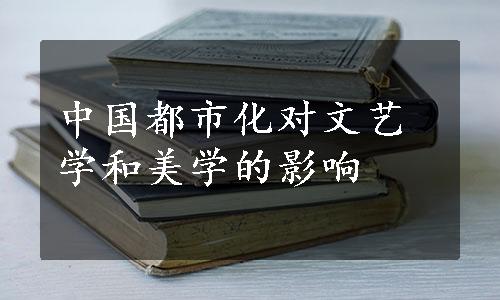
从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看,可以说它们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它的主要问题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必然表现。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往往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同时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之一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是这同时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都市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真正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早已存在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两者之间的桥梁,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可以将个中原因略述为二:
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文艺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粹学术研究”,它的一个具有基础本体论性质的命题即众所周知的“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可以说它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始终是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其学术主流。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言而论,但这种文艺学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的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郁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文学是人学”这个基本命题中,由于“文学”中的“文”在当下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中的“人”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论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是不存在任何学理问题的。
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上看,众所周知,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被看作“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这个看法源于他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把“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先生所做的解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11]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领地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领域中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价值问题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研究为中介,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基因,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暴风雨中奋力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www.zuozong.com)
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理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使社会科学摆脱它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灵动,同时也为人文学科飘飘然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大地。在这个崭新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环与互动,从而催生出一门以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这不仅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大方向,也是文艺学、美学可以介入这个领域的合法性根据。而从实践的角度看,通过引入作为文艺学天性的“情感本体”与作为美学本质的“诗性智慧”,为都市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一种诗性原理与审美原则,这对减少或改造当代大都市生活的拥挤、忙碌、机械、枯燥等异化性,显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却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而建立起来的。从学理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应纳入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工程科学之下的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区域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也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文学从“文学研究”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文学,对后者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相比之下,文化批评更关注的是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它们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也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去解释中国文学,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其次,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的研究,他们将文艺学、美学的基本理论运用于对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进行解释与批判,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或大摇大摆,或暗度陈仓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同时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刘士林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同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中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取得了双赢效果的。再次,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一向是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基本特色。但受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研究“文化学转向”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的引进,在这个原本平静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典籍做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公允地说,也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其实,由于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三门二级学科,其他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本身,也是应予以关注与思考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