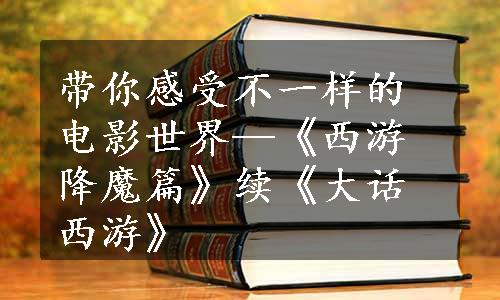
周星驰出生不好,早年是个“跑龙套的”,后来慢慢地,他就成了中国喜剧的无冕之王。在观众那里,他天生就有搞笑的禀赋。“无厘头”一词,就是经由他发扬光大的。从香港传到内地,“无厘头”成了一种特定的喜剧表现方式。什么是“无厘头”呢?这个词来自粤语,原意是“没来头”,可以解释为“没有缘由”“没有头脑”“无缘无故地”“莫名其妙地”,等等。演员在表演时,突然地故意演技变差了,或者莫名其妙地来一段与剧情无关的台词,又或者突然地与观众直接对话起来。比如,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突然与华夫人演上一段推销鹤顶红的广告;《大话西游之大圣取经》中,罗家英饰演的唐僧突然翻唱上一段英文歌。这样的例子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数不胜数。
“无厘头”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先从“表演”的最一般的定义去理解。“表演”就是呈现出一种形象。演员演技之功力的标准是“像不像”。有句话说得好:好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糟糕的演员则演什么都像自己。也就是说,在优秀的表演中,演员没有“自己”;不仅如此,他还要不留痕迹地把“表演”的过程本身抹去,看上去就像是真的而不是演出来的。那么“无厘头”呢?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表演区别在哪?周星驰在“表演”孙悟空吗?不太像。《西游记》原著的孙悟空并不作为原型,周星驰的表演的根本目标也不在于“像”。毋宁说,“孙悟空”只是周星驰的道具,被用作为表演中的素材。这如何可能?一个演员自称在表演孙悟空,可是他又表演得不像,但观众们却觉得他演得好,这如何可能?因此“无厘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相反,在无厘头中“无厘头”本身被解构与重组了。无厘头表演刻意加重了“表演的痕迹”,让观众直接看到“表演”本身;周星驰表演的是那个周星驰本人表演的孙悟空。这套玩法的结果是奇妙的,其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个多面体。《大话西游》中的那个孙悟空是周星驰的孙悟空,换言之,周星驰既表演了自己,也表演了自己表演的孙悟空。观众们不得不觉得,这样一个孙悟空只可能是周星驰的,换作别的演员,不管他表演的功夫如何,他呈现的形象也只能是另一个。
1.《大话西游》中孙悟空带上紧箍的那一刻,他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2.《西游降魔篇》完美地还原了《西游记》小说中的孙悟空的真实形象
这时,我们再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周星驰不仅只是个表演笑话的人,“无厘头”给予作为演员的他另一种本质。一般的喜剧演员,善于讲笑话,但观众们不至于把演员本人与演员所呈现的形象混淆在一起。优秀的喜剧演员在荧幕之外可能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周星驰呢?他可不仅仅在表演啊,他也在表演自己。在无厘头中,他还把自己贡献出来。在《喜剧之王》里,周星驰表演一名喜剧演员,被感动了的观众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电影里,周星驰才是真实的。这意味着,那个不处于表演中的、现实里的周星驰便是虚假的。
再转念一想,无厘头毕竟还是表演,周星驰与至尊宝不一样。周星驰本人与周星驰表演的周星驰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博尔赫斯不可能真的就把自己写进书里。那么,真正的周星驰是谁呢?这个不断在表演中取笑自己的男人到底是谁?
这时我不由地想起电影《守望者》中的那个关于笑匠的笑话,这个笑话是关于笑话本身的:
我听过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去看医生,说他很沮丧,人生是如此无情和残忍,他说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上觉得很孤独。医生说:“这病很好治,伟大的小丑——帕格里亚齐——就在城里,去看他的演出吧,你会振作起来的。”男人嚎啕大哭。“可是医生”,他说,“我就是帕格里亚齐。”这笑话真不错,大家都笑了。鼓点响起,幕落。
周星驰就是那个伟大的小丑。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表演出来的周星驰”,他也把“自己”讲在笑话中了。那个真正的周星驰是不会笑的。并不是周星驰老了,他笑不动了;也不是因为周星驰知道了世界上所有的笑话,所以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新笑话能让自己笑起来。他不笑,是因为,只要他一笑,他就在自己所讲的笑话中。(www.zuozong.com)
在这个意义上,在《长江七号》之后的第五年,《西游降魔篇》上映时,当得知“周星驰本人”并不在电影中时,观众们不由地悲伤起来。在一片“还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呼声中,观众们热情高涨。电影在2013年的贺岁档上映,拿下当年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头名。观众们的热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周星驰本人”,尽管早已得知星爷本人并不出演,但人们还是期待在电影里重新找到他的形象;其次是“大话西游”,1995年的那部《大圣娶亲》的结尾,周星驰冷静得像条狗。观众们也许觉得,那个让至尊宝带上金箍圈的人正是自己,因而欠下的那张电影票就是为了还给周星驰一个至尊宝。可能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游降魔篇》的初衷,才能忘记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部优秀电影。也只有如此,才能把电影票还干净了。
《西游降魔篇》中也充满了许多奇怪但有趣的笑料,以及诡异的造型和人物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唐僧是一位驱魔人。但他只有一腔道理可讲,却没有一身武艺。降魔路上,他遇到了鱼妖、猪妖,还有当年大闹天宫如今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在另一位驱魔人段小姐的帮助下,唐僧感化鱼妖,收入门下成了沙悟净,又将猪妖降伏做猪八戒。唐僧手中有一本《儿歌三百首》,用来唤醒恶魔的初心。妖怪本不是妖怪,只是被“邪恶”迷了眼才看不清自心本善。再凶恶的人都可以被感化,只要恶魔放下执着,回归本心,重拾初衷。
与1995年的《大话西游》相比,《西游降魔篇》在叙事结构上不再花哨,故事也没有那么复杂,情感上也不再那么炽烈。相反,它讲了个简单的故事,一个简单的道理,以及一份克制住了、淡化了的感情。无厘头的表演方式更多的是一种重复,显得刻意又无趣。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主角的至尊宝,最终是带着一份遗憾上路的;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不再是主角,他的遗憾与执迷不再是核心,相反,主角是那个讲着大道理的唐僧。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想,至尊宝也许明白了,也许还是执迷不悟,不管如何,他还是不得不踏上取经路。那个周星驰是无法自己解脱的,他的金箍圈终究只是戴在头上。他并没有真正被降伏,还是一个心中多有怨念与不忍的妖。那最深又最难以解脱的执念一直在头上。至尊宝虽然不在了,但孙悟空也没有一身轻松地上路。最终,他也没有给自己一个解脱,他还是一个妖,而且是个大妖;与受困于外在的恶的小妖相比,受困于自身的大妖将更难降伏。在这个意义上,《西游降魔篇》的主角就不可以再是孙悟空了。仅凭着自己,孙悟空得不到拯救,他越是要救自己,救下彩霞仙子,紧箍咒就念得越紧,他毫无出路可言。因此《大话西游》之后的孙悟空未必已经准备踏上西天取经的路,需要再来一部《西游记》前传,再来一次真正的解说,《西游记》的故事才能开始。降魔人不能自己心中还有一个魔。
再回到一个不会笑的笑匠周星驰那里。为什么星爷本人不再出演《西游降魔篇》了?他老了吗?也许,我们可以替星爷再讲一个笑话,好做最终的交代:
“我听过另一个笑话,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笑话大王讲的。医生说,他刚刚听了小丑讲的笑话,那小丑自称是伟大的帕格里亚齐。他说,人生很沮丧又无趣,他讲了一辈子笑话,却不曾听过别人讲笑话能有他讲得好,所以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听过别人讲笑话的人。多悲哀啊!笑话大王这样回答医生:医生啊,那些听伟大的帕格里亚齐讲笑话的人未必不悲哀到哪儿去。曾经,帕格里亚齐讲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自那以后,听笑话的人在听别的笑话时,都在想着,怎么没有那一个笑话好笑了?从那个最好笑的笑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真的笑出声来啦!”
这就是周星驰的信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仰,一种宁愿让自己遍体鳞伤也要继续坚持的信仰。这一信仰在《西游降魔篇》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