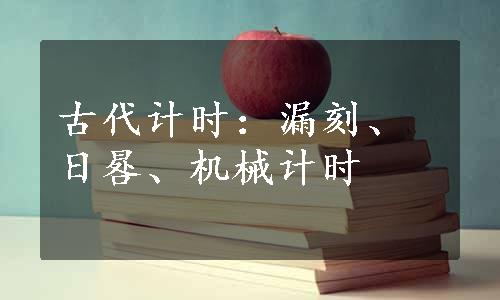
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早使用的时间单位应当是“日”。太阳是全世界人认识时间的第一个标志物。先秦时期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的升与落是一日劳作和休息的标志。由昼与夜组成的一天,则是一年的基本单位。汉字中,“旦”字表示太阳刚刚升起,把“旦”倒过来就是古体字的“昏”。随着先民们认识的深入,白天和黑夜又被细分。《左传》记载“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这种划分一日为十时的方法,应当和古代传说羲和生了十个太阳相关。后来普遍流行的是一日为十二时辰的分法。
另一种等时制是把一天均分为一百等份,即百刻制,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计时法,其产生年代尚无定论。但关于百刻计时的资料,既有文字记载,也有出土文物印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指出“昼夜百刻”,东汉马融注解《尧典》时说:“古制刻漏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这里所讲的古制,当指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汉以后历代都将十二时辰和百刻制配合使用,但一百和十二不可通约,因此,各个朝代的配合方案常有改变。
中国古代人说时间,白天与黑夜各不相同,白天说“钟”,黑夜说“更”或“鼓”,因此有“晨钟暮鼓”之说。古时城镇多设钟鼓楼,晨起(辰时,现在的7点)撞钟报时,所以白天说“几点钟”;暮起(酉时,现在的19点)击鼓报时,所以夜晚说“几鼓天”。夜晚说时间也有用“更”的,这是由于巡夜人边巡行边敲击梆子,以点数报时。从酉时(现在的19点)起,巡夜人敲击手持的梆子或鼓,称为“打更”。全夜分五个更,19点至21点一击,为一更;21点至23点两击,为二更;23点至凌晨1点三击,为三更;1点至3点四击,为四更;3点至5点五击,为五更;之后天亮了,不再打更。“夜半”或“半夜”之说一般是泛指,如夜半歌声,没有实指几点时唱,而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唱;若要实指,就得在“半夜”前后加字,那就有实指了。如三更半夜,实指了三更。又如过了半夜,实指“过了”,这时就有说法了:夜的一半在什么时间?在正三更处,即子时四刻,就是现在的零点整。另外,古代军队营寨里也有打更的,不过敲击的不是木制的梆子,而是金属的梆子,叫作“金柝”。《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有“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诗句,这里的金柝即刁斗,三足一柄,白天用以烧饭,夜晚用以打更。在“更”之下,有个名叫“点”的专用时间,一更分为五点,差不多是现在的24分钟。三更两点,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深夜11时48分。
汉代日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时”以下的计量单位为“刻”,一个时辰分作八刻,每刻等于现时的15分钟。“刻”以下为“字”,关于“字”,粤语地区和闽南语地区至今仍然使用,如“下午三点十个字”,意思是15时50分。据语言学家分析,粤语中所保留的古汉语特别多,原因是古代中原人流落岭南,与中原人久离,其语言没有同留在中原的人一样“与时俱进”。“字”以下又用细如麦芒的线条来划分,叫作“秒”。秒字由“禾”与“少”合成,“禾”指麦禾,“少”指细小的芒。秒以下无法画出来,只能用“细如蜘蛛丝”来说明,叫作“忽”。如“忽然”一词,“忽”指极短时间,“然”指变,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在极短时间内有了转变。
一日分为十二时辰,比日大一号的刻度是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月亮定期的循环变化,把月亮圆缺的一个周期称为一个朔望月,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朔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望日,为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从朔到望,是朔望月的前半月;从望到朔,是朔望月的后半月;从朔到望再到朔为阴历的一个月。一个朔望月为29天半,实际上是29天12小时44分3秒。出土的西周铜器金文上大量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种名称。关于它们的含义历来有许多争议,在古代大致有两大类解释:一种是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代表每月某一天或两三天,这叫作定点月相说。另外一种四分月相说则认为周代将一月分四份,每份一个名称。也有学者认为西周将一个朔望月分成两半,上半月称既生霸,下半月称既死霸,而初吉和既望则指新月和满月。另外,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一个月三个时段的名称,也是三种月相名,这种说法称为三点三段说。而初吉与月相无关,与其他三个术语有所区别。
北京钟楼内大钟
日和月因为太阳和月亮的循环变化直接看得到,但认识季节就有一定的难度。四季中古人最先认识的是春天和秋天,这是由于对农业生产来说,春种和秋收是最重要的。甲骨文中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夏”字。“冬”字虽然有,但表达的是“终”字的意思。大概因为古人更早熟悉“春”和“秋”的划分,即便在出现了“夏”“冬”后,有些古籍说起四时,也依旧把春秋连起来,把四季说成“春秋冬夏”。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被命名为《春秋》,应当就和这一古老的习惯有关。
“年”是我们生活中很大的时间单位,认识它就更需要对自然进行整体把握的思考能力。汉民族很早就发明了白天用立木测日影的方法,古人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发现了冬至和夏至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由此延伸出春分和秋分,在两分两至之上,又发展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最后发展成二十四节气。
中国古人认识一年的另一个途径来自夜晚对星星的观察。经过精密的观测,古人发现头顶的星空中,北极星永远挂在北方,而北斗七星按照季节不断地旋转,日落时,斗勺柄春天指东,夏天指南,秋天指西,冬天指北。聪明的古人于是把星空分成了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个星区,又在每个星区选出有代表性的七颗星,这就是二十八星宿。如果把一年的时间比喻为一个钟表表盘,那么北极星就是钟表的表芯,北斗七星就是指针,而二十八星宿则是周围的时间刻度。
依靠对于日、月、星的观测,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古人已经建立了对日、月、四季和年的基本认识。其中最体系化、最有代表性的是“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把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一分为三,并按时序分别选取三种物候编成,每一种物候都是可以作为时间变化标志的自然现象。
北京鼓楼曾设“铜刻漏”计时,现依据相关史料仿制后重置
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古人已经通过对天文地理的观察,基本掌握了大自然时间变化的秘密。这些有关时间的知识,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意义重大。一旦清楚了时间循环的链条,古人就可以预先知道大自然即将发生的许多变化,从而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年的生产和生活,并从中抽象出敬天顺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秦汉“晷仪”目前出土了三具,它们是一种功能不太明确的仪器,兼有定方位、占候等功能。关于晷仪的性质和用法众说纷纭,但应该是源于上古时候“立表测影”的圭表。立一根杆子,杆影在一天中的方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太阳方位的周日变化,利用这一点便可制成日晷,用来测量真太阳时。由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如果在一个圆盘的中央垂直立一根细棍(晷针),不就成了一个简单的日晷吗?再把圆盘加以改造,按晷针不同时刻在盘上的投影刻上刻度,晴天的时候放在外面便可计时了。
这样想想是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对古人而言却似乎困难重重,以至于又过了1000年,直到南宋,才出现“赤道式日晷”的清楚记载(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1176年)。这种日晷的晷针垂直于晷面且横穿晷心,晷盘平行于天赤道(也就是说,晷针的延长线正连接着南、北天极),正反面刻度相同。向北的一面用于春分到秋分这半年,余下的时间用向南的一面(春分、秋分时,太阳正好与晷面平行着经过天空,南北晷面皆无影)。晷影在晷面上的方位角和时角相等,因此晷影是落在等分刻度形式的时刻线上。
这里所描述的日晷是用木头做的;后来人们逐渐把木质改为石质的整圆晷面,以抵御风雨侵蚀。
古代保存下来的日晷都在西安,一具是小雁塔日晷,适用于从春分到秋分的夏季半年,算是尚不完善的赤道式日晷,年代约在隋唐(僧一行已描述过赤道式日晷的形态,但未流传下来);另一具大清真寺日晷,不清楚其用法,是一座可左右旋转的地平式日晷,可能与元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的交融有关。
另外,元代郭守敬曾创制半球形的仰仪,模仿天球,既能测天,也可用来测时,还能通过小孔投影来观测日食,避免伤害眼睛。但是元代中西交流通畅,此类日晷在西方十分古老(“球面日晷”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难以确定它的源流。这种仪器后被专门用作太阳时指示器,又称仰釜日晷,有两件类似的日晷分别保存在朝鲜和日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前陈设的青铜月晷
本土日晷在中国为什么发展如此缓慢?前面说了,“按晷针不同时刻在盘上的投影刻上刻度”,不就可以成为一个日晷吗?难就难在刻度上。只有当晷面与天赤道平行摆放时,晷针每天在盘上的投影才会均匀地改变方位角,也才能简单地按投影来刻制刻度线。
而其他样式的日晷,最常见的如地平式日晷,确定它的刻度就要用到投影几何知识——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所欠缺的。而赤道式日晷尽管安装比较复杂,但在刻度上则相对简单,因此,中国古代流行赤道式日晷,是很自然的。而这么晚才流行起来,部分可以归咎于天赤道这个概念较为抽象,不能脱离天球而存在;虽然东汉已有浑天说,但是其中不太明确的天球观念要深入人心尚需时日。
古代西方的日晷,样式要丰富得多。这是因为古希腊人对于球面坐标系统,以及这种系统所需要的球面几何学,都已经掌握(今天全世界天文学家统一使用的天球坐标系统,就是从古希腊原封不动继承的)。对于平面几何学,当然更不用说了。古希腊人还掌握了将球面坐标投影到平面上的方法,及这种投影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何学原理,特别是关于圆锥截面的知识。因此,古代西方的日晷不但有水平式的“平晷”,还有挂在墙上的“立晷”、面南的“天顶晷”等。这些种类多样的日晷在明末传入中国时被统称为“洋晷”,引起了当时人们极大的学习兴趣。
清代铜镀金提环式日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机械钟最早模拟的都是天球运动,因此也被称为天文钟。从张衡开始有水运“浑象”、浑天仪,它们本质上也是时钟装置。张衡以“漏水”驱动的浑象或浑天仪,能自动与天体的周日视运动同步,并通过“蓂荚”这个报时装置显示历日的推移。蓂荚传说是帝尧时代的一种植物,生长极有规律:每个朔望月的初一开始每天长出1荚,到十五共生出15荚;从十六开始,它又每天落下1荚,到月底,若该月为30日,正好全部落完。如逢小月多出1荚怎么办?这1荚就不会落下来,而是枯焦掉。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每一天是朔望月中的第几天,到月底还能知道本月是大月还是小月。
张衡仪器的主要功能是演示、占候,同时也具备粗略的报时功能。所谓粗略,是指一天只报一次而言,并不意味着不精确。事实上,要准确地推移历日,就得控制好误差累积,需要很高的精度。张衡的仪器可以被视为机械天文钟的始祖。
要使机械天文钟报出更精确的时间,就需要加入擒纵机构(一种机械能量传递的开关装置),周期性地控制、释放动力轮,使后者的连续运动变为可计数的间断运动。11世纪后期,北宋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已设计出了水轮的擒纵装置,使均匀的水流依次装满水斗,但是这个擒纵装置本身并不创造等时性,等时性仍然来源于水流的均匀性(吴国盛语)。
这与伽利略以来,基于钟摆的“摆动等时性”制造的机械钟有本质不同。因为单摆的小幅摆动近似简谐振动,周期只与摆的长度及当地的重力加速度有关,后者在地球表面上同一地点通常是不变的。从此以后,计时走上了依靠“稳定的振荡”这一条康庄大道,如立钟、座钟的钟摆振动,后来发展为怀表、手表里的摆轮振动,进而又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利用压电效应使石英晶体产生高频的机械振动——这就是今天最流行的民用计时仪器“石英表”。
提高振荡频率是改善精准度的主要途径,机械表在这方面无法与石英表比肩,渐渐变成了纯粹的奢侈品,不再以精度取胜。2017年出品的一款瑞士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将机械表的振荡频率提高到惊人的10.8万次每小时,每天误差仅1/4秒——仍远不如普通的石英表准确。
因此在整个古代,或者说在西方钟表传入之前,中国的机械计时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水流均匀性”的漏刻(具体器物名“刻漏”)计时。
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当政,开展了“太初改历”,于是当时呈现了一派繁忙景象:“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汉书·律历志上》)这正是中国传统时间计量的集中体现。
“漏刻”又可分开来讲,“漏”是指装满水的漏壶,“刻”是指一天当中的时间划分单位。“箭”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壶里面的浮箭刻度可以显示、计量一昼夜的时刻。根据漏壶或箭壶(详见下文)中水量的均匀变化及水面在箭尺上指示的刻度,就可以计量时间。(www.zuozong.com)
这里就产生出了两个大问题:1.怎么保证水量变化是均匀的?2.如何使浮箭刻度对应一昼夜的时刻?
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多级刻漏,实际上只需要两级。汉武帝初年的浮箭漏由两个漏壶组成:上面是供水壶,下面是受水壶,因壶内装有箭尺,通常也叫作箭壶。箭壶承接从供水壶流下的水,随着壶内水位的上升,安在箭舟上的箭尺也随着上浮,所以称作“(单级)浮箭漏”。
单级浮箭漏只有一个供水壶,要靠人工往供水壶里加水,总得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吧?没人能做到往供水壶里面持续地、均匀地加水,一刻不停,因此加水前后的水位就会有较大变化,导致流往箭壶的流量不稳定,因此计时误差较大。
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又在供水壶上面加了一个漏壶,使下面的漏壶在向箭壶供水的同时,不断得到它上面那个漏壶流进来的水的补充,从而使下面这只直接向箭壶供水的漏壶的水位保持稳定,这就是“二级补偿型浮箭漏”。自此,古人已基本上解决了漏壶的水位稳定问题。二级补偿型浮箭漏发明的具体年代已不清楚,可能是在西汉中后期。据唐徐坚《初学记》记载,东汉张衡使用的就是典型的二级补偿型浮箭漏。
当然,理论上,供水壶上面的补偿漏壶,本身也有水位稳定问题,似乎再往上增加漏壶会更好,这就是多级补偿型浮箭漏。于是晋代有了三级漏,唐代出现四级漏,补偿壶最多达到过六个。但实验证明,二级已足够稳定,三级、四级效果不明显,四级以上完全没必要。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受文化惯性影响了,它也确实激起了文化碰撞。
在古代中国,从一开始就与漏刻联系在一起的是“百刻计时制”:把一昼夜时间均匀分为一百等份,每份称为“一刻”。百刻制的每刻时间是相等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
这与我们今天说的“一刻钟”显然不同。按我们现在的习惯,一昼夜有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四刻钟,那就是九十六刻。但如果你以为九十六刻是一种现代习俗,那就错了。实际上,早在南朝梁武帝萧衍当政的时代(5—6世纪),就曾试图把百刻制改成九十六刻制。(以下参阅江晓原《天学史上的梁武帝》)而这是他决心做一个印度式的佛国君王、把南朝改造成佛国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梁武帝萧衍
作为一种独立的计时系统,中国传统的“百刻制”原本没有问题,但百刻制与另一种时间计量制度——十二时辰制之间,没有简单的换算关系,从而带来诸多不便。这种不便在梁武帝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只有汉哀帝时曾改行过一百二十刻——又在梁朝之后继续存在了1000多年,直到明末清初西洋天文学传入中国。
为什么梁武帝偏偏想到要改百刻制为九十六刻制?因为他是一位虔信佛教的君主,如用批评的口吻,就是“佞佛”。
梁武帝自登基之后,就开始不食荤腥,并坚持“日止一食,过午不食”这一佛教僧侣的戒律。如遇事务繁多,已经过了正午来不及吃饭,他竟漱漱口就度过这一天。梁武帝既然立志弘法,并且身体力行,在行动上以“僧戒”严于律己,因此对佛国君王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也极力模仿。根据史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对佛国君王作息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佛国君王的作息是用印度民用时刻制度——昼夜八时来安排的。虽然印度与中国都是用水漏来计时,但中国刻漏单位是将昼夜分为一百刻,而印度民用时刻制度则分昼夜为八时(或六时)。刻度单位不一致,就不能方便地按照佛经中所讲的正确时刻来行事。因此,在梁武帝看来,将百刻改为与印度八时(或六时)制有简单换算关系的九十六刻是非常必要的。
梁代以后,各代仍恢复使用百刻制,直到明末清初西洋历法入华。西洋民用计时制度为二十四小时制,与中国十二时辰制也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九十六刻制又被重新启用,成为清代官方的正式时刻制度。现今通行的小时制度,一小时合四刻,一昼夜正好是九十六刻——这正是梁武帝当年的制度。遥想梁武帝当年,焉能料到自己的改革成果,在一千余年后又会复活?
意味深长的是,梁代和清代两次改百刻为九十六刻,都受到了外来天文学的影响。清代受欧洲天文学的影响,梁代则受到了随佛教传来的印度古代天文学的影响。
梁武帝为表忠心事佛,四次舍身入同泰寺
知识拓展
中国古代时辰与现代时间的对比
古时候的中国人,将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刚好是今天的两个小时。从西周起,人们就为每个时辰取了优雅别致的名字,又以地支来表示。每个时辰名,或描绘了天地间一景,或阐明起居作息的道理。
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仪器——莲花漏
【子时】夜半,又名子夜、中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北京时间23时至1时)。
【丑时】鸡鸣,又名荒鸡,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北京时间1时至3时)。
【寅时】平旦,又称黎明、早晨、日旦等,是夜与日的交替之时(北京时间3时至5时)。
【卯时】日出,又名日始、破晓、旭日等,指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初升的那段时间(北京时间5时至7时)。
【辰时】食时,又名早食等,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北京时间7时至9时)。
【巳时】隅中,又名日禺等,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北京时间9时至11时)。
【午时】日中,又名日正、中午等(北京时间11时至13时)。
【未时】日昳,又名日跌、日央等,太阳偏西为日跌(北京时间13时至15时)。
【申时】晡时,又名日晡、夕食等(北京时间15时至17时)。
【酉时】日入,又名日落、日沉、傍晚,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北京时间17时至19时)。
【戌时】黄昏,又名日夕、日暮、日晚等,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将黑未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因此称黄昏(北京时间19时至21时)。
【亥时】人定,又名定昏等,此时夜色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北京时间21时至23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