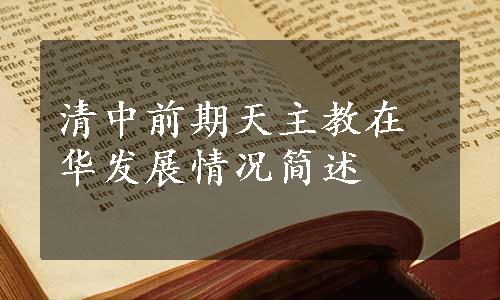
如果从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于1582年12月27日进住肇庆算起,到清1644年入关到北京时,天主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62年。由于汤若望很快地得到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信任,天主教在清初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664年时,耶稣会住院前后有38所,耶稣会士前后来华人数达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2]
清初杨光先通过历狱案将传教士排出钦天监后,天主教在华发展一度受挫,后经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努力,康熙皇帝对天主教传教士逐步怀有好感,这样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三人联名上奏,要求为汤若望平反,他们在奏疏中说:
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呈请礼部代奏。呈为:诡随狐假,罔上陷良。神人共愤,恳歼党恶。以表忠魂事。棍恶杨光先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痛思等同乡远臣汤若望,来自西洋,住京四十八载。在故明时,即奉旨修历,恭逢我朝廷鼎新,荷蒙皇恩。钦敕修历二十余载,允合天行,颁行无异。遭棍杨光先依恃权奸,指为新法舛错。将先帝数十年成法,妄谮更张。频年以来,古法件件参差。幸诸王贝勒大臣考正新法,无有不合。蒙恩命怀仁仍推新历,此已毋庸置辨。惟是天主一教,即经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为万物之宗主”……在中国故明万历间,其著书立言,大要以敬天爱人为宗旨,总不外克己尽性、忠孝廉节诸大端。往往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御制碑文,门额“通微佳境”。赐若望号“通微教师”。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不严禁?乃为光先所诬,火其书而毁其居,捏造《辟邪论》,蛊惑人心。思等亦著有《不得已辩》可质。且其并将佟国器、许之渐、许缵曾等,诬以为教革职。此思等抱不平之鸣者一也。
又光先诬若望谋叛。思等远籍西洋,跋涉三年,程途九万余里。在中国者不过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东,有何羽翼,足以谋国。今遭横口蔑诬,将无辜远人栗安当等二十余人,押送广东,不容进退。且若望等无抄没之罪。今房屋令人居住,坟地被人侵占。况若望乃先帝数十年勋劳荩臣,罗织拟死,使忠魂含恨。此思等负不平之鸣者二也。
思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狐死兔悲,情难容已。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冒恳天恩。俯鉴覆盆,恩赐昭雪,以表忠魂,生死衔恩,上呈。[3]
康熙八年九月五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这样在华的传教士扭转了杨光先“历狱案”以来的被动局面,远在广州的传教士也允许回到原来的教堂传教。1683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并被康熙召见,传教士在宫中的力量日渐强大,在日后与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积极斡旋,使中俄双方签下了《尼布楚条约》,传教士的这些表现终于使康熙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下达了著名的容教令: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4]
但此时在入华传教士内部争论已久的礼仪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从而严重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发展。1693年3月26日(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发布著名的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从此天下大乱,争论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这样关于中国教徒的宗教礼仪这个纯粹宗教的问题演变成了清王朝和梵蒂冈之间的国家问题,并促使梵蒂冈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和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先后派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和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两位特使来华,其间罗马教廷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5]铎罗使华以失败而告终,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圜时,乃奏请回罗马”[6]。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在看到嘉乐所带来的“禁约”[7]后说: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8](www.zuozong.com)
“礼仪之争”是清代基督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清代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既表现出了一种纯粹文化意义上的碰撞与争论,也使“清代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对外交往”[9]。
1722年康熙驾崩后雍正继位,由于传教士穆敬远在康熙晚年卷入几位皇子之间争夺皇位的政治旋涡,雍正对传教士心怀不满。在雍正禁教期间相继发生了福安教案和苏努亲王受害等事件,天主教陷入低谷之中。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世宗驾崩,由高宗践祚,乾隆对传教士的态度较之雍正有所改观,他对西学的态度也较雍正更为积极,这使得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环境有所改变。不少传教士在宫中受到很高的礼遇,如郎士宁(Joseph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戴进贤(Ignace Kogler,1680—1746)等人。但乾隆禁止天主教在华发展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这样先后发生了1736年(乾隆元年)、1737年(乾隆二年)和1746年(乾隆十一年)三次较大的教案。
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由于本文献截止到1748年(乾隆十三年),故1748年后清朝的天主教发展情况在这里暂不做研究。天主教在清中前期的发展呈现出由高到低的状态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它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个人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有关,“因人容教”和“因人禁教”是清前期基督教政策的重要特点。[10]康熙在文化态度上较为宽容,对西学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对天主教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这样,他必制定出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而雍正本身对西学并不感兴趣,又加之传教士卷入宫内政治斗争,成为他的直接政治对手,他实行严禁天主教的政策是很自然的。乾隆上台后纠正雍正严厉的政治政策,他本人和传教士也无直接的冲突,这样苏努一家的平反是自然的。而他本人对西洋技术又有较浓的兴趣,由此“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就成为乾隆对待西学的基本态度。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思想认识、决策措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取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受制于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也与他们的心态、性格、才能密切相关”[11]。
其次,“礼仪之争”是天主教在清代发展的关键事件,以此事件为转折点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呈现出了两种形态,这也是最终导致康熙禁教的根本原因,而这个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恐怕应该由罗马教廷承担”[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