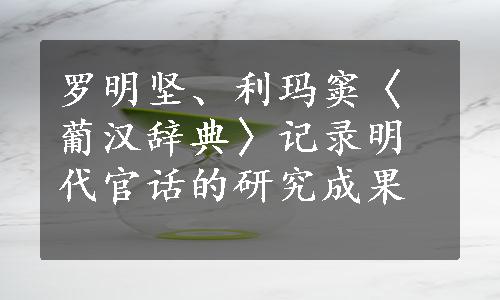
1986年,美国乔治城大学杨福绵先生在台湾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上用英文发表了《利玛窦的葡汉辞典:一个历史和语言学的介绍》(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1989年夏,杨福绵又赴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对该手稿原件进行了研究,并于1995年在《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发表了长篇研究文章《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杨福绵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葡汉辞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共同作品。
这部手稿的第32页至165页是《葡汉辞典》。这个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和词组、短句,大体按ABC字母顺序排列;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句。例如:
葡语词 罗马字 汉语词
Aguoa scioj 水
Aaguoa de frol zen sciãscioj 甑香水
Bom parecer piau ci 嫖致,美貌,嘉(“嫖”为“标”之别字——杨注)
Escarnar co gio 割肉,切肉,剖肉
Fallar chiãcua,sciuo cua 讲话,说话
杨福绵先生认为,根据手迹来看,罗马字注音为罗明坚手迹,汉语词条“大概是罗利二氏的汉语教师或其他文人书写的”[20],但手稿从第32a页至34a页的第三栏,汉语词后加上了意大利词条,“从笔迹上看似乎是利玛窦加的”。(www.zuozong.com)
手稿第3a页至7a页《宾主问答辞义》内有这样的问话:“客曰:师父到这里已几年了?答曰:才有两年。”根据字典末尾的一个拉丁文附记,杨福绵认为手稿形成于1585—1588年间,定稿于1586年6月,而后“很可能是罗氏亲自带回罗马去的”。根据杨福绵的统计,手稿中收入葡语词语6000余条、汉语字词5460条,其中有540多条葡语词语未填汉语对应词。例如Aguoa benta是“圣水”(英文为Holy Water),但当时在中文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只好暂缺。
第二,《葡汉辞典》是汉语拼音的早期方案。
按照时间推论,《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拼音系统是中国最早的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以后才有了利玛窦在《程氏墨苑》中提出的方案。罗马注音系统的真正完成应是1598年,即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失败后,坐船返回南京的途中。利玛窦说:“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套中文发音表,这对后来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帮助。他们发现,中国话全部是由单音字组织起来的;中国人利用多种不同的音调来区分多字的不同意义,若不懂这些音调,说出话来就不知所云,无法与人交谈,因为别人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他也听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神父们选定了五个音标,使学生一看就知道该是哪个音。中国字共有五音。郭居静神父在这方面贡献很大。……神父们决定,以后用罗马拼音时,大家都一律采用这五种符号。为了一致,利玛窦下令,以后大家都要遵守,不可像过去那样,每个人一种写法,造成混乱。用这种拼音法现在编的字典,及以后要编的其他字典可以送给每位传教者,都能一目了然。”[21]
正因为《葡汉辞典》是罗马拼音的早期方案,作者是按照16世纪的意大利或葡萄牙的拼写习惯来拼写的,故显得较为粗糙和不太完善。杨福绵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如没有送气音符号,这样声母中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没有区别,一律成了不送气音,例如“怕”和“罢”都拼成“pa”,“他”和“大”都拼成“ta”。而以后的利玛窦方案中在辅音后上端都标出“‘”,以表示送气音,如:“怕”拼成p‘a[p‘a],“他”拼成t‘a[t‘a],以区别于“罢”pa[pa]、“大”ta[ta]等。又如,同一韵母拼法不同,如“悲”拼成pi、py,“起”拼成chi、chij、chiy,这是当时意大利语中的i、j、y三个字母可以通用造成的[22]。
所以杨福绵先生认为这套拼音系统“属于初创,在声母和韵母的拼写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棱混淆的地方”[23]。
第三,《葡汉辞典》证明了明代官话的方言基础是南京话。
杨福绵通过对《葡汉辞典》中音韵、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的深入分析,认为《葡汉辞典》中许多特点是北京话中所没有的:“音韵方面,如‘班、搬’和‘关、官’的韵母不同……词汇方面,如四脚蛇、水鸡、桃子、枣子、斧头……如今、不曾等;语法方面如背得、讲得等,都和现代的北京话不同,而和现代的江淮方言相同。这证明它属于南方(江淮)官话,而不属于北方官话。”[24]
这个结论可以被两个历史事实所证明。一是南京曾为明都,迁都北京时曾带了大批南京人及江淮一带的人士北上,这样南京话在明代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二是利玛窦在他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的第4卷第11章中记录了他在临清与马堂等太监的交往,讲了一位太监赠送给他们书童一事,说:“刘婆惜非常高兴,在分手之前,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了神父,为教庞迪我神父学中文。这书童讲一口很好的官话。”后金尼阁在他的拉丁文版中改为:“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25]金尼阁把“官话”改为“南京话”,说明南京话是当时中国的官话[26]。
杨福绵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继罗常培先生1930年的文章以后,60年间关于来华耶稣会士在语言学贡献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对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给予了如实的评价。他说:“《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编写这部辞典时,罗明坚因为到中国时间不久,初学汉语,记音时,有些汉字拼写法尚不一致,甚至有模棱含混的地方。不过从拼音资料整体来说,已可使我们归纳出一个大致的官话音韵系统。”[2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