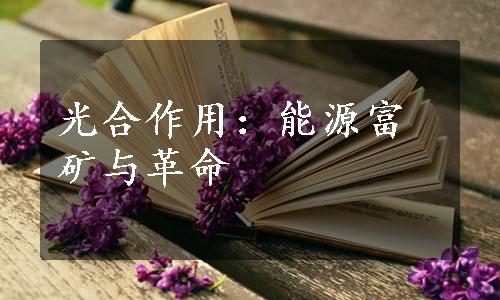
大约35亿年前,一场新的进化创新,即光合作用的发现,使某些生物开始尝试利用来自太阳的能流。这是生命体的首个能源富矿,其影响之大,恰似原核生物发现了争相追逐的宝贝。
来自太阳的光子要比来自疲弱的宇宙背景辐射光子能量高数千倍。能够利用这种巨大的能流可谓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事件。从此,尽管生物还在持续回收利用使用过的物质(因此之故,科学家们才会对碳、氮、磷的流动感兴趣),生物体可以利用的能量似乎无穷无尽了。13活细胞现在有了足够的能量实现自身及周围环境的重组,而且是在全新的规模上。生物体也因此广为扩散,生命的数量也因此增加几个量级。
那么生物是如何利用阳光的呢?实际上,有好几种光合作用反应都可以把阳光转化成生物能,虽然其效率和释放出的副产品也颇有不同。所有形式的光合作用都利用来自太阳的高能光子来激发光敏分子(如叶绿素)中的电子。电子因遭震撼而逃离原子,遂被蛋白质绑架,虽一再挣扎也无法逃脱。蛋白质传输高能电子穿过细胞膜,就像救火队员排成长龙传递水桶一般。这样在细胞膜处就产生了一种电梯度,后者便可以用来为传输能量的分子充电,比如三磷酸腺苷。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化学渗透的运作过程,只不过这次为三磷酸腺苷充电的不是来自食物分子的能量,而是一架来自空中的巨型发电机——太阳。
但这还只是所有光合作用过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被捕获的能量被应用于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不同化学反应使用能量的效率差别很大,要么是在细胞内做功,要么是合成碳水化合物之类的分子,后者的目的是储存能量,以备未来之需。最初形式的光合作用的副产品并非是产生氧气,而且越是在缺失游离氧的环境下,其运作就越理想。此时的光合作用可能使用了来自太阳光的能量,目的是从硫化氢(腐臭鸡蛋气)或溶解在早期海洋中的铁原子那里盗取电子。
不过,哪怕是早期最简单形式的光合作用也代表了一种能源供给的革命性变革,而且正因此,早期海洋中生物的数量可能已增至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左右。14此时,通过光合作用谋生的原核生物也必须靠近海洋的表面或干脆迁移至海岸处。许多原核生物因此形成了类似珊瑚状的构造,所以被称作叠层石(stromatolites),且伴随数以亿计的生物在祖先的尸骨上层层累积,最后竟在大陆边缘生长出了珊瑚礁。叠层石迄今依然只在少数特殊的环境中生存,比如西澳大利亚海岸外的鲨鱼湾(Shark Bay)。叠层石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从它35亿年前最初问世至大约5亿年前——足可谓我们这颗行星上生命史的大部——叠层石可能是所有地球生物中最显眼的一种。如果有外星人来我们这颗行星寻找生命的迹象,肯定会首先看到叠层石。但也许我们人类要到其他星系中山石嶙峋的行星上寻找生命,可能也会首先看到类似叠层石的生物存在。
终于有一天,新式的光合作用在一群被称作蓝藻(cyanobacteria)的生物中间进化成功。这种形式的光合作用使用水和二氧化碳为原料能够提取更多的能量。从水分子中撬取电子肯定比从硫化氢或铁元素中提取更难。可一旦掌握了诀窍,就可以提取更多能量,而且水中蕴藏的能量要大得多。擅长新式光合作用的生物利用从阳光获得的能量,决意攻击水分子,以使电子与其中的氢原子分离。下一步是把捕获的电子添加到二氧化碳分子,以形成碳水化合物分子,后者的作用是巨型能量储备仓库。而在这一过程中,氧元素被作为废料从水分子中释放。光合作用生成氧气的一般原理如下:H2O+CO2+从阳光得来的能量→CH2O(作为能量储备仓库的碳水化合物)+O2(释放到大气中的氧分子)。制氧的光合作用要比此前的光合作用效率高得多,但却只能从阳光中提取约5%的能量,这要比现代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低多了。光合作用为熵上缴了大量的垃圾税,因为这一过程在细胞内部造成的浪费以及被氧带走的物质都相当可观。
制氧的光合作用,也就是现代蓝藻所使用的那种光合作用机制,可能早在30亿年前就已进化而成。此说的证据在于,甚至在25亿年前太古宙结束之前,大气中已显见氧含量的增加。不过起初,光合作用释放出的氧气都被铁、硫化氢或游离氢原子迅速吸收,因为氧是电子的窃贼,所以会特别急切地与任何有备用电子的元素结合。因此之故,凡有电子从原子处失窃,我们常说是被氧化了。[原子尚有备用电子被称为还原(reduction),而涉及这两种过程的多种化学反应被称作氧化还原反应。]我们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蓝藻最初成功进化之日,正是30亿年前富含黄铁矿的沉积岩(愚人金)的消失之时,因为后者就像铁元素一样,遇到游离氧就会生锈。但这一机制吸收氧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自大约24亿年前开始,大气中的氧含量急剧上升,从当初不足今日氧含量的0.001%增至1%,甚至比这还要多。(www.zuozong.com)
25亿年前开始出现富氧的大气层(GOE,即所谓“大氧化事件”)极大程度地改造了生物圈。氧水平提高改变了生物圈的化学过程,甚至包括地壳上层的状况。游离氧有超强的化学能,由它驱动的化学反应创造出了地球上现存为数众多的矿物质。15而在大气层的顶端,氧分子更是结合成有三个氧原子的臭氧(O3)层,后者开始屏蔽地球表面,使其不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侵害且持续至今。由于有臭氧层的保护,有些藻类可能已开始第一次在陆地上定居,而在此之前,太阳辐射下的地球大陆基本上没有什么菌类生存,因为太阳辐射会撕裂任何敢于冒险登陆的细菌。
氧气的累积对活的生物体来说可谓是一次严重冲击,因为对大多数生物体而言,氧气是有毒的。所以,氧气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生物学家琳恩·马古利斯所谓的“氧气大屠杀”(oxygen holocaust)。大量的原核生物因此消失了,即使没有马上死亡的也躲进了大洋或岩石深处、氧成分不高的、能受到保护的环境。
氧气水平的提高还干扰到地球的恒温器系统,因为当时的恒温机制还无力吸收过量的氧,所以氧积聚近乎失控。游离氧分解了大气中最强大的温室气体之一——甲烷,而从事光合作用的蓝藻消耗了另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随着元古宙早期氧水平的上升和温室气体水平的下降,整个地球经历了第一次的冰雪覆盖期(此后还有过几次)。冰川从两极延伸到赤道,把整个地球都变成白色,而白色的地球更容易反射阳光,从而在一种可怕的正反馈回路中加剧了寒冷。最终,地球上大部分的海洋和陆地都被冰覆盖。马坎宁冰期(Makganyene glaciation)前后大约持续了一亿年,从约23.5亿年前至22.2亿年前。
这是一次近似剃光头(close shave)的重大事件。凡受氧毒害的生物要么消失,要么躲到了海洋深处。即使勉强能够应对高氧的生物在此后漫天冰雪的世界中也是受尽了苦难。冰川覆盖了陆地和海洋,也阻挡了生物光合作用所需的阳光。生命体真可谓命悬一线,因为大多数生命形式要么蜷缩在冰层下,要么挤在温暖的海底火山周围。
但地球并未因此而步火星的后尘,以至于过于寒冷而不再适合生命存在。这要归功于板块构造驱动下的地质恒温器,因为此时的恒温器经历了新的生物技术创新和补充,已经能够利用光合生物的活动。冰川阻断了光合作用,从而减少了氧气的产生。同时,在冰川之下,海洋火山也不断地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抽回到海洋中。温室气体开始在冰层下累积,直至最终冲破冰川,使地球表面再次变暖。氧气含量骤然下降至大气的约1%或2%,而随后是长达10亿年的漫长时期,氧气含量保持在低水平,气候也持续温暖。地球的古代恒温器似乎已被重新设置,以应对蓝藻在大气中制造的大量氧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