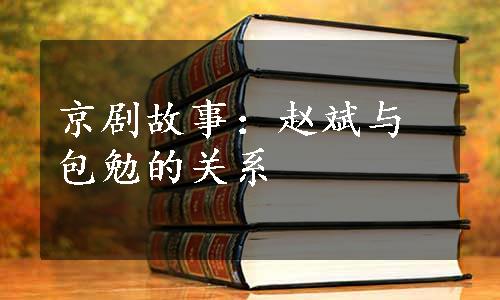
这出《赤桑镇》经常演出,我很熟悉。不过,戏里只说包拯铡了贪赃枉法的侄子包勉,怎样贪赃枉法却没说。这可是个关键情节啊,我知道另有一出《铡包勉》,就找了剧本来看,剧情挺有意思。那么,我就把这两出戏连起来讲吧,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丑角扮的包勉先上场,他介绍自己:“下官包勉,曾为越州萧山知县。未到一年贪了十万两银子,被人参奏,因此弃官逃走。回到家中,我母亲言道,我三叔去往陈州放粮,今日启程。我这就前往长亭,一来饯行,二来跟三叔讨个官儿来做。”
长亭是送别远行人的地方。今天去长亭的不仅有包勉,还有一些官员,其中一个叫赵斌。赵斌是皇亲,他与包拯的关系并不好。
“可恨包拯与我等作对。圣上命他去往陈州放粮,命我与他饯行。”是皇帝硬叫他去送包拯的。“本当不去,怎奈圣命难违,只好暂时忍耐。有朝一日抓住他的把柄,定要拔去这眼中之钉。”
包拯是正直的好人,这个赵斌把包拯看作眼中钉,那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了。
赵斌到了长亭,看见丞相王延龄也来了。
接着包拯要出场了,担任护卫在前面开路的四位大汉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恩师,赵大人——”包拯正招呼王延龄、赵斌,见大太监陈琳也赶来长亭。
陈琳吩咐:“酒宴摆下。”这是以皇帝的名义安排的送行酒宴。
众人刚刚举起酒杯,包勉到了。
王朝便替包勉通报:“来人说家住合肥小包村,姓包名勉,要见包大人。”
一听这话,包拯急忙出亭。包勉行礼:“拜见三叔。”
包拯问:“包勉,你从哪里而来?”
包勉说:“我从家中而来。”
“我嫂娘可好?”
“她让我问候您呢。”
为何称“嫂娘”,其中有故。因为包拯出生时又黑又五,被父母抛弃,是包拯的嫂嫂吴妙贞抱回了他,把他和自己的儿子包勉一起抚养长大,所以嫂嫂对包拯有大恩,既是嫂又是娘。
包拯又问包勉:“你做什么来了?”
包勉回答:“奉了母亲之命,与三叔饯行来了。”
包拯便领包勉进亭,嘱咐他:“见过列位大人。”
包勉看看众人:“哎呀呀,这长亭之上的众位大人,我对哪个行礼,对哪个不行礼呀?有了,我给他们行一个撒网礼。”
赵斌就不懂了:“娃子,你这是怎样的行礼呀?”
包勉说:“我这叫撒网礼。”
“何为‘撒网礼’?”
“我好比渔翁站在船头,这一网鱼、鳖、虾、蟹都在其内了。”
赵斌问:“可有你三叔在内?”意思是,如果有你三叔在内,他也成了鱼、鳖、虾、蟹了。
包勉回答:“无有我三叔在内。”
赵斌笑了:“顽皮的娃娃!”
陈琳和王延龄问包拯:“此位是——”
包拯介绍:“侄儿包勉。”
众人便说:“与大相公看座。”这是吩咐下人添设座位。
包拯说:“列位大人在此,哪有他的座位?”
众人说:“有话叙谈,哪有不坐之理?”
包拯嘱包勉:“还不谢过列位大人!”
“列位大人,我这厢——”包勉便要行礼。
赵斌赶紧阻止:“不要撒网了,坐下吧。”
王延龄对包拯说:“老朽有几句言语对你言讲。”
陈琳也有话要对包拯说,包拯便和二人转至屏风后叙谈。
场上只剩赵斌和包勉,赵斌不满地指着屏风后:“好话不背人,背人无好话。”
包勉赶紧讨好赵斌:“老大人,我与你满上一杯。”
赵斌说:“你也喝一杯吧。”
“卑职多谢老大人。”
“嗯?你口称‘卑职’,在哪里当过官么?”
包勉回答:“做过一任萧山知县。”
赵斌便跟包勉闲聊起来:“大相公,老朽在帘内为官,不晓得帘外的规矩,你可说给我听听。”
在京城朝廷里当官叫“帘内”,当地方官或不上朝的官叫“帘外”。我写过一出《打严嵩》,其中的邹应龙就由帘外御史升为帘内御史。
包勉遵命细细说来:“在京城领凭,去当地上任,拜了庙,拜了客,便可升堂理事了。”
赵斌问:“来打官司的,都是些什么案子?”
赵斌好奇道:“这赌博的案子你是怎样的判法?”
“这有何难,”包勉说,“在大堂上放两堆荆棘,叫那赌博之人去抓。”荆棘是一种带刺的植物。
“抓什么?”
“抓荆棘呀。”
赵斌惊愕:“岂不把手抓烂了?”
包勉说:“抓烂了,他们就不赌钱了。”
“这倒是个好法子。”赵斌说,“你包家辈辈都是清官。”
包勉叹口气:“这清官么,难做得很哪。”
“怎么难做得很呢?”
“这一任未满,我连裤子都赔掉了。”
“至于如此么?”赵斌笑问,“后来你便怎么样?”
“后来我就贪——”包勉自知失言,赶紧住口。
但赵斌追问:“贪什么?”
包勉道:“没有什么。”
“娃子,”赵斌安慰包勉,“我与你三叔一殿为臣,但讲何妨?”
包勉说:“后来我就……贪赃了。”
“怎样贪法呢?”
“若有打官司的前来,我就在大堂之上放两个竹筒,叫打官司的往里丢。”
“丢什么?”
“丢银子。”
“噢!”赵斌算是开了眼界,“那被告要是丢满了竹筒?”
“被告就赢了。”
“原告丢满了呢?”
“原告就赢了。”
“两家都丢满了呢?”
包勉毫不为难:“我就在花亭备上一桌酒席,让师爷给他们两家说合说合也就是了。”
赵斌问:“这银子叫他们拿回去?”
包勉狡黠地一笑:“这银子就是我的了。”
“这一任知县未满,你赚银多少?”
“一任未满我赚银十万。”
这可震了赵斌一下:“你三叔知道吗?”(www.zuozong.com)
包勉说:“我三叔不知。”
赵斌暗想:“不料他包氏门中也出了贪赃枉法之人。”
“啊,大人,”包勉忽然有点儿害怕,“方才之事不要对我三叔言讲。”
赵斌说:“娃子,我的嘴好比一把锁。”
“什么锁?”
“不要钥匙自开锁。”
包勉吃惊:“大人不要开玩笑哇。”
赵斌脸一冷:“哪个与你开玩笑!”
这时王延龄和陈琳一边嘱咐一边与包拯回到宴席。
赵斌便故意问包拯:“大相公在哪里为官?”
包拯说:“曾任越州萧山知县。”
“倒是个正印官儿。”
知县是一个县里最大的官,他偶然外出时,就会由典史来顶替他理事。
包拯便替侄儿谦虚一句:“他年轻不会当官。”
“嘿嘿,”赵斌冷笑了,“说什么年轻不会当官,一任未满他就赚银十万。”
包拯厉色问包勉:“可有此事?”
包勉慌了:“乃是句戏言。”
包拯吩咐:“撤座!”
“啊,三叔,列位大人赐我一个座位,为何撤去?”
“慢说一个座位,少时你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包勉眼看要坏事,赶紧把母亲抬出来:“若论国法,你大我小;若论家法,你吃过我母亲三年奶,你我要弟兄相称!”
包拯大怒,唱:“在长亭怒坏了龙图包拯,骂一声小包勉胆大的畜牲。初当官你竟敢不清不正,贪赃银受贿赂苦害黎民。叫人来与爷铜铡搭定,”两个穿红衣、头上插一根野鸡毛的刀斧手应声上场,“长亭上铡包勉决不容情!”
铁面执法的包公造了三口铡刀:皇亲国戚用龙头铡,官员用虎头铡,平民用狗头铡。包勉本来有资格用虎头铡的,可他现在弃官回家了,只能用狗头铡了。
“不不不不……不好了!”包勉唱,“一见此情心内惊,不该长亭来饯行。走向前来忙跪定,”他跪在赵斌面前,“大人与我讲人情。”
赵斌问:“包勉,你跪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呢?”
包勉哭丧着脸说:“方才我对大人讲了一句戏言,你对我三叔言讲,我三叔要铡我一死,望求大人给我讲个人情。”
“好吧,要看你运气如何。”赵斌心想,其实包拯也就是装个铁面无私的样子,他怎么会铡亲侄子,何况嫂嫂对他有如此大恩。
赵斌便对包拯说:“老夫乃是一句戏言,你怎么认起真来了,看在我面上饶了你侄子吧。”
“你住口!”包拯怒斥,“若不看在同朝面上,把你和包勉一同处置。”
赵斌不高兴了:“铡的是你包家之人,与我什么相干?岂有此理。”
“大人,”包勉忙问,“人情讲得怎么样了?”
赵斌说:“你再哀告王大人去吧。”
接下来,王延龄和陈琳先后求情,都没能说动包拯。
那赵斌还在一旁冷嘲热讽:“包大人,你若铡他一死,谁为你包家赚银子呢?”
包拯立刻命令刀斧手行刑,铡了包勉。
然后他叫王朝拿来纸笔,边写边唱:“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嫂娘吴妙贞。包勉犯下了欺君罪,我坐开封难徇情。长亭铡了小包勉,铡了包勉有包拯。书信下到合肥县,王朝,你与我多多拜上嫂娘亲。”
《铡包勉》到此结束,下面就是《赤桑镇》了。
王朝去合肥送信,吴氏夫人读信时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
包拯在放粮路上到了赤桑镇,住进馆驿(yì),他唱道:“恨包勉他初为官贪赃罔上,在长亭铜铡下一命身亡。命王朝下书信合肥县往,嫂娘亲闻凶信定要悲伤。闷悠悠坐馆驿心中惆怅……”
这时马汉来报:“启禀相爷,吴氏夫人来到赤桑。”
包拯一惊,接唱:“嫂娘亲因何故亲到赤桑?”
包拯急忙出迎,吴妙贞在王朝搀扶下已怒冲冲进了屋,激动地唱:“见包拯怒火满胸膛,骂声忘恩负义郎。我命那包勉长亭往,与你饯行表衷肠。谁知道你把那良心丧,害死我儿在异乡。有何脸面你活在世上,快与我儿把命偿!”
记得近三十年前,我的童话《哼哈二将》在台湾出版。台湾一家电视台想为我做个采访节目,摄制组在北京找了处外景,让我从上海飞去会合。主持人杨文敏是个小伙子,据说他在台湾有些名气。那次由一群戏校的孩子当群众,都十岁左右吧。开拍前,我们提议孩子们随便来两段,其中一个小老旦就唱了这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高亢疾速的西皮快板,一口气唱到“快与我儿”,此处有个停顿,杨文敏用食指代替鼓楗(jiàn),节奏准确地说出锣鼓点儿:“扎,扎!”小老旦惊讶地瞪圆眼睛:“哟,您还真会!”大家笑了。我接触的年轻人基本上对京剧所知其少,我以为海峡对岸也这样,这小伙子的“扎扎”两声震撼到了我,使我觉得传统京剧还是有可能吸引年轻、年幼的人们的。
包拯心情沉重地唱:“嫂娘年迈如霜降,远路奔波到赤桑。包勉他初任萧山县,贪赃枉法似虎狼。叔侄之情何曾忘,怎奈这王法条条——”
吴妙贞抢着唱道:“你昧了天良!国法今在你手掌,从轻发落又何妨?”
“弟也曾前思后又想,徇私舞弊犯王章。”
“手摸胸膛你想一想,我是包勉他的娘。”
“还望嫂娘多体谅,按律严惩法制伸张。”
“住口!”吴妙贞想起往事,太心痛了,“你休要花言巧语讲,恩将仇报负心肠。想当年嫂嫂将你来抱养,衣食照料似亲娘。你与那包勉俱一样,长大成人习文章。龙虎之年开科场,高榜得中伴君王。到如今做高官国法执掌,你不该铡死包勉丧尽天良。我越思越想气往上撞,你是人面兽心肠!”
包拯让嫂嫂坐下。月琴的伴奏声中,包拯深深行礼,缓缓告白:“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蒙兄嫂抚养成人。如今养育之恩未报,谁知包勉贪赃枉法,国法难容,私情难宥(yòu)。”
包拯唱道:“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金石言永不忘铭记心上。前辈的忠良臣人人敬仰,哪有个徇私情卖法贪赃。到如今我坐开封国法执掌,杀赃官除恶霸伸雪冤枉。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小包勉犯王法岂能轻放,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
吴妙贞一想:是啊,自己一直都是这样教导包拯和包勉的啊。“恨我儿他不该贪赃罔上,按律条铡包勉理所应当。怎奈我失却了终身靠养……罢!倒不如我碰死在赤桑!”
“使不得,使不得!”王朝和马汉赶紧拦住绝望的吴妙贞。
“呀——”包拯唱道,“见嫂娘只哭得泪如雨降,纵然是铁面人也要心伤。劝嫂娘息雷霆你从宽着想……”他让王朝取来一条到时候可扎在头上的白色孝巾。“劝嫂娘,休流泪,莫悲伤,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戴孝的儿郎。今日事望嫂娘将弟宽放,我还要去陈州赈济灾荒。”
包拯再三恳求:“嫂娘,宽恕小弟吧,宽恕小弟吧。”
吴妙贞身心震动:“小包拯他把那赔情的话讲,句句话感肺腑动人心肠。为黎民不徇私忠良榜样,万不该责怪他我悔恨非常。叫王朝你与我将酒斟上——”
王朝端来一杯酒,吴妙贞双手接过向包拯举起:“表一表为嫂我这一片心肠。此一番到陈州去把粮放,休把我吴妙贞挂在心上。饮罢这杯中酒起身前往,为百姓公废私理所应当。”
包拯接酒在手,高呼一声:“好嫂娘——”又是一段势如江河的快板,“嫂娘亲她把那真情话讲,肺腑言感天地荡气回肠。明是非主正义贤良高尚,劝包拯爱黎民永做忠良。深施礼谢嫂娘恩高义广,小弟我放粮回再孝敬嫂娘。”
包拯扶住白发苍苍的吴妙贞,凛然正气环绕着这对深明大义的叔嫂。
周锐趣说京剧
《赤桑镇》是花脸和老旦的对儿戏。我们以前对老旦的介绍较少,这次要说说老旦。
最早老旦角色并无专人扮演,大多由老生或丑行来兼任。我们介绍过《清风亭》,直到现在张元秀的老伴儿贺氏仍然常常由丑行担任,应该就是丑行扮老妇的遗留现象了。老旦这一行的专业化从郝兰田和谭志道开始。艺名叫“谭叫天”的谭志道我曾说过,他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父亲。郝兰田的徒弟是罗福山和龚云甫(fǔ),龚云甫的徒弟李多奎(kuí)则成了名噪全国的老旦。
李多奎八岁进科班时学的是老生,九岁开始登台演唱,十一岁时便能担任主要角色。那时他每场戏可挣八十吊铜钱,去戏园能坐骡轿车(骡子拉的带棚的车),这可是一般小伙伴没法享受的。可是好景不长,十四岁时他“倒仓”了。所有男孩都要经历变声期,嗓子往往会变得不再适合演唱,李多奎就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一是改行,不再吃开口饭;二是不懈地喊嗓锻炼,直到声音恢复。
李多奎就改学胡琴,以伴奏糊口。但他没有放弃练嗓,期待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在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李多奎总是每日天不亮就去天桥四面钟喊嗓子,风雨无阻。那时候天桥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四面钟又很空旷,周围很少人家,是艺人们喊嗓练功的好地方。
一天,李多奎在大哥的陪同下去四面钟,路上被一个值夜勤的警察拦下了。那时一到天黑就关城门,住在城里的得赶紧回城,住在城外的得赶紧出城,晚上不许人们在街上乱遛达。
那警察掏出怀表给李家哥俩看:“瞧瞧,几点啦?”
李多奎看表——才两点半。哥俩没话可说,因为这个时间任何人没有理由出现在大街上。而且警察又发现疑点,他看见李多奎背着个布口袋,摸一摸硬梆梆的,这可不像良民啊。
警察命令:“把口袋打开。”
李多奎打开口袋,露出一把胡琴,弄得警察啼笑皆非。
警察问:“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李多奎说:“您应该问,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不管为什么,”警察说,“再有下次,就把你们抓起来!”
从此,李多奎每天总是看了钟再出门。尽管这样,冬天不晚于五点,夏天不超过四点,终于十年练出一副铁嗓子。他有一次喊嗓时,一位前辈老师发现他的雌音,认为他极有老旦的天分,李多奎便用他的铁嗓子改学老旦,后来创立了领导老旦潮流的“李派”。
不过,李多奎成了大家以后仍然坚持吊嗓。他要求学生:“要想台上唱一出,私下就得吊两出,并且应当比台上高一个调门儿,这样在台上才能绰绰有余。”
他自己吊嗓子时用双手按着桌子,甚至把脚跟提起来使劲,唱完一段往往满头大汗。他还很重视养嗓子,如果当天有戏,这一天就不说话了,也不会客,就是来到后台也很少和人讲话,他管这叫作“养音”。
这使我想到杨小楼的“禁声养功一百天”。被誉为“国剧宗师”的杨小楼同样也经历过变声期的难关,那时他唱赵云那句“黑夜之间破敌阵”,唱得母亲心灰意冷。母亲不愿他给去世的父亲杨月楼丢人,让他辞了戏班坐吃父亲的遗产。杨小楼竟独辟蹊径地变喊嗓为养嗓。一百天内他在小黑屋里钻研技艺,像哑巴一样不说话。想吃饺子就向母亲做捏捏的手势,想吃面条就用两根手指一挑……
一百天后他大叫一声:“呔,马来呀!”跑去干爹谭鑫培面前,连唱带舞地表演那段“黑夜之间破敌阵”,使谭鑫培大为惊喜,如彩蝶破蛹。
不管怎样,各人有各人的成才之路,但都不平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