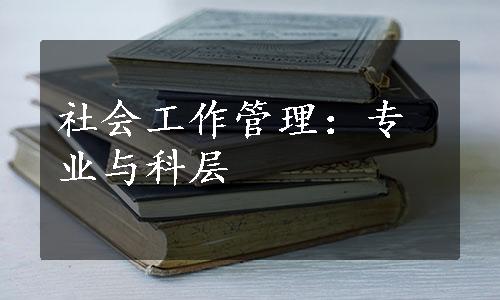
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一套与社会行为相关之任务取向的行为(task-oriented behaviours),包括高层次的专门技术,监督每项工作管理的自主性和裁量权,对任务的承诺和自由,认同同侪以及一套伦理和维持标准的方法。高层次的专业主义往往有其专业组织,以使得专业者能相互支持和提升其专业标准,并可借由确保其同侪的标准,以保障他们集体的声望(Southon和Braithwaite,2000)。Finlay(2000)将专业者所应具备的特征归纳为功利主义、信任性、技术、知识、才能、行为守则、组织、自主性、权力以及专业文化和成规。这些专业主义的体制,其目的乃在于排除非技术性者及不具资格者,以建立一套执业的独占权和规范其劳动市场(Abbott和Meerabeau,1998)。因而,专业者依据其专门的知识与技能,致力于专业服务和咨询的提供,并将其特定工作之绩效与个人问题加以联结,以合理化其所宣称的专业自主性和专业地位。
专业主义之异于科层化,最主要是在于其核心即是个别判断和裁量的概念,这种自主性的授予是基于有证照的训练、精通一套有系统和复杂的知识体系、持续的专业发展、依附的实务伦理守则以及同侪团体的责信(Miller,2004)。然而,福利国家建立之初,其服务输送的组织安排,一方面是立基于科层行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立基于专业者的专门技术。科层行政是以一种理性、规则限制和层级的观点,去联结人和资源之复杂体系,它提供福利专业者(例如医生、教师、社工师等)运用其专业判断的组织脉络;这种行政理性和专业技术的结合,确保了福利国家的中立(neutrality),并保护社会福利输送时专业判断的运作。虽然官僚(bureaucrats)和专业者(professionals)之间可能会反复出现紧张的现象,但这种组织体制为战后福利国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制度基础(Newman,1998)。这种“科层”与“专业者”的结合,也就形成了战后科层—专业主义(bureau-professionalism)的福利服务输送模式(请参阅本书第2章)。
1970和1980年代里,在科层—专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服务,社工被视为一种“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线上的社工通过对服务的决定权和行动,而对社会服务的诠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DuBois和Miley,2011),甚至他们会使用其裁量权作为防卫,以管理难以抗拒的工作负荷(Ellis、Davis及Rummery,1999)。社工实务的研究发现,专业裁量大部分被用来防卫而非倡导专业的理想,或弹性地回应人们个别的需求。街头官僚的行为直接地以其工作更具可预测性与可控制性之需求作为引导,因而,不同于赋予专业裁量之弹性和个别化的理想,街头官僚采用刻板印象将案主类别化,以简化其管理和回应的方式,这使得引导社工的并非是专业原则和方法,而是“以实务为基础的意识形态(”practice-based ideologies),这不仅让他们能够掌控其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因应在时间与资源皆有限的情况下所遭遇的困境(Ellis等,1999;Hughes和Wearing,2007)。专业主义所赋予的自主与裁量权,在实务的运作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妥协。(www.zuozong.com)
1970年代中期之前,科层—专业主义的福利服务模式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共识,然而,福利国家危机却伴随着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批评。在经济上,公共选择理论视公共部门在福利服务的供给上是浪费和无效率的;在社会上,旧式体制的父权主义和奶妈国家,造成一种破坏自立的依赖文化;在政治上,科层—专业的权力被视为为自身的利益,而阻碍并威胁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这种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提出全面性的批判,事实上也即是对过去政府在福利服务扮演积极性角色的重新思考,进而带动对传统科层—专业主义之福利服务输送模式的反省,一股强调削弱政府角色的“管理”理念,便在这股趋势下逐渐成长与茁壮。
在这股强调新管理理念的带动下,1990年代之前,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已出现于许多先进国家,它被冠以不同的名词,如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或企业型政府及新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科层理想,它在公共部门的发展是因为具有某些出现于私人部门的特性,包括对“结果”“绩效”及“成果”的关注,给予人员、资源和方案的管理较高的优先性,以相对于行政之于活动、程序和规范(Pollitt,1993)。此外,新管理主义的知识也被视为一种“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它适用于所有组织,而非仅是特定的组织,它呈现出一种超越服务或部门之间的理性行为(Clarke和Newman,1997;Flynn,1999)(科层—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的比较,请参考表2.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