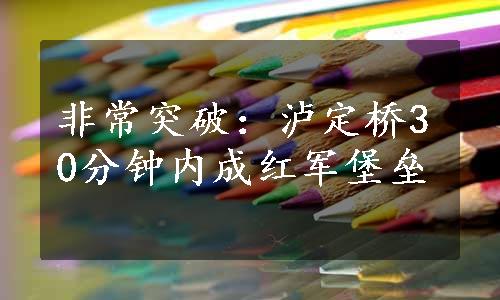
1935年5月29日16时左右,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
接下来的场面,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之人,都是从影视作品上见识的。
——冲锋号吹响,枪声大作……
——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前进……
——东桥楼敌军机枪向桥面疯狂地吐着火舌……
——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有人伤亡,但仍然一往无前……
……
这场面在各种表现这场传奇战事的影视作品中千篇一律,无一例外!这也是革命历史教育数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笔者是打小看着这种场面长大的,对这些攀铁索去夺桥的英雄,那就是一个如同对神人般地由衷景仰和膜拜!然而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军后有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及兵器常识后,却对这种“英雄画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当年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金陵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理论射速为五百至六百发/分,这样的家伙什正对着的射场不过是一段百把米的桥面,而这“百把米”桥面对操家伙开火的射手来说,无论在视界、射界还是射距方面都毫无障碍!也就是说,扭着铁索前进的红军突击队员们完全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守军枪口之下的。如此,泸定桥守军的机枪——无论是正对着桥面的这挺重机枪,还是在东桥头南侧李团重机枪主阵地上的重机枪编组,只要有机会能够获得持续十秒至二十秒以上的开口发言机会,那么攀铁索抢桥的这二十二位勇士就肯定不会再有一人还能留在这些光溜溜的铁索上,遑论爬过一百米距离来夺桥!
可为什么红军又夺桥成功了哩?
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如今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泸定桥的“猛料”: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这场战事乃至那二十二个英雄,纯系子虚。当年这个日子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守军,也没有拆桥板,红军是排着队太太平平过河的;红军是用现大洋买通守军顺利过桥的;红军过桥是因为刘文辉故意放水;红军有地下党的接应……
这样的“猛料”如今已有几十种版本。
然而这大堆的“猛料”却难以突破大量史证形成的强大证据链——即或把这当间来自胜利者的那部分记录予以删除:从蒋委员长本人直到川军河防诸将,乃至守桥部队的亲历者,都不讳言当年为这座桥的归属而发生过的战斗——甚至还有人作出了不吝夸张的渲染:“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29]
既然确认发生了战斗,战斗的结果又是改变了泸定桥的归属,那么逻辑导向就能够相对集中地指向一点: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而从双方自动火器配备至少100∶4到100∶6的对比来看,这样的剥夺完全是天经地义且顺理成章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曾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后来得到了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或伤亡或逃跑……”[30]
如此,笔者不妨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试着对夺桥战斗发起时的场景作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复原:随着红四团首长的一声令下,泸定桥西沿岸上百挺轻、重机枪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啸叫,守军几乎所有的自动火器发射点都被红军几挺乃至十几挺机枪定点锁定,射手们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而像李团机枪连、迫击炮连阵地这样的重要火力点,那是一定受到了红军追击炮手们“特殊关照”……
二十二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很多教科书乃至回忆录在陈述这场战事时,不曾道出或不愿道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红军强大火力有效压制了泸定守军,突击队员们开始……”似乎一道出这个前提,二十二勇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大打折扣似的。这种思维定式真正是让人啼笑皆非:红军强大火力对敌军的有效压制的确是给突击队员们上了一道保险,但这道保险却不是万能保险,“有效压制”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有枪子儿朝他们身上飞来!更何况,就算没有这种枪子儿飞来飞去的战场环境,又有多少人敢于尝试去攀着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过河?
泸定有群众目击了二十二勇士攀铁索夺桥的场面:“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的人)两个、三个(人)一起(堆),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31],“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抄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32]
在突击队后面“铺板子”的,就是三连连长王有才的“铺桥突击队”。
现住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下了河,就在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33]噢,再给他们整点门板来哈’……”[34]
李老太太对笔者等人口述的时间是2006年7月22日。那天笔者去她家拜访,刚敲门却发现老太太正拄着拐杖从泸定桥上气哼哼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念念叨叨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海内外关于泸定桥的那些“猛料”已传到了泸定,老太太是瞅着桥上桥下生意人也在传播这类“猛料”而动了气:“没打仗啷个过桥?莫非他们是来会亲家的么?……”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些年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从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从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她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整反了,整反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目击了红四团夺桥战斗的李国秀老太太(现居泸定河西街)
执拗的老太太无意之中道出了一个真谛:就创作劳动而言,艺术家享受的自由比史学家享受的自由要大得多!捡起一个具备传奇要素的素材作夸张、渲染、突出、引申等“艺术加工”,将“生活真实”提炼成为“艺术真实”,那是艺术家们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们的当然权利!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宣传口径”“新闻通稿”这一类官腔八股,那是阻塞不了人们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真欲的!
当然,如果有人要掂着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场景去质疑或臧否历史的本相,那也是和尚朝着道观磕头——没认准庙门儿!同样道理,艺术家在从事创作劳动时,还是得时时掂量拿捏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要过于轻狂、轻薄乃至轻率地去挑战“艺术真实一定要反映生活真实”这个底线!
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那日的泸定桥头来。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二十二勇士以勇悍无畏之气概一步一步攀着光溜溜的铁索靠拢东桥楼,手中的“花机关”吐出了一条条火红的信子……这气概这阵仗,想必与如暴风骤雨般的强悍掩护火力一起发生了作用,大大催生了东桥楼守军心中的震撼和挫伤:
“红脑壳的炮火好劲仗噢,弟兄伙怕是躲不脱噢……”
“红脑壳这是些啥子人噢?啷个楞格拿命不当命哩?……”(www.zuozong.com)
王靖宇老先生在其回忆文字中也转述过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红军机关枪密集猛烈,红军突击队步步逼近,“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民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红军突击队员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35]。
这种场面对守军上上下下的压力肯定是很沉重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他的长官袁镛通了一个电话[36]。
关于这个电话,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即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见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37]
这可能正是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直扑龙八埠第四旅旅部的那个当口。而袁、李在这次通话后即失去联系: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和十一团杨开诚部残兵从龙八埠撤向化林坪、飞越岭后,红一师也就随即进占了龙八埠,袁镛当然也就从此失去了对泸定桥战况的掌控。
李全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是在泸定死扛到底,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死扛到底?龙八埠距泸定城不过五十里开外,现如今旅部已受到“赤匪”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向泸定赶来,旅长自顾不暇,那肯定就顾不上他们了!几个小时后东岸“赤匪”主力可能就要扑到泸定,他们腹背受敌,泸定肯定是守不住的,又该如何是好?……
死扛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怎么走?昨日来路显然是不成的——“赤匪”们既然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朝这边奔来,往那边跑显然是送到人家面前受死!如此就只有一条道:从泸定城沿河上行到四湾、五里沟,再向东翻越马鞍山垭口退往天全……
李全山跟两个营长一合计,“大家认为既然龙八埠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笔者注:应为团直和李昭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38]。
东桥楼守军撤离时,泼上一桶煤油点着了一把火。
这个时候红四团突击队已接近了东桥楼,却突然被冲天而起的火焰拦住了。
突击队员们一时愣住了。
黄开湘、杨成武急红了眼,站起来就喊:
“同志们,莫怕火,这是最后关头,敌人已经垮了,赶快冲过去,就是胜利!”
爬在最前头的突击队长廖大珠突然起身,冲向正在燃烧的东桥楼。
突击队员们接二连三地站起来紧随其后,烂脚丫子套草鞋,踩着滚烫的铁索、燃烧的桥板,冲进了火势熊熊的东桥楼,手榴弹也接二连三地朝双枪兵扎堆的地方招呼。杨成武等带着二梯队也赶了上来,王有才头一回铺的门板铺得很稀,铁索桥被成百双套着烂脚丫子的草鞋踩得像筛筛子一样乱晃荡,而这当口冲过去的人们却谁也没感觉——仗打完了重走,人人都小心翼翼。
目击战斗的当地群众称:“他们(敌人)跑时,泼上煤油烧房子,红军冲过去一阵就打熄了”[39],“桥这面桥楼就烧了,红军冲过来后不一会就打熄了”[40]。而数年后在此间游历考察的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亦称:“二十四年因阻红军过境,守军纵火并焚毁泸定,后中央拨款饬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重建,一仍旧制”[41]。
实际上,泸定桥桥面上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城中的战斗进行了个把小时——红四团冲进泸定城时,“周桂三营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几人。”[42]
当日17时左右,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关于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情况,守军连长饶杰有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忆述。尽管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证据综合当地目击群众的回忆,再经过反复考据后认为:这段忆述水分太大,至少难以全部采信,但这毕竟是当年亲历泸定桥战事的守军人士留下的唯一一份口述文字记录,故而还是原文照录如下,以供各位方家继续探究辨析:
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只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43]
这里所言的“水堡”就在沙坝村河滩,而那里是根本找不着船的——船早就被拖过了河,而且那里的河段水势也一点儿也不缓(当时是正逢涨水)。即便是红四团佯动分队靠现扎的木筏渡河,也会顺流漂向下游很远的安乐坝,少数人登岸上行攻城的难度未必就比攀铁索抢桥更小。
天黑尽的时候,红四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泸定城。
见证——川军焚桥后保存下来的一根横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