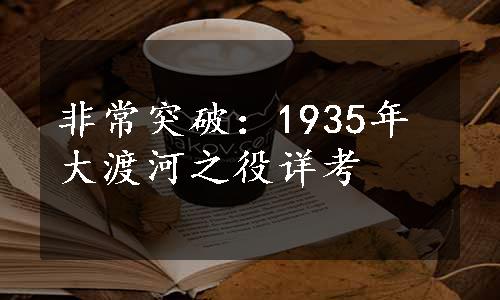
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对刘文辉而言,那效果是震撼性的!
此时正从雅安去汉源途中的大渡河上游守将刘文辉是何时得到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确切消息的?——注意,笔者说的是“确切消息”。从目前川军档案文献中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5月26日凌晨5时。刘文辉虽然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穷酸得紧,但电台还是可以通到旅一级单位乃至部分执行重要任务的团一级单位的。但在这个时间以前,他得到的是一个“不确切”的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而且这个信息很可能是来自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的报告——肖团位于安顺场上游八十里外的挖角坝,向刘文辉上报这个“不确切信息”的时间是在5月26日凌晨1时之前。
笔者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清溪镇的川军第四旅旅长袁镛相继发出的几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下达给第四旅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
顷本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绍成)团防线,仰派队取捷径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该团即派肖守哲营(即第三十八团第一营),即刻出发,经富庄取小道捷径向挖角坝前进,位于肖绍成团后方,并切取联络,相机行动。仍将前方情形随时报部为要。
此令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
旅长袁镛[57]
此令是1935年5月26日午前1时发自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教育局旅部。
肖绍成距安顺场距离很远,加上山路隔绝,与下游旅部的通讯联络实际上是不畅的。“赤匪”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消息,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就知晓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个“不确切信息”的?笔者不得而知,只好推测:是红一团强渡成功后,向挖角坝方向派出了侦察人员?还是肖绍成自己心有惴惴因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不管肖绍成这个“不确切信息”来源如何,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这个时候的刘文辉认为,肖团报告的这个“敌情”不算太大,故而只是“派兵一营”;二是此间与安顺场两岸渡口失守担待最大的第五旅旅长杨学端,迄至此时为止,并没有向刘文辉报告准确而可靠的信息,甚至连不准确的信息也没有。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此间在前线指挥的杨学端正焦头烂额,电台还不一定随时跟在身边。
到了凌晨3时,袁镛又向挖角坝方向增派援兵了,这个命令是发给所辖各团的:
顷奉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仰率部取捷径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积[碛]。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团曾(子佩)营进驻冷积[碛],三十八团肖(守哲)营经富庄向挖角坝先行搜索前进外,其余部队按照如下之时间顺序向挖角坝出发;
一、十一团二、三营于午前五时三十分;
二、手枪连、旅部于午前六时二十分;
三、三十八团二、三营于午前七时三十分;
四、各团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汉源城,由陈盈欧营派兵一连负责保管。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团长即便遵照为要。此令。[58]
援兵增至四个营,另派出一个营翻越飞越岭进驻冷碛!增兵的依据哩?仍然是那个“不确切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看来刘文辉对这个原以为并不算太重大的“敌情”还是心有惴惴,不太敢掉以轻心,于是又将第四旅袁镛部这支他手中唯一的机动兵力派出了三分之二。
然而当天下午6时40分,这个命令又被改变了,而且改变得很厉害,是方向改变:
一、顷奉军长电渝,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等因。
二、杨(开诚)团陈(盈欧)营随同副师长到飞越岭,李团肖营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该营即派官长侦探一名,设法前进至挖角坝,与肖(绍成)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晓,按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手枪连之顺序,向目的地出发,杨(开诚)团务于本日到达。仰转饬遵照。此令。[59]
这个命令是从飞越岭东坡下的泥头驿县(今汉源县宜东镇)发出的,可见这个时候袁镛已率第四旅旅部离开清溪进驻了宜东。同时也可以说明,26日凌晨的那两个命令在当日白天并没有执行(否则该旅主力当天至少已进至王岗坪,第三个部署也就无法执行)。究其缘由,只能是“当日白天”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从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处传来:过河的红军不是什么“便衣队”,而就是“赤匪”主力!杨旅担负的大渡河下游防线已全线崩溃!
还可以看出的是,刘文辉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操心泸定桥的问题。
究其缘由,很可能是刘文辉对于“赤匪”渡河后架桥不成而从最坏处着想所产生的“船只困难”,未必就能已清楚洞悉:26日当天中央红军过河部队已向杨旅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逐退至三梭窝、美罗场附近,这在刘、袁等川军将领的心目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数十公里河段的船只完全有可能已被“赤匪”控制,“赤匪”主力完全有可能从此间全部渡河。他们很可能溯河而上来抢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川康通道也是“茶马古道”,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控制沿岸船只。此间过河“赤匪”首先威胁的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侧数十里之遥的“桥”!
这从刘文辉“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埠,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的“电谕”内容可以得窥一斑:“对左翼择地作工”,那就是对大渡河东岸的下游筑工设防,防止已渡河的“赤匪”溯河而上来抢“川康要道”!而原本部署驰援挖角坝的“一营”人马,现在已变成了“官长侦探一名”,任务当然不是增援而成了“与肖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侦察从下游溯河而上的“赤匪”的“情形”。
刘自公现在最担心也是最操心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沿东岸溯河而上,夺取“川康要道”而趋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尔后再顺势夺取雅安!这就相当于要刨刘自公的老根,他就是明知挡不住,也得把头皮硬起来挡一挡!
次日一大早,川军第四旅主力从宜东出发,翻越飞越岭,开赴大渡河东岸。
很有意思的是,日前——也就是刘文辉确悉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并紧急向大渡河上游东岸派兵布防的那天,蒋介石又给薛岳下达了一个要求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各部“稳打稳扎”的手令:
薛总指挥:
我军由西昌前进时,各部应照剿匪行军要领,须梯次交番前进。例如,第一日第一纵队先由西昌到礼州,次日仍须暂驻原地筑碉,掩护其第二纵队第二日向泸沽前进。及至第二纵队到达泸沽时,则第三日令其暂驻泸沽筑碉,而掩护第一纵队或其他纵队向冕宁前进。及我冕宁部队到目的地之日,再令驻礼州部队或泸沽部队向冕山与越嶲前进。但其在礼州与泸沽已筑之碉堡,仍须派后续或指定守备部队防守,而前进行之时,切戒其对本身掩护、搜索、警戒之署,勿稍违剿匪手本之原则为要。中决本日飞成都。
中正。[60]
佩服蒋介石,这心操得实在是太仔细了!不光是每日行程,连进止时间都给卡得死死的。
目前笔者可以确认的是,蒋介石写下这个手令之时,并不知晓“赤匪”已成功渡河的消息——刘自公也是当天下午才确悉这个消息并作出了相关反应的。蒋介石当日在到成都后的23时,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已经延展到了西域荒漠乃至黄土高坡:“残匪窜向:甲、宁夏;乙、张掖;丙、陕北;丁、玉树”[61]。而在给薛岳的另一电文中,通报的则是刘自公在24日晚上上报的一个既“陈旧”又“乌龙”的“敌情”:
限即到
薛总指挥:
中刻抵成都,据刘自乾敬亥电(笔者注:5月24日23时)称:大树堡已发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河防部队擒得,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发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有[亥]侍参电[62]
看来左权、刘亚楼那天在大树堡的佯动,既哄了刘自公,也哄了蒋委员长——还连哄了几天。比如,蒋介石在5月27日那天的反省录中,仍然固执地将包围圈划在了一片遥远天际:“以后剿匪战略。如匪向西康突围。则取远势大包围之。注重陇西南之布防。若匪合股,则急定川北包围之法,北守南攻。东攻西守。以期聚歼”[63]。
薛岳将军生前撰有《剿匪纪实》,对这一段时间的部署留下了很详尽的文字:他也的确是没有辜负蒋委员长的这番操心,“中央大军”的日行程始终控制每日三十里至六十里之间。[64]当然,估计他的属下官兵肯定也很欢迎最高统帅再次强调的“稳打稳扎”的那个手令:走一天歇一天,怎么着也比被催着命踢着屁股往前闯要好得多啊!再说这越往大渡河边儿走,这地形越是复杂艰险,要一个不留神儿被“赤匪”冷不丁杀个回马枪打个伏击,那不是上赶着自找倒霉么?
还真是这样,蒋委员长给薛长官发出这个手令的第二天,被薛岳部中央军“礼让”到了“中央大军”前头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就在泸沽被“赤匪”们打了一个伏击。因“川康边防军”在红军从金沙江畔北进时守住了会理、西昌两座城池,得到了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奖赏,心气儿也高了起来,跟追“赤匪”的劲头竟然超过了“中央大军”。
27日那天,已尾追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至松林的刘元琮部兵分三路合击泸沽,还传令甘相营邓秀廷率部前来助战。泸沽系西汉古镇,坐落于安宁河与其支流孙水河交汇处,有桥连接孙水河两岸的南北街,镇东有要隘孙水关,西有梳妆台,南有接官坪,北有老君台,军事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刘元琮的部署是:刘本人率机关枪、迫击炮两连及旅直属队从接官坪大路北进,作正面攻击;白永安团从安宁河西岸经梳妆台攻击红九军团左翼并切断通往冕宁的道路;旅部手枪连则占领孙水关及五里牌隘口,从东侧切断泸沽通往越嶲的道路。
这位刘元琮是刘文辉族侄,与刘元瑭一样,也是个狠角色,人称“三莽子”。
不过他这回遇上了一位更狠的。
红九军团一个营在南街顽强阻击刘旅,在掩护机关、后勤部门和辎重物资转移后,撤至孙水河北岸隐蔽布阵,正面攻击的刘旅直属队一部跨桥尾追,被红九军团迫击炮火击退。从泸沽东侧进攻的刘旅手枪连在镇东郊涉河攻击时,又遭预伏红军集火射击,手枪连阵形大乱,尸体顺河漂下,余者狂奔入南岸民房躲避,红军则从容撤至北街。刘旅直属队一个连再度跨桥攻击进入北街时,又遭预伏红军火力杀伤,伤亡十余人。刘元琮恼羞成怒,集中迫击炮火向北街猛烈射击,红军为避免民众伤亡及民房损毁,从北街撤向镇外。
率部从泸沽西郊迂回红九军团的白永安看见红军北撤,认定这是在“逃窜”,遂令所部从梳妆台经踏水桥放胆追击。红军且战且退,经东岳庙退向李家堡,白永安越加气盛,继续放胆跟追。白团先头营进至李家堡时,预伏在此的红九军团主力在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下突然杀出,迫击炮、机关枪、排子枪齐发之后,又是刺刀、马刀一拥而上。一片开阔地上无处藏身的白团先头营官兵顿时乱作一团,前头的纷纷跪地缴枪,后头的疯狂奔逃。督战的营长策马跃上踏水桥急欲奔逃时,又被桥板缝隙别住了马腿而堵塞了桥面,于是正纷纷涌上桥面奔逃的官兵纷纷落水。踏水桥下是安宁河散流河水形成的小峡谷,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岸陡水深,白团官兵落水者罕有活命。急切中,一士兵砍断马腿,桥面方得通畅。白永安又指挥机枪在此岸山头掩护,从红军枪下刀下幸存的先头营官兵始得平安过河……
不过半小时,刘旅白团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红九军团俘敌百余,白团官兵落水而亡亦有百余,阵亡中校参谋、连长、副连长各一员,士兵七八十名。红九军团缴枪百余、子弹万余,于当日主动撤离,从容北进。而刘元琮旅也于当日退回松林。这个时候,奉刘元琮之召的邓秀廷部才姗姗从甘相营来到泸沽。
战后,“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传令将白永安撤职,在率部再度进至泸沽镇时,又以“作战不力”为由,将白团两个排长枪决于泸沽桥上。[65]
就在刘元琮泸沽惨败的同一天,安顺场的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夹河而进,奔袭泸定桥。
【注释】
[1]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01~10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3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想哈子:四川方言,想一下。
[5]楞格:四川方言,这么。
[6]光腔腔:四川方言,空架子。
[7]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页。
[8]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1~142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www.zuozong.com)
[9]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24~25页、第4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0]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4~145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11]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5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03~10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2]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73~37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3]《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14]《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15]吴鲁仲:《赖执中在西昌》,《石棉文史资料》第1辑,第84~96页;孙汝坚:《赖执中的两件事》,《石棉文史资料》第2辑,第125~127页。
[16]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5~146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笔者曾到现场与曾任安顺乡乡长的罗向如同志一起调查核对过当年的地形和敌军工事配备。
[17]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页。
[18]笔者参照红军方面的回忆文字并到现场与曾任安顺乡乡长的罗向如同志一起作过调查核对。另据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在《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一文中称:5月25日,红四团、红六团分别接替了红一团在安顺场上游老街、下游下坝、小水的掩护阵地。参见邓飞:《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11页。
[19]肖华:《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5页。
[20]脱不倒爪爪:四川方言,摆脱不了关系。
[21]干人:指穷人。
[22]《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3]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6~147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24]拽:四川方言,厉害。
[25]萎:四川方言,懦弱。
[26]李一氓诗:“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险,又见红军过铁桥。”
[27]《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页。
[28]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7~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29]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30]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31]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页。
[32]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149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33]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34]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35]《战士报》第186期。
[36]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37]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9~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38]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5页。
[39]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40]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41]“牲部”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1935年6月3日《战士报》第186期),《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2]《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54页,国史馆2008年版。
[43]《林彪、聂荣臻关于安顺场渡河情况致红三、五军团电(1935年5月26日7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4]《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45]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28页,1986年。
[46]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7页。
[4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1~34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8]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9]当时川造步枪因钢材质量问题,不耐高膛压,因此不得不减少子弹的装药量,有的甚至“减半装药”。
[50]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2~3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1]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2]邓飞:《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12页。
[53]肖华:《向安顺场英雄的船工致敬》,《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页。
[54]李富春与宋大顺的谈话,张弗尘先生在《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一文中有过考证,参见《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7页。另外,参见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3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55]《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1935年5月2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5~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6]《朱德关于继续阻击追敌致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李井泉电(节录)(1935年5月26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7]《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1935年5月26日午前1时于汉源教育局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0~15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58]《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1935年5月26日午前三时汉源城教育局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59]《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1935年5月26日午后6时40分泥头驿县公署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15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60]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2~16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61]《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57页,国史馆2008年版。
[62]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5~1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63]《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58~159页,国史馆2008年版。
[64]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65]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2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