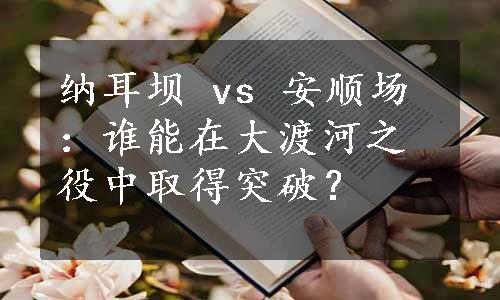
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中,左权、刘亚楼所率的第二先遣队,最先到达目的地。
5月23日,红五团从海棠出发,经平坝、深沟、河南站、晒经关,直奔大树堡。
过了晒经关,先头分队迎头撞上了几个团丁,抓起来一问,原来是大树团防局派来接越嶲县长彭灿的,而这位县太爷日前在海棠已被红五团抓获且应群众所请就地正了法,可见这稀里糊涂的团防局还未得闻昨天发生在海棠那一幕的消息……
从团丁口中,左、刘首长也得悉了大树堡的情况:负责富林正面防务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昨日已派一连过河进驻大树堡。这一连人有一个排搁在通越嶲方向的隘口渔塘,一个排则负责守卫大树堡的渡口,连部和连主力则驻在场镇里。场镇街上已经堆满了谷草、麦草、玉米秆,待红军一到就要纵火焚街……
左、刘首长和红五团干部合计一番,决定由被俘团丁带路,兵分三路合击大树堡。
战斗很快解决,大树堡守敌根本还没来得及纵火就成了俘虏,恶霸张金波的二百余民团团丁因为都是当地人,人熟地熟,逃走了一半也散去了一半,红五团夺取了大树堡。只有渡口那个排比较警醒,红五团战士们扑到渡口时他们已经驾船过河快到对岸了……
23日当晚,红五团顺利占领了“宁雅正道”的重要渡口——大树堡。
大树堡这个渡口正面,是隔河相望的富林镇(现汉源县城),这里刚好是大渡河下游几十公里方圆的一片平坝,水势平缓且水面宽阔。在不考虑战斗和时机的情况下,这段河面上架设浮桥或船渡,相较于两侧河道上的峡谷急流,要更为容易和安全。
当年石达开先锋部队,就是购尽大树堡所有布匹联结船只而成浮桥,顺利地过了河。
但这次不一样:对岸守军,恰恰是大渡河沿岸河防部队中装备最硬也最精锐的一支。
——这条道,“一线中通”,是蒋介石这些日子里屡屡提及的重点。
左权、刘亚楼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找船、修船,收集木材造筏——拆了关帝庙、王爷庙、陕西会馆、分县监狱,把木料运往渡口,动员船工修船和准备撑船,到处牵电话线,发动群众组织抗捐军,找船、修船和扎筏的船工们天天都有酒喝有肉吃,后边红三军团的队伍还在向这里开来……完全是一副马上要杀过河去的架势。甭说船工和百姓了,连红五团自己的好多官兵,都以为部队真的是要从这儿渡河了。[37]
这当然也不全是假动作:当晚21时,朱总司令的部署中就有“五团应相机占领富林,并控制渡河点”一项内容[38]——相机嘛,就是相准机会,或机会好了,就可以干一票。
这个阵势,肯定给对岸的守军川军王泽浚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这个在大树堡掀起的渡河声势,在“朱毛”的部署中,属于“虚晃”的一枪。
——这个声势整得轰轰隆隆的那当口,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团正悄悄奔向安顺场。
因为“彝海结盟”的耽搁,刘伯承、聂荣臻实际上比左权、刘亚楼在行程上要晚一天。5月23日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占领大树堡之时,他们还在从大桥向察罗前进的途中:日前他们刚把在路上袭击红军的黑彝家支头人给搞定,大家喝了血酒拍了胸脯。部队当晚折回大桥,次日才得已重新上路……
23日清晨,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离开大桥,一路疾行奔大渡河而去。
山路崎岖艰险,为了把“耽搁了的时间再抢回来”,队伍没有工夫停下休息和吃饭。行至黄昏,大风刮来了,大雨淋来了,从刘、聂首长和随先遣队行动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到红一团官兵,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看看天色已暗,前面还有高山悬崖,夜里行军十分危险,先遣队便在路边一个叫作簸箕湾的小村埋锅造饭,就地宿营。[39]
清早起来,部队又继续前进。穿过一片森林又跑了一段路,突然听见前边山上有人喊:“啥子人?到哪儿去?”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一瞅:嗯,是几个民团团丁。
他让杨得志把队伍停下来就地隐蔽,派一个连跟着便衣侦察员继续往前走。
山上的团丁还在吆喝:“哥子,你们到底是干啥子的嘛?”
团丁们被唬住了。这方“化外之地”的人们,既没见过红军也没见过中央军——见过的只是川军破落户刘文辉的“烟枪兵”。这一听说是“中央大军”,马上飞奔回镇传讯:中央大军来了,通知街上店铺把“青天白日”旗挂出来,准备茶饭,欢迎中央大军……
红一团大摇大摆进了镇。
迎面上来几个挎盒子炮的,其中一位蓄着八字胡的自称是区长:“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啷个事先不晓得哩?招待不周,长官莫要见怪。请稍候片刻,本区长有酒饭伺候各位哥子。二天得空了,欢迎各位再来耍。”
土地爷们从没见过红军,更没想到红军能如此迅速地通过彝民区,只当这些挎着“花机关”背着盒子炮的大兵真就是传说中的“中央大军”,于是点头哈腰,端茶倒水,伺候得很是殷勤周到。不一会儿工夫,宴也摆上了,酒也奉上了,一派热情洋溢,要招待“中央军弟兄”。
杨得志等将错就错,摆足长官架子,一屁股坐下来就大吃大喝。
一边吃,一边还“检查”防务,既严格又仔细。
区长很饶舌,一五一十细细道来,杨得志听得眉开眼笑,连声赞“好”!
饶舌区长细细说,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杨得志细细听,把该听的也听完了。
完了一抹嘴站起身来,“叭”的一声酒杯掷地。
“好了好了,你们该找地方歇哈哈儿了……”
每位土地爷的腰眼都被一支上了红槽的驳壳枪给顶上了。
“军……军爷,你们是……是……”
“朱毛红军。”
土地爷们浑身散了架,纷纷瘫倒。
红一团战士们在察罗找到了一个粮库,里头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袋装大米。一问管事才知道,这是“刘家军”的一个兵站:大米拢共有四千多袋,都是准备运往康定去补给“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的。杨得志听完看完了一摆头:“老规矩,我们背几包走,分些给老百姓,粮库封存起来,等后边部队来接管。”
老百姓高兴坏了——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儿么?
一时间,满街熙熙攘攘,欢语声声:
“噢哟,红军先生,把‘刘家’的米分给我们吃,硬是好噢!”
“好久没吃过白米饭了,托红军先生的福啊!”
……
先遣队狼吞虎咽吃完白米饭,日头已经偏西。
队伍继续上路——向六七十里外的安顺场方向,而不是纳耳坝方向。
刘伯承骑着一匹老白马,紧随红一团后边,口中不停念念叨叨:“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这里有一个很多回忆文字和史料都忽略了的细节。
本来按军委21日部署,第一先遣队准备夺取的渡口有两个:纳耳坝、安顺场。
纳耳坝是第一选择。
23日军委的部署电中,只提到了纳耳坝,没提安顺场。这也就是说,军委首长至少正在考虑:是否将纳耳坝从“第一”变作“唯一”?——军委部署电特别提到了“从岔(察)罗到纳耳坝是汉族居地”。这样的地域,一般不会再有前天先遣队在大桥遇到的那些麻烦。
察罗,刚好就处在去安顺场和去纳耳坝两条道上的分岔口——刘、聂首长需要作出选择。
刘、聂选择了安顺场——这个选择,与军委23日部署电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刘、聂首长又一次机断处置,便宜行事。(www.zuozong.com)
那么他们作出这个“机断处置”的理由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一般的回忆文字和史料提到的是,杨得志等在土地爷们的欢迎酒宴上得到了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刘、聂首长是根据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奔船而去的。
这个理由和依据当然是成立的。
但是,刘、聂首长的这个“机断行事”,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么?
这是刘伯承、聂荣臻受领奔大渡河畔抢占渡口的任务以来,第二次“机断行事”,也是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而且,这个“机断行事”也与上一次一样,被后来——不!被当晚就发生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富“英明预见”的正确措置。
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从大桥出发的同时,川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也从富林西移,开始在安顺场至富林河段布防了;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察罗的同时,杨学端率该旅部及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已经进驻了纳耳坝对岸的八排(今石棉县迎政乡),第七团余味儒部也进至上游的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所部韩槐堦营也进驻了安顺场对岸的安靖坝和桃子湾渡口;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安顺场的同时,纳耳坝场镇已被杨学端部过河拖船的部队焚之一炬!那天晚上的纳耳坝,就是一个火光冲天、哭声动地的场景。刘、聂首长倘按军委原部署奔那儿去,一来根本找不着船,二来也正好跟对岸设防的杨学端旅唐灼元团主力撞个对头,先遣队抢渡成功的概率,那几乎就是——没有!
刘伯承、聂荣臻是否在察罗逗留之时就得到了相关信息,不得而知;刘伯承、聂荣臻的“机断处置”是否出于他们驰骋疆场所历练积淀的军事敏感或直觉,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不可能在察罗就得到了纳耳纳场镇被焚的信息,则是肯定的——纳耳坝被焚是他们离开察罗奔安顺场去之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当晚的安顺场渡口,也面临着与纳耳坝场镇同样的命运。
当时大渡河沿岸守军奉有严令:
(一)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
(二)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
(三)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40]
那天晚上的安顺场,也面对着一个“几乎”……
【注释】
[1]国民政府1943年《宁属调查报告》,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页、第30页注释[53]。
[2]陈亲民:《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勾子:四川俚语,意即屁股。勾子后头,即背后、屁股后头之意。
[4]刘忠:《在大渡河下游》,《星火燎原》第3辑,第132~134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
[5]粮子:四川地区群众对旧时代“官兵”的俗称,意即“吃粮当兵的混小子”。
[6]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6~17页。
[7]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17~120页。
[8]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0~21页。
[9]《喜德县志》,第457~459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河道七场:今石棉县境内大渡河南岸在1951年6月建县前属越嶲县河道七场。“七场”具体为:安顺场、新场、察罗、泆马姑、纳耳坝、海耳洼(今新民)、田湾河。
[11]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页。
[12]倮倮:民国时期对彝族群众的蔑称。
[13]二天:四川方言,指以后。
[14]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6页。
[15]梁锋等:《长征中的神秘向导》,《中国民兵》2006年第2期。
[16]关火:四川俚语,意即“说了算”。
[17]王耀南:《“总部命令,不准开枪”》,《星火燎原》第3辑(未刊稿),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18]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页。
[19]沙马马海(木呷):《红军过彝区“彝海结盟”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4页。
[20]梁锋等:《长征中的神秘向导》,《中国民兵》2006年第2期。
[21]沙马马海(木呷):《红军过彝区“彝海结盟”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4页。
[22]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页。
[23]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页。
[24]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2页。
[25]《朱德关于我军先遣团通过彝民区情况及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1935年5月2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2~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6]《李聚奎回忆录》,第144~第1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7]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16页。
[28]《朱德关于继续阻击追敌致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李井泉电(节录)(1935年5月26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9]《王首道回忆录》,第1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30]黄应龙(1906~1935),曾用名王绍之,又名王德生,湖北省黄梅县古角山人,生于1906年1月24日,黄埔四期生,长征中曾任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首任政治指导员。
[31]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4~25页。
[32]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3~14页。
[33]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4页。
[34]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5~27页。
[35]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3~14页。
[36]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1页。
[37]刘忠:《在大渡河下游》,《星火燎原》第3辑,第138~139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张维光:《红军长征在大树》,《汉源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9~31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98~10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8]《朱德关于部署野战军二十五日行动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24日21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94~95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