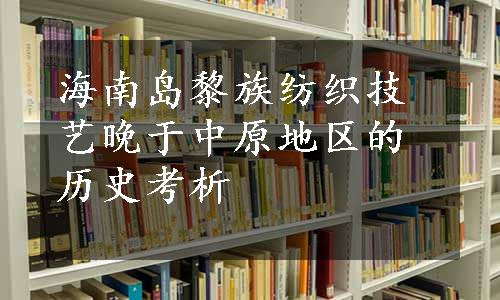
“纺织”是由“纺”和“织”两个部分组成。在生活中,“纺”的意思就是把丝、麻、毛、棉等纤维伸展旋曲,再经过合并及缠绕形成纱线的过程。在我国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一书中这样解释:“纺,网丝也。”也就是把丝质纤维编织起来的意思。在实际操作中,“纺”往往和纺织、纺绩[1]纺手[2]这样的内容或者方法联系起来使用。纺的繁体字为“紡”,其中的“糹”偏旁和“糸”是相同的意思,“糸”的本意就是指“细纱”和“丝线”。织的繁体字为“織”,基本意思是用丝麻、棉纱、毛纺纤维等编织成布料或者衣被的统一称谓。织的繁体字由“糸”和“戠”共同组成。“戠”的原意是军事上的操练和操演,是对排兵布阵的解析。纺和织连在一起使用,就是对适合纺织的各种纤维合成纱线并进行编织的过程。
我国最早的纺织记述来自“嫘祖养蚕”的传说。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唐代军事家赵蕤在《嫘祖圣地》的碑文中说道:“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没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这段话中,嫘祖最先开始“种桑养蚕、抽丝编绢”。嫘祖因此而成了养蚕缫丝的始祖和纺织的发明人,到了北周以后,嫘祖在民间已经成为祭祀神,被尊称为“先蚕娘娘”,也就是主管纺织活动的“蚕神”。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最先被发现有纺织遗迹的,是旧石器时期的山顶洞人。据测定,山顶洞人遗址距今有25万~60万年。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早期人类纺织使用的骨针,这也成为我国已知早期人类纺织技艺的最早起源。到了新石器时期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多处遗址中发现了石质、陶质纺轮,纺轮的出现,使纺纱技艺更加方便快捷。我国的西周以后,开始出现了原始纺机和纺车,各种有关纺织的记载也逐渐清晰完整了起来。
2016年12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发布了:“12月12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期刊Plos One发表长文,题为《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Biomolecular Evidence of Silk from 8,500 Years Ago)。该文报道了河南中部地区发现的贾湖史前遗址,并取得了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在贾湖两处墓葬人的遗骸旁,逝者腹部的土壤样品中,科考人员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根据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综合分析,表明贾湖居民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也就是说,根据当前的考古发现,我国的原始人类从事纺织工作的历史,距今已有8500年之久(图1)。
在现代的考古发现中,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纺织工具,在距今5300年之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也发现了丝绸织品的碎片,在距今5000多年的山西西阴村遗址里,发现了半个蚕茧……
对照以上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海南岛目前已知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来自三亚的落笔洞遗址(最新掌握的资料表明,考古工作者在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信冲洞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的3件石器,说明人类活动在海南的历程已有两万余年,见图2、图3)。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表明:落笔洞人的生活时限大致在旧石器时期末期,距今10000年左右。落笔洞人曾经被认为是黎族先民,但专家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落笔洞遗址并未出土与纺织有关的遗物,距离黎锦的出现还显得极为遥远(图4)。显而易见的史实表明,海南岛的人类活动时间以及纺织技艺的出现时间,都远远晚于中原地区。
海南黎族的创世神话,主要有“大力神”和“黎母传说”。据说,是大力神最早来到海南,他筑起了海岛、创造了人类(黎族先民),但其中并未涉及纺织的内容。黎母传说和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有关(说法之一)。黎母就用天上的七彩祥云纺出彩丝,就彩丝编织彩衣,并依据这种方式教会黎女纺织技艺,这应该是海南黎锦最具神话色彩的起源说法。
从有考据的历史来看,目前最为一致的说法是:“黎锦的出现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这一说法,海南岛黎族先民从事纺织生产的历史明显晚于中原地区。还有一个表述是:“黎锦是中国棉纺织历史上的‘活化石’”!这一说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图2 海南远古时期遗留化石
(来源: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编者摄)
图3 海南远古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
(来源: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编者摄)
图4 三亚落笔洞旧石器时期遗址出土文物
(来源:海南省博物馆)
能够佐证或者推断出海南岛黎族纺织技艺出现了3000多年的说法,依据的是成书于2500多年前的《尚书》[3],最早的《尚书》被认为是伏生撰写的。
就后世考据可以注意到:关于作者“伏生”的介绍歧义甚多,其真实性难于考证。其中比较靠谱的说法是: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过程中,这一上古流传下来的《尚书》大部已经毁损,个别可能保存的篇章,也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散失。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府(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内史官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里包括了《今文尚书》33篇,以及《古文尚书》25篇,这就是我们如今可以看到的、完整的《尚书》。但到2018年的11月,清华大学发布了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证明《尚书》是后人假托春秋时期古人名义撰写而成的,《尚书》其实是后世的“伪作”。
抛开对《尚书》辨别真伪的过程,《尚书》中言明纺织出现,在《尚书·禹贡》篇中有表述,文中提到了“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句话。但联系前后文加以辨别,这段话的本意是指“天下九州”划分后的“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文中的“扬州”是指的淮海之间,也就是北起淮河、南到大海之滨的广大区域,就现在通行的地理划分来看,这一区域包括了现在江苏、安徽两省之中的淮河以南地区,还有浙江省和江西省的部分区域。从中不难看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指称地并非专指海南岛,这和文中表述以及当时人们对视线以外地区无法关注到是有直接联系的。
“岛夷”是指沿海岛屿上居住和生活的人类。“卉服”的出处在孔颖达的《疏》中:“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各种草本的植物都可以被称作为“卉”,“卉服”就是用草本植物或纤维编织成的服装。颜师古在《注》中解释:“卉服,絺葛之属。”“絺”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为“细葛”,“葛”是多年生的藤蔓植物,其茎可以用来制作绳筐之类,破开的葛纤维能够制作粗布。明代的宋濂在《白牛生传》中做了进一步的辨析:“锦衣与卉服虽异,暖则一。”就是说“卉服”与“锦衣”是两个完全不同质地的御寒穿着之物。
就上述考证来看,海南岛黎族织锦技艺的流传之源并未有明确的时间!其中,“海南岛黎族地区流行的织锦技艺”也并未具备清晰可辨的史实和考据。但考虑到海南岛为外界可知的历史最早不超过秦汉时期的史实,加上海南岛黎族仅有语言传承而没有文字记载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尚书·禹贡》的“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理解为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下推论而出的史实。尽管这种推论并不严谨,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东南沿海乃至海岛“夷人”,在2500年前就已经有了纺织草科植物纤维用作御寒的历史。其中的“岛夷”是否为黎族先民?也缺乏史实及考据。
海南省位处我国最南端,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一个省。
海南省简称“琼”。海南省的陆地面积为3.5万平方千米,蓝色土地面积,也就是海域面积大约为200万平方千米。海南省陆地面积比我国其他各省(地区)中面积最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64万平方千米还要少3.14万平方千米。所以,海南省就常常被误认为是我国各省(地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省。其实,海南省的面积还要加上西沙、中沙和南沙的偌大海洋区域,陆地加海洋,海南省的总面积就超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66万平方千米约30余万平方千米,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
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海南岛在唐虞三代就被称为“南服荒缴”。这段证明海南自古为中原部族统领的文字记载,载于宁波天一阁藏本的:“沿革表—历代统隶”的第一栏,即:“唐虞三代,南服荒缴”。所谓的“荒”主要是指荒凉、少人居住的意思。“缴”是指边界,就是大国边境的意思。
“唐虞三代”,“唐”指唐尧。唐尧姓伊祁,名放勋,古唐国(今山西临汾尧都区)人,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虞”指虞舜,姓姚,名重华,字都君,山东诸城人,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三代”指中国建朝最早的三个朝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换言之,在明代木刻版的这本古书中,作者依据对前朝的考证,得出了在夏、商、周之前,海南就是中原部族的边界的结论。
海南在秦代的时候,《外纪》这本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南越郡外境,地接雷,当附象郡。《外纪》又以为南海郡外镜。”这段话是对秦代海南岛隶属关系的梳理,说明这个时候的记载并不统一。但黎族为海南岛最早的居住民一说,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并无明显和确凿的证明。
一般认为:“最早居住、最早开发海南岛的是黎族”。这个说法的依据在哪里呢?
海南省人民政府网上介绍黎族时说:“黎”是第三人称,主要是汉民族对海南岛黎族的称呼。在西汉以前曾经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了海南岛的黎族先民。
“黎”的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唐代刘恂所写的《岭表录异》里。在这本书中,开始出现了:“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海南儋州一带,救济当地的“黎民”。其中的“振”类同于今天的“赈”,是救济的意思。考据中“振”还有一个意思是“震”,表示“威震”。“夷”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原始先民。到了北宋以后,几乎所有介绍海南原始先民的文字都开始使用“黎”字,来代替了过去的“俚”“僚”等称谓,此后就成了海南岛黎族群众的统一称呼。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府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等差异有‘哈’(过去作‘侾’)、‘杞’(又称‘岐’)、‘润’(过去汉称‘本地’黎)、‘美孚’、‘赛’(过去称‘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黎族的起源认定比较混乱,一直缺乏严谨科学的说法。经过近数十年的专家学者研究,尤其是从文献记载,考古学、语言学、民族等方面的梳理后,已有较多学者认可黎族是从古代的“百越”族发展过来的,特别是和“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一带的除了汉族外广泛居住的少数民族地区,称呼为“百”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部落族群不但众多而且习俗、行为与语言都有差异。这种差异对于长居中原的汉族人来说极难分辨清楚,就以“百越”称呼他们。“越”也叫作“于越”,主要指现在的赣、浙、粤、闽、桂及越南北部一带居住的部落。越和广东省的简称“粤”为通假,所以“百越”也被叫作“百粤”。更为广泛的说法是“百越”是对我国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
“骆越”是百越当中特别强大的部族,大致的居住位置在今天的广西南部。骆越在典籍上最早的记载在《逸周书·王会》这本书中。其中的“路人大竹”,在朱右曾的《集训校释》中解释为:“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周朝的史实:周武王灭商后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建都,时间大致是公元前11世纪。周朝共延续了800多年,直到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终止。《逸周书》也叫《周书》,成书于先秦时期。书中所述最远时间为距今3000多年的周朝建国之时,所谓的骆越族或者是骆越国的记载,也大致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
骆越或骆越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过特别深远的影响。骆越的一部分后来逐步南迁,到战国末期,这些人就迁徙到了越南河内附近,在越南的北部成立了瓯雒国。“雒”和“骆”通假,是如今越南京族和黎族的前身。其中的“黎族”部分被认为和海南岛的黎族一脉相承,这也许是黎族产生于3000多年前、黎族的纺织技艺被认定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重要佐证。
黎族织锦技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具体是从哪里出现的呢?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海南黎族对本民族的记事、记物,我们只能从汉语言文字的记载中得到了解。这些记载又因为年深日久、缺乏系统性的缘由,无法得到清晰和完整的印证。所以,我们只能简略地得出这样一个概念:最早来到海南岛的居住民应是黎族(尚有存疑)。从有考据的历史来看,黎族出现的最早时间不会晚于3000年前。
黎锦是黎族先民的生活用品,其出现历史应与黎族出现历史基本一致。(www.zuozong.com)
从秦汉之后的历史记录来看,黎族在此前就生息繁衍在海南岛上,因为黎族织锦和黎族纹饰在当时和后世的大量流传,黎族织锦技艺就具有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承。黎族群众在与瘟疫酷热、毒虫猛兽的斗争中,不断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独特的集体生活方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黎锦纺、染、织、绣传统技艺。
海南现有黎族人口约130万,大多居住在海南岛的中南部河谷与丘陵地带。黎族延续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女子的地位略高于男子。黎族妇女中流行黎锦,黎锦技艺的全称是黎族原始纺、染、织、绣技艺。这些技艺在黎族的“五大方言区”中均有传承。
从上述的梳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代文献记载中,黎族出现的历史有3000多年,黎族的服饰文化和其纺织技艺紧密关联。黎族是一个有语言但没有文字记述的民族,关于黎锦的记录,大多出自黎族先民的口口相传和汉语言文字的典籍记录当中,是汉族对黎族的认识和表述。除了这些记载以外,还有什么证据可以佐证黎锦技艺的出现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考古发现和遗址出土这两个环节上!
根据《海南日报》记者陈蔚林、杜颖发表于2016年2月5日的《揭秘海南东南沿海新石器时期遗址群:史前墓葬被发现》来看: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入选了“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它让海南史前年代序列日渐清晰,所显现的南岛语族特征亦随文物的出土愈发明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傅宪国介绍,经过3年多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现了桥山、英墩、莲子湾等处全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该文中说:海南东南部“海地”的陵水英墩遗址、陆仔湾遗址、莲子湾遗址和桥山遗址、大港村遗址,均发现了新石器时期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其中出土了大量原始人类的骨殖和石质、陶质的器物,尤其是发现了数量不菲的陶质“纺轮”。
纺轮也叫纺专,“专”与“砖”字通假,是陶质纺织专用器物。“专”在殷墟甲骨文卜辞当中,写法为古人纺纱姿态。这个字的结构是把一束纤维集中起来绕在纺杆上,下面有一个陶制的瓦轮形状的“叀”,左边加一个“手”(寸)的形状,表示手捻“专”的纺纱动作。
在海南陵水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中,圆孔是插转杆用的,当人手用力使纺盘转动时,砖自身的重力使一堆乱麻似的纤维牵伸拉细,纺盘旋转时产生的力使拉细的纤维经捻搓而成麻花状。在纺盘不断旋转中,纤维牵伸和加捻的力也就不断沿着与纺盘垂直的方向(即转杆的方向)向上传递,纤维不断被牵伸加捻,当纺盘停止转动时,将加捻过的纱缠绕在转杆上即完成“纺纱”过程(图5)。“小小的陶轮虽然十分简单,但人们配合自己灵巧的双手,完成了至今为止现代纺纱工艺仍然沿用着的五大运动:喂给、牵伸、加捻、卷取、成形。现代纺纱机虽然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传动机制和电脑控制方式,但是不管是喷气、气流还是环锭纺纱,万变不离其宗,纺纱的原理还是相同的,基本的五大运动一个都不能少。”
海南东南沿海出土的陶纺轮,被考证为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类在4500年前的杰作。海南原始先民的纺织技艺和纺织生产活动也被上溯至距今4500年左右。根据实物优于记载的原则,海南岛的纺织技艺出现于4500年前更具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海南岛有陶纺轮等出土发现,佐证了海南纺织历史的上限可推至新石器时期,但能够佐证黎锦出现的原始棉织物至今还未曾在海南各地查找到相应的证物。同时,也无法确证海南岛黎族的织锦技艺可以和新石器时期的海南岛原始居住人群相重合。换句话说,海南岛在4500年前就有了原始人群使用陶纺轮进行纺织活动的物证,但这个物证是否为海南岛黎族先民所为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书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将海南岛最初的居住民与黎族先民加以重合,据此得出:
图5 清代《琼州海黎图》中的黎女采用手捻纺轮纺纱的技艺
海南岛黎族织锦纺、染、织、绣传统技艺的起源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4500年前。这也就是本书提出“黎锦的出现历史可以上溯到4500年以前”的由来!
在黎锦的发展历史上,有“中国纺织业革新家”之称的黄道婆,曾经在宋末元初来到海南岛。她在岛上与黎族妇女的交流中掌握了黎族原始的织造技艺。她在晚年返回中原以后,将原有的纺织技艺和海南地区的纺织技艺相结合,在棉纺织技艺的改革和推广上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终以“衣被天下”享誉华夏。但本书对黄道婆学到了黎锦技艺并带至中原发扬光大的说法并不认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依据现有资料,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镇(现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1245年出生。黄道婆出身贫苦,她12岁就被卖给一户人家当了童养媳。这户人家对她并不好,她需要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纺纱织布,往往到了深夜才能休息。也就是说,黄道婆在少女时期就已熟练地掌握了纺纱织布的技能。黄道婆不但要承受极强的劳动重压,还要忍受公婆和丈夫的毒打,但她也在这种严酷的生活环境下经受了历练。在又一次被毒打后,她决定逃出这个让人绝望的家庭而去另寻生路。她在半夜的时候从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江边的海船上并随船出海。这艘船在海南崖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省三亚市的崖州区附近遭遇风浪,黄道婆被附近打渔的黎族人救起并在这里住了下来。当地的黎族同胞知道她的境遇以后,都十分同情并收留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在共同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黄道婆从当地的黎族群众中学习到了“崖州被”的织造技艺。
崖州被也被叫作“龙被”(有争议),龙被是流行于崖州黎族群众当中的织品,是黎族织绣技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较高、技术要求全面和高超的手工织品,据称曾经作为“贡品”使用(有争议)。黎锦的传统工艺主要是纺、染、织、绣四大技艺,主要运用在织造环节。崖州被一般长2~3米、宽1~1.5米,这是黎族妇女采用原始的腰机所无法做到的幅度(图6)。
崖州被的图案主要有龙凤纹、麒麟纹和各种吉祥图案,因为宋末元初(黄道婆在崖州的时间)的黎族地区已有“生黎”和“熟黎”的区分。崖州被主要产生于熟黎地区,而黎族的“生”与“熟”又主要以汉化程度区分,所以,黄道婆所掌握的黎族织锦与织造技艺亦应具有汉化的成分。踞腰织机织造的布匹和图案比较单一,通常呈现出几何化图案的特点。而使用脚踏织机织出的崖州被(龙被)质地好,布幅宽大。崖州被是先织制好布料,然后才在布料上刺绣花纹图案,崖州被的最大特点在于“刺绣”。随着脚踏织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绝迹,现在仍在延续的黎族织锦已基本上难觅崖州被的踪迹。黄道婆学习的黎锦,其实和她在老家已经熟练掌握的纺织技艺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其二:黄道婆来到海南崖州时,当时的黎族妇女生产的被单(黎单)和用于装饰的各种棉织物(黎饰)已经十分出名,黄道婆在虚心向当地妇女学习黎锦技艺外,还能把黎汉两族的纺织技术加以融合与变通,也就逐渐成了一位深受当地黎族妇女喜爱的织锦能手。黄道婆在来到海南岛30年以后重回故里,到她去世时的1296年,她在返回故里之后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六七年的样子,她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成绩而被后世敬仰的呢?
图6 清代《琼州海黎图》中的黎女采用腰机织锦的过程展示
据记载,黄道婆在元代的元贞年间重返故乡,她发现故乡妇女还在使用落后的纺织技艺,她就把在学习崖州被和黎锦技艺中得到的经验加以改良,在自己的老家乌泥泾镇上收了徒弟,把主要学自黎族地区的棉纺织技艺用来改造当地的丝麻纺织技艺,逐步传授和推广了轧棉的赶车(去籽搅车/机)、弹弓(弹松棉花的椎弓)、纺车(一锭变三锭的脚踏纺纱车)和织机等,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是指先把棉纱染成需要的颜色,然后再使用提花的技术织出各种图案,而这种染纱后再织出花纹的技艺被普遍认为是从黎族地区学习到的。
因为这种改良技艺的领先性,黄道婆所传授的棉织技艺被迅速传播到大江南北,松江府当地成了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黄道婆也以“衣被天下”的美称广誉后世。
就这个历史评价来看,黄道婆返回故里的时候,当地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技艺都已成型,只是相应的纺织技艺比较落后。黄道婆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对棉纺技艺的改良和改革上,有效地提高了纺织水平和织造效率。黄道婆在纺车的改革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当时流行的都是旧式的单锭手摇纺车,织造效率非常低下,严重制约了织布业的发展。黄道婆就在纺麻的脚踏纺车基础上改造成了纺棉的纺车,极其有效地提高了纺纱效率。同时,黄道婆还把从海南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提花技艺总结为当时十分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艺向大家传授,才有了当地棉布与花布质量的提升与产量的提高。资料表明:“乌泥泾被”在16世纪初已有一天上万匹的产量,到了18世纪还大量出口欧美,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名,这个伟大的贡献是和黄道婆直接相关的。
重温这段历史,重点在于厘清这样一个史实:
目前在学界和民间都有一种提法,是说黄道婆在海南学习到了黎锦技艺,她把这个技艺带回了家乡并进行了传授,从而取得了极大的声誉。
这种说法显然是有违史实的!
首先是黄道婆本身就具有高超的纺织技艺,她在做童养媳的时候就以纺线、织布作为工作重心之一。如果说这种纺织技艺和海南地区的纺织技艺进行比较的话,这时的纺织技艺更加侧重于丝麻织品的纺织劳动。
其次,黄道婆来到海南岛后,她在海南当时织造最为发达的崖州地区,和当地的黎族妇女学习的黎锦技艺更加侧重于脚踏织机的应用,这和史料记录的“崖州被”的织造技艺是一致的。目前在海南黎锦的织造技艺中,脚踏织机早已失传,而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黎锦纺、染、织、绣传统技艺主要是指踞腰织机,也就是腰机。而腰机织造与黄道婆返回故里后传授及改良的纺织技艺并无直接关联,黄道婆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一锭变三锭”的纺纱效率提高,以及把染纱与提花工艺带入织布当中,由此带来棉纺织技艺和产品数量、质量的大幅提升。
还有,黄道婆的贡献主要是改革棉纺织技艺并由此带动当地棉纺织产业的发展。这个功绩的核心在于勤奋、思考、改革、推广以及广阔的内地市场容量上。如果看不到这些,而只是片面宣传黄道婆把黎锦带回中原借此成名的话,不但贬低了黄道婆的贡献,也把黎锦的这段历史定位引入歧路。
海南岛从秦汉时期就为中央政府管领,各地官府都有疆域图绘制的任务,海南也概莫能外。我们近年收集到多幅珍宝级的清代海南岛图卷,其中就包括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琼郡舆地全图》,本书作者费尽心力得到了一件等大的、高精度的复制品,亦将在相关章节呈现给读者朋友们(图7)。
还有一个人及一本书值得我们纪念,这个人就是被誉为“黎学研究第一人”的史图博先生。一本书,则是他率领调查团队,历经3年的艰苦跋涉,于1932年到1934年进行的对海南岛居民,尤其是黎族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在德国汉堡出版,书名为《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
据称,这本书目前世上仅存两本,一本存放在汉堡的博物馆中,一本存放在本书作者工作的海南大学图书馆,并作为“镇馆之宝”收藏。本书所附史图博《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中的黎锦、黎族装束图片,均是本书作者在原版书上翻拍所得,望读者珍视。
图7 黎族哈方言抱怀人单面传统编织图案
(来源: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2006年6月,“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这一流传数千年之久的海南本土文化惊艳于世。黎锦除了纺、染、织、绣四大绝技被世人了解,黎锦的丰富内涵,尤其是源自新石器时期的各种纹饰也逐渐被世人所知。到了2008年6月,“黎族服饰”又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这一历史文化元素与也许更为久远的服饰文化共同入选国家级“非遗”,黎锦的实用性和服饰文化的连带性、共有性得到了应有的重视。2009年10月,海南省申报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黎锦与服饰文化的继承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意义非同小可。
海南岛因其特殊地理属性,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较小,再加上黎族群众大多居住在人烟稀少的海南岛中南部山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造成了相互之间交流有限。这种原本在地理上的劣势,反倒使得黎锦的纺、染、织、绣传统技艺得以保留至今,殊为难得。
黎锦发展到当下,虽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争议存在,但黎锦核心的原始织造技艺仍然得到了保留并做到了“活态传承”。
针对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最好的尊重方式就是客观和如实地记录!本书作者和团队成员从2002年起,每年都会深入黎族地区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活动,不但积累了经验,也从中学习到了民族民间艺术瑰宝。书中选取了海南省目前仅有的三位黎锦技艺“非遗”国家级传承人:容亚美、刘香兰和符林早的调研手记。但愿这种如实记录的调研方式,对黎锦的传承和保护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