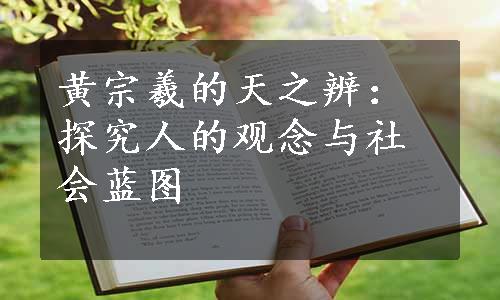
贾庆军
“天”之观念历来为思想史家关注热点,近来又有不少作品探究这一问题。因为在古人那里,天人关系密切非常,天之自然宇宙的运转直接关系到人之政治道德世界的运营,知晓了其关于“天”的观念,也就知晓了其关于“人”的观念。为了透彻了解黄宗羲关于人的观念及其对人类社会蓝图的勾画,有必要先了解其关于“天”的思想。
牟宗三先生曾谈到刘宗周思想中的混乱,说其将官能之“知”混同于良知本体之“知”。而黄宗羲似乎也继承了其先师的这一特点。在他论述天人之概念时,也出现了某种混乱和矛盾。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两种“天”的概念。
在其《易学象术论》中,黄宗羲说:
“夫太虚,絪缊相感,止有一气,无所谓天气也,无所谓地气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见,则谓之天,自其凝滞而有形象,则谓之地。故‘资始资生‘,又日’天施地生',言天唱而不和,地和而不唱。今所谓生者,唱也;所谓成者,和也。……是故一气之流行,无时而息。当其和也,为春,是木之行。和之至而温,为夏,是火之行。温之杀而凉,为秋,是金之行。凉之至而寒,为冬,是水之行。寒之杀则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万物,其凝之之性即土。盖木、火、金、水、土,目虽五而气则一,皆天也;其成形而为万物,皆地也。……是故言五行天生地成,可也;言地生天成,不可也。”
黄氏说得很明白,“天”、“地”皆是“气”,也就是“太虚”。而“气”之不同样态才使我们区分出了“天”和“地”。“气”之“清通而不可见”者为“天”,“凝滞而有形象”者为“地”。无形之“天”是万物的始源,其生化万物的形式就是五行之流行。木、火、金、水是化生万物之动力,它们对“天”之“气”进行调配,以便塑造万物之模型,而土则最终将万物之模型定型。五行皆属无形之“天”,即无形之“气”。而最后万物的有形和生成就是“地”。所以说“天施地生”[1]、“天生地成”。虽然“天”、“地”有先后之别,但它们终究属于一气:一为气之始(无形),一为气之终(有形)。天为体,地为用,体用一源。
对于“天”之始源,黄氏在别处也多次谈到,如在《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中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在《孟子师说卷二·浩然章》中说:“天地间只有一气,生人生物。”在《孟子师说卷四·人之所以异章》中说:“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纯是一团和气。”我们看到,有时黄氏说“天”生万物,有时说“天地”生万物。这样说并不矛盾,因为万物生成必须要经历由“天”到“地”、“天唱地和”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在黄氏的“气”一元论中,气就是宇宙的本体。而“天”作为“气”之初始形态,也就成为了万物的初祖。
黄氏这一观点无疑承自其师刘宗周,后者说:“惟天太虚,万物皆受铸于虚,故皆有虚体。”“虚即气也……非有非无之间,而即有即无,是谓‘太虚’,又表而尊之曰‘太极在刘氏看来,“天”、“太极”、“太虚”皆是一种样态,即“气”。他说:
“天地之间一气而已。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本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使实有是太极之理,为此气从出之母,则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万物而无穷乎?今日理本无形,故谓之无极,无乃转落注脚。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阳生阴,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而合之只是一个生意,此造化之蕴也。”
与朱子尊奉理之“天”不同,黄、刘皆奉一气之“天”。
那么,此“天”或“气”的具体样态是怎样的呢,它又有怎样的运转法则呢?黄氏说“天”的法则就是“自然”。在《孟子师说卷五·人有言章》中,黄氏写道:
“‘莫之为而为者‘寒暑之不爽其则,万物之各有其序。治乱盈虚,消息盛衰,循环而不已。日月星辰,错行而不失其度,不见有为之迹,顾自然成象,不可谓冥冥之中无所主之者,所谓‘天’者,以主宰言也。……所谓’命’者,以流行言也。流行者虽是不齐,而主宰一定,死忠死孝,当死而死,不失天则之自然,便是正命。若一毫私意于其间,舍义而趋生,非道而富贵,杀不辜,行不义,而得天下,汨没于流行之中,不知主宰为何物,自絶于天,此世人所以不知命也。”
“天”以自然之法则主宰万物。此自然法则也可称为“天理”[2]、“天道”[3]、“天命”[4]等。
将“天”看做是万物始源,似乎没有问题。但是,通过仔细阅读上述文献,我们会发现,在“天”化生万物时,产生了不同分身,出现了另外一个“天”——“理”之天。这就让人产生了困惑,到底孰为真身、孰为主宰。接下来我们就探讨黄氏的第二个“天”。
在《尧以天下与舜章》中,黄氏这样写道:“四时行,百物生,其间主宰谓之天。所谓主宰者,纯是一团虚灵之气,流行于人物。”在《浩然章》他说:“人身虽一气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条理者。自其变者而观之谓之流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谓之主宰。”可见,“气”之“天”不仅会化“生”万物,与万物合一,还会“主宰”万物之运营兴衰,为万物之精。如此,“天”就扮演了两个角色:在其化生万物之体的同时,又化为万物运行之法则。万物运行之法则就是“条理者”,通常被称作“理”。于是,在“天”是“气”的同时,“天”也是“理”。这样,我们就理解黄氏所说的理气合一了。在《生之谓性章》中,他说:“无气外之理,'生之谓性’,未尝不是。”在《形色章》中,他说:“形色,气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自能聪,有目便自能明,口与鼻莫不皆然,理气合一也。”其师刘宗周也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盈天地间皆性也,性也,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即心,即理,即事即物,而浑然一致……所以谓中庸之道也。”在黄、刘看来,天、气、理、心、性、命皆为一。因此,可以说天是“气”,也可以说天是“理”。
照此说,只说天是“气”就行了,因为“理”就是气之理。在太虚氤氲中,气就生意盎然,此生生不息中有主宰,即是“理”。此“理”在人而言就是义与道,“言此气自能有条理而不加横溢,谓之‘道义就此而言,“气”与“理”就是一个包含的关系,没有“气”就没有“理”。“气”似乎就具有了优越性。但是,黄氏却非要说天是“理”,且其学说的主体就是性学,而“性”恰恰是天之“理”降衷于人的结果,即在天即“理”,在人即“性”。稍后会详细解析,兹不赘言。这说明,尽管黄氏认可理气合一,但还是要将“理”与“气”区别开来。在《口之于味章》,他写道:
“耳目口鼻,是气之流行者。离气无所为理,故日性也。然即谓是(为)[5]性,则理气浑矣。乃就气中指出其主宰之命,这方是性。故于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谓之为性也。纲常伦物之则,世人以此为天地万物公共之理,用之范围世教,故日命也。所以后之儒者穷理之学,必从公共处穷之。而吾之所有者惟知觉耳,孟子言此理是人所固有,指出性真,不向天地万物上求,故不谓之命也。顾以上段是气质之性,下段是义理之性,性有二乎?”
这样看来,“气”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气之流行者”。正是这一团生意之气塑造了万物之形状,如上所述,“形色,气也”;一部分是气之“主宰”,即“理”,正是这一“主宰”划定了万物的界限、规范其流行之次序,从而体现了天之性或天之命,如上所述,“天性,理也”。换句话说,“气”是万物形体的塑造者,而气之“理”则是万物性情的缔造者。
这让我们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理论。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有诸多模糊之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其主旨的。邓晓芒先生对其主旨论述得很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实体都是由质料和形式相结合而产生的。而其中使实体成为实体的本质东西就是“形式”。是“形式”而不是“质料”使各个实体区分开来的。而“形式”并不是抽象的样式,还是一种赋形活动。这一能动的“形式”和“质料”相互作用,塑造了整个宇宙。同样清楚的是,黄氏的理气理论和亚氏的形式质料理论是有差异的。首先,黄氏之“气”与亚氏之“质料”并不相同。表面上看,“质料”和“气”都是万物的基质或本体。但其存在状态却不同:黄氏之“气”具有能动和创造的特征,在气化流行中形塑万物;而亚氏的“质料”却是被动的存在。亚氏对“本性”的一种解释也是对“质料”的解释,他说:
“‘本性’的命意又指任何自然物所赖以组成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是未成形的,不能由自己的潜能进行动变;如青铜就说是造像的‘本性’也是青铜器的本性,木器的,本性,就是木,余者以此类推;这些物料被制成产品以后,它们的原始物质仍然保存着在。就是这样,人们对组成万物的自然元素也称为‘本性”
对亚氏来说,这些质料只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它有赖于能动的“形式”助其实现。如果说“气”是创生万物的本源的话,“质料”则只是构成万物的被动基质。在质料之外,另有创造本源。
“如果全无永恒事物,创造过程也不会有;一物必由另一物生成,在这生生不息的创造系列上,必须存在有一原始的非创造事物;万物总不能由无生有,因此这创造与动变的发展也必须有一个初限。每一动变必有一目的,没有无尽止的动变。凡创造之不能达到一个目的,完成一个事物者,这种创造就不会发生;一个动变达到之顷正是一个事物完成的时候。又,因为‘物质’总是不经创变便已存在,物质所由以成就为本体者,即‘怎是‘,也就存在,这可算是合理的;‘怎是‘与‘物质’若两不存在,则一切事物将全不存在,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综合实体之外,必须另有事物,即‘形状或通式”[6]
这里的“物质”就是“质料”,“形状或通式”就是“形式”。亚氏没有交代“物质”或“质料”的来源,只是说其“不经创变便已存在”。这一被动的、潜在的自然基质需要另外一种力量的推动才能成为现实万物,这一推动力就是“形式”,其最高表现形式即最终的动力是“纯形式”,也可以说是“神,于是,同黄氏的气一元创世不同,亚氏则是神与质料之二元创世。而最高的创造者不是“质料”,而是“纯形式”。所以,“气”是万物的初祖,而“质料”则只是万物的组成部分。
其次,黄氏之“理”也与亚氏之“形式”不同。“理”是气之主宰,并不在气外。而亚氏之“形式”却有独立于“质料”的可能,他说:
”请注意物质与通式两不创生——这里我意指最后的切身物质与通式。每一变化之事物必原为某些事物所变,而成为某些事物。使之动变的为切身之动变者;被动变者为物质,动变所成为形式。假如不仅是铜创成为圆,而圆也在创成,铜也在创成,则创成过程将无尽已进行;所以这必须有一个终止。”
在这里,亚氏明确指出“质料”与“形式”是不同的,而且两者不能都创生,否则创生过程将无穷无尽,万物也不会有最终之完成。因此,必须有动变者和被动变者之分。既然“质料”与“形式”两不创生,自然这两者也就不互相生成,“凡具有物质本性的,或其整体包含有物质的事物,则其怎是与它们本身就并不相同”,“公式的成立与否并不依傍生灭过程;因为上面已说过,没有一人生育公式,也没有一事物制造公式。”“怎是”、“公式”都是“形式”的一种,它们与物质(质料)并不相同,也不被事物(包含质料)所创生。而黄氏之“理”却和“气”一起参与了万物的创造,且两者都是动态的。更重要的是,黄氏强调有“气”才有“理”,“理”似乎是由“气”生的。
所以,黄氏之理气观在亚氏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了。黄氏理气观既同亚氏“同一事物不能同一时既是而又不是,或容许其他类似的相反两端”原理相违背,黄氏之“气”同时也是“理”;也不合于亚氏"两不创生"的理论;也冲破了亚氏关于永恒本体不能由质料等诸要素组成的法则。黄氏之理气与万物融为一体;也不合于亚氏无中不生有的法则,黄氏之“气”生出了自身之主宰——“理”。[7]
话转回来,关于气之流行者与气之主宰之区分,黄氏与其师刘宗周似乎不同,刘氏更强调气即性(理)。他说:
“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性。故曰:'性即气,气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学者姑就形下处讨个主宰,则形上之理即此而在。孟夫子特郑重言之,曰‘善养浩然之气'是也。然其工夫实从知言来,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则心有所主,而志常足以帅气,故道义配焉。今之为暴气者,种种蹶趋之状,还中于心,为妄念,为朋思,为任情,为多欲,总缘神明无主。如御马者,失其衔辔,驰骤四出,非马之罪也,御马者之罪也。天道即积气耳,而枢纽之地乃在北辰,故其运为一元之妙,五行顺布,无愆阳伏阴以干之。向微天枢不动者以为之主,则满虚空只是一团游气,顷刻而散,岂不人消物尽?今学者动为暴气所中,苦无法以治之,几欲仇视其心,一切归之断灭。殊不知暴气亦浩然之气所化,只争有主无主间。今若提起主人翁,还他调理,调理处便是义,凡过处是助,不及处是亡,亡助两捐,一操一纵,适当其宜,义于我出,万理无不归根,生气满腔流露,何不浩然?云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动些子,是以谓之气即性。即此是尽性工夫,更无余事。”(www.zuozong.com)
刘氏说得明白,性、气不过是形上、形下之分,而形上之天道(理)又不过是气积之结果,总归只是一气。气与气积所成之枢纽(性或理)不能稍有分离。气与枢纽之同在,才有此气之浩然、湛然,才有天地运转自然浑然。如果枢纽(理)在气之外,则其不过是一不动物而已,理气两不相涉。如此则气必散落无方,理必枯滞憔瘠。惟有性(理)在气中,气、性相为滋始,天道才如春风和气,披拂万物。是以,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养气即是养性。
黄氏本来与刘氏一样,赞同理气合一、性在气中。他在评价卢宁忠的思想时说:
“先生谓‘天地间有是气,则有是性,性为气之官,而纲维乎气者’,是矣。然不知此纲维者,即气之自为纲维,因而名之日性也,若别有一物以为纲维,则理气二矣。”
黄氏赞同卢氏关于“性”主宰、纲维“气”的观点,但他认为有必要澄清的是,是“气”自己主宰、纲维自己,“性”不过是“气”能主宰自己这一功能的命名而已。作为这样一种功能,“性”自然属于“气”。说“性”(理)与“气”,不过是一物有两名,“抑知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
既然如此,黄氏为何会说不能混理气呢?师徒俩的分歧就出在孟子的“口之与味”章,而巧合的是,刘氏也说此章最难解。将两者对此章的理解进行对比,会否发现其中端倪呢?兹录刘氏言如下:
“‘口之于味’一章,最费解说,今略为拈出。盖日耳目口鼻之欲,虽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独无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谓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纲常伦物之则,有至有不至,虽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则所渭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尽人达天之学。盖性命本无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权籍而言,则日命,故尝能为耳目口鼻君;自其体蕴而言,则日性,故可合天人,齐圣凡,而归于一。总许人在心上用功,就气中参出理来,故两下分疏如此。若谓命有不齐,惟圣人全处其丰,岂耳目口鼻之欲,圣人亦处其丰乎?性有不一,惟圣人全出乎理,岂耳目口鼻之性,独非天道之流行乎?审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则性命各有条理,令人一一推诿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后之言性者,离心而言之,离之弗能离,则日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远。离性言命亦然。”
在这段语录后面,是黄氏大段的注解,如此长段的注解在《明儒学案》中很少见,足见黄氏对其之重视。但其注解之内容我们并不陌生,就是前面我们摘录的其《孟子师说》中的“口之于味章”。[8]不同的是,《明儒学案》中在开头处加了一句“羲以性命之辨,莫明于此”,结尾处用“宋儒”替代“顾”,用“岂不误哉”替换了“性有二乎”。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主旨。
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才会明白,黄氏所说的“耳目口鼻是气之流行者”指的是“耳目口鼻之欲”。而造成“耳目口鼻之欲”的“气之流行者”,已经不是本然之“气”,毋宁说是“气质”。这是本然之气受到习染后的结果。[9]如果是本然之气,我们就可以说“气即性,性即气”,但对这受到习染的“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谓之为性也”。为了遏制耳目口鼻之欲,使人们重新认识天理,人们制定了纲常伦物之则,而这被叫做“命”。因此,在有形世界里,本然之气受到习染,其自然天道就不能再称为性,而是人们从可见天地万物上获取的公共之理——“命故“君子言命不言性”。这里的“命”亦不是和本然之气相应的“天命”,而是世间之“命”。然而君子终究会体认到,出于万物之理终究不全,溺于万物之心不过是个认知器官,“吾之所有者惟知觉耳”。离开本然之气的心就逐渐成了枯瘠滞涩的抽象法则。所以,君子要复归本体之心、本然之气,复真正之性或天命。当君子言性不言命时,他就开始追求真正的天道或天命了。当刘氏说“盖性命本无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权籍而言,则日命,故尝能为耳目口鼻君;自其体蕴而言,则日性,故可合天人,齐圣凡,而归于一”时,他是在说性与天命,在这里,性、命是合一的;当黄氏说“乃就气中指出其主宰之命,这方是性”时,他说的是本然之气、天命和性。
所以,黄氏和刘氏都区分出了两种“气”(本然之气和受习染之气)与之相对的两种“命”(天命和人世之命)。但他们并不承认有两种气、两种性和两种命。它们的关系只能是真假,而不能是对等。其中本然之气、天命才能称为性。而习染之气、人世之命只是气、性之不完善的表现,其根本没有独立成性的资格。它不是真性,也不能称其为“气质之性”。因此只是一气、一性、一命。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黄氏一会儿说理气合一,一会儿又说理气不能相混了。在气是本然状态时,气及其主宰“理”是一体的,这时气即性,气即理。而当气成为“习染之气”时,其理就不称为性,而是命了。此命与本然之气判然有别。因此,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看,黄氏依然会承认理气合一、气性合一的。他并没有像朱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提倡理气二元论或形式质料二元论。
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在黄宗羲这里,天既是“气”,也是“理”。当其单独言天即“气”时,此“气”已经包含了“气化流行”与“气之主宰”,也即此时之天是一个理气合一之天。天此时就是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当其言天即“理”时,他业已将万能之“气,,分成了两部分:形上之气(理)和形下之气(流行之气)。而此时之天只是“气之主宰”者。然而,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其复杂关系如下图:
至于为何“部分”能用“整体”的名称,这就是东方哲学特有的逻辑了。用黄宗羲的话说,天既能化生万物,与万物一体,也能跳出万物之外,主宰万物,即天能自己创造自己,也能自己管理自己。天与天的造物就没有了界限,浑然为一。哪里还有部分与整体之分呢?
[1]刘绪义.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一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明)刘宗周.《刘子遗书》卷一《圣学宗要·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注释
[1]“天施"之“施"就是“资始”的意思,相当于后语“天生地成”之“生”;“地生”之生是,,生成”的意思,相当于“天生地成”之“成”。
[2]见《孟子师说卷六·性犹杞柳章》:“告子不识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即谓之天理也。"(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32页)也见《孟子师说卷二·浩然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0页)等。
[3]如《居下位章》所言:“太虚之中,浑沦旁薄,四时不忒,万物发生,无非实理.此天道之诚也”((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94页)等。
[4]除《人有言章》所说,也见《牛山之木章》:“孟子……形容平旦之气,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为知命,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39、140页)也见《尽其心者章》:“造化流行之理,万有不齐,……此不齐者,正是其画一所在,所谓命也。”(《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49页)。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此“为”字,而沈、吴本无此字。从全文来看,此“为”字乃有必要。无此字,“然即谓是性”一语中“是”则为助动词,整句话让人无法明白消为“性”的是“气之流行者”,还是“离气无所为理”之理。有此字,“然即调是为性”一语中“是”则为宾语,易让人明白其指“气之流行者”。故文渊阁本更为宜。奇怪的是,在《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中,黄氏曾将这一段全录于刘子语录之后,在那里,也有此“为”字。见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919页。
[6]文德尔班曾说亚氏的质料概念本身就不确定。见(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0页。黑格尔对亚氏的理解更深入一步。尽管黑格尔的论述也有些混乱,如他一会儿将亚氏的质料等同于潜在性、形式等同于现实性,一会儿又将质料等同于物质、将形式等同于精神(理性),但他看到亚氏的质料和形式范畴更多的是同其可能性与现实性范畴放在一起进行阐释的。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291、352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三章四,第47页。但有时亚氏怀疑这种独立存在,“综合实体(我意指物质和形式在组合中的事物)以外是否另有独立事物?若说此外别无事物,然而一切事物之存寄于物质者既均可灭坏,则我们无以回答不灭坏的问题。如其另有事物,这当是通式或形状。那么何种形式为可能分离而独立,那些又不能,现在很难分明。”(《形而上学》卷十一章二,第213页)
[8]沈、吴本为“仇视”,文渊阁本为“缚束”。根据上下文,刘子似在批释氏之刻意灭心。故说“缚束”更准确,说“仇视”亦通。
[9]沈、吴本为“云”,文渊阁本为“夫”。根据上下文,“夫”更恰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