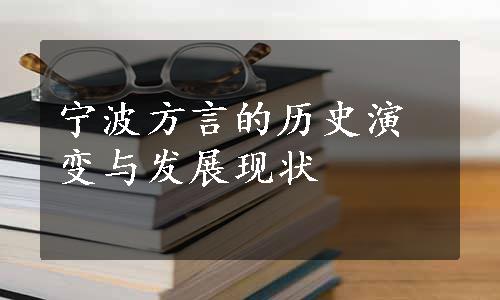
周志锋
宁波方言起源很早,但要钩稽宁波方言形成发展的历史,却比较困难。这是因为,第一,可以用来印证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第二,宁波方言作为吴方言的次方言,文献多以吴语或越语来概括,很少单独标出甬语。但是,既然宁波方言从属于吴方言,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吴语形成发展的历史,来弄清宁波方言历史上的大致情况。
吴语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法,披草莱而邑焉。”唐张守节《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根据记载可知,古吴国亦称勾吴,其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初都蕃离(也作“梅里”,今江苏锡山市东南),后徙都吴(今苏州市);越国亦称於越,其始祖是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古吴越两国都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后裔所建,在上古三代之世就由华夏人作君长,当时的古吴越语其实就是中原华夏语言的分支,而与当时土著百越族所说的越语相去甚远。
吴越两国自古同音同俗。《吕氏春秋·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地域相连,土著民族本来比较接近,加上两国间战争与并吞,促使两国语言和文化不断交流以至于逐渐融合。古吴越语还受到过古楚语的较大影响。一方面,吴越长期是楚的属国,长期接受楚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楚又灭越,尔后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楚国语言和文化对吴越的影响更为加大。另一方面,楚国接受华夏文化最早最全面,通过楚国,吴越进一步接触到了华夏的语言和文化。
总之,古吴越语是先秦中原华夏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形成又受到古楚语影响的一种汉语方言,是今天吴语的前身和源头。
到了汉代,吴语已经演化成与当时中原汉语和其他方言很不相同的一种方言。
东晋南朝是吴语受到中原汉语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吴语本身的变化最为巨大的一个时期。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后,晋室南渡,大批北人随王室渡江南下,中原汉语又给古吴语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北人与吴人长期杂居,语言不可能不发生同化、融合和变异。而正是这种语言接触,使吴语的语言结构和分布范围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唐宋时期,吴语进一步发展,其语言结构和特点也渐趋稳定,成为一种很有个性很有影响的汉语方言。这期间,宋室南迁,吴语再一次受到中原汉语的强烈冲击,特别是杭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渗透进北方官话的许多成分。明郎瑛《七修类稿》中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现代吴语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最迟在元代已经形成。李新魁《“射字法”声类考》一文根据元代吴人陶宗仪《辍耕录》中著录的“射字法”字母诗考订元代吴语的声母,认为“现代吴方言声类系统的规模,在元代已经奠定了”。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韵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明代以后,文献中谈到吴语特点的,也与现代吴语(包括宁波话)大体相同。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吴语黄、王不辨”;明徐渭《南词叙录》“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清潘耒《类音》“歌韵之字,吴音读作模韵;麻韵之字,吴音读作歌韵”;清刘禧延《刘氏遗著》“吴语呼此韵(引者按:指车遮韵)字与家麻无别,车如差,遮如渣,赊如沙,蛇作沙阳声”;清李汝珍《音鉴》“南音或以黄王、湖吴不分”,等等。这说明,明清时代的吴语,已与现代吴语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综上所述,我们对吴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作如下概括:吴语萌芽于先秦,发展于六朝,定型于唐宋,成熟于元明。这个过程,也就是宁波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大致过程。
古代文献中明确指明宁波方言的材料比较少,并且大多是明清以后的。现就我们目力所及,酌举十条如次:
(1)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今古方言大略》:“凡取物……宁波、浙东日驼。”明清例多,如:明陆人龙《型世言》第二十七回:“驼茶来,先生但说何妨。”清鹫林斗山学者《跨天虹》第五卷第一则:“半当儿子半当奴才,服侍自己的儿子,拿书包,驼雨伞。”“驼”也作“驮”,明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第三十七回:“你就驮请帖我看。”清菊畦子《醒世奇言》第十回:“那眼泪滴在床上,被褥都湿得水里驮起来一般。”“驼”又作“拕”,清欧阳钜源《负曝闲谈》第十九回:“马车钱准其明日子到华安里去拕。”今宁波话仍管拿、取叫“驼”,如衣裳驼过来;手里驼本书。《戒庵老人漫笔》另有“视谓之张",“扶谓之当去声”,“按谓之钦去声”,“浮谓之吞上声”,“虹谓之吼”,“捧谓之掇”,“藏物谓之园音抗”,“整叠谓之周捉”,“器用日家生,一日家火,又日家私”,“抱持人物日探音杰”,等等。虽然没有标明方言地域,但也可以看做是宁波方言,因为今天宁波话仍旧这么说。
(2)明席浪仙《石点头》第十四回:“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篷篷,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话虽不同,光景则一。”文中介绍了各处乡语关于“鸡奸”的不同说法,其中宁波人叫“善善”,慈溪叫“戏虾蟆”。
(3)明无名氏《鸣凤记·严嵩庆寿》:"[丑]牛大叔,昨日小礼到了么?……[副末]这个有了。只是少些。[丑背云]这个戏丫麻,一百两银子还嫌少哩。[副末]你怎么骂我?[丑]岂敢骂大叔。我慈溪乡语,但是敬重那人,就叫他是戏丫麻了。[副末]如此多叫我几声,折了银了罢。[丑]这个就叫戏丫麻,戏丫麻,嵯娘戏丫麻。[副末]怎么有个娘字在里面?[丑]娘者是好也。[副末]罢罢。我不计较了。”这出戏说的是慈溪人赵文华“名登黄甲,官拜刑曹”后,为了“附势趋权,市恩固宠”,趁严嵩寿庆之际,用厚礼贿赂严嵩父子,甚至连“他家书房内罗龙文、门上牛班头,又各送银一百两,求他为先容之地”。上文是赵文华赴严府祝寿时与“门上牛班头”的一段对话。其中“戏丫麻”一语是赵文华用“慈溪乡语”骂人,其中“戏”即交媾;“丫麻”宁波话有两义,一是贬称嘴巴,二是指女阴,此当指后一义。“戏丫麻”相当于今之口语“娘戏胭”(“胭"即女阴,《广韵·质韵》:“胭,牝䏘。”譬吉切)。又,上条提到,“鸡奸”明代慈溪话叫“戏虾蟆“,颇疑“戏丫麻”与“戏虾蟆”是一语之转,因为男女性交跟男子与男子性交毕竟有诸多类同之处。
(4)清王濬卿《冷眼观》第十七回:“不意话犹未了,只见一个小茶房走来,对着仲芳道:'叹嗱,那处没寻到,叹嗱,你先生还在这里,娘个细劈,船主叫请买办呢,快点儿上去罢,叹嗱,细劈,急的狠呢。’仲芳听了,便随着那宁波老,三步两步的走去。”“叹嗱”、“细劈”本为皆词秽语,这里成为宁波小茶房的口头禅,今天口语中也有这种情况。其中“细劈”即“戏胭”,性交。字又作“戏辟”,清陆士谭《新上海》第十三回:“忽见那边码头上,许多人都指着只轮船破口大骂……走近了,听得骂人的都是宁波口音:'妈戏辟,妈戏辟’不绝于耳。”又作“希匹”,蒋介石好骂“娘希匹”,例见唐人《金陵春梦》。
(5)清陆士谔《新上海》第三十九回:“法庐向刁邦之道:‘阿拉行里,昨晚头贼骨头爬进东,偷掉一百个金八开,今明天亮头,外国人得知了,跳得八丈高呢。昼过时光,阿七、小山被外国人喊了包打听,都送进巡捕房东。阿拉总算运道高,这几天恰巧喊替工东。’刁邦之道:’这也是无妄之灾。'法庐道:’小山、阿七原也不好,三不时有朋友来打横。(“阿拉”,我们也;“贼骨头”,小窃也,爬走也;“今明”,今朝也;“天亮头”,午前也;“昼过”,下午也;“打横”,游玩也;“东”,语助词。以上都是宁波土白)外国人心里本有点子不对,才吃着这冤枉官司。'”下文:“法庐道:’尽可放心,阿拉行里外国人,从没有说谎话过。前年子,阿拉兄弟在行里做时光,外国人与其非凡要好。有一朝,外国人问其老人有没有,阿拉兄弟回老人还没有抬过。外国人说,只要服侍得我舒服,我拕出洋钱来替你抬一个老人。后来阿拉弟媳妇,果然是外国人拕出洋钱来抬的。邦之哥,你想阿拉行里外国人,诚实不诚实?’(“其”,他也;“老人”,妻也;“抬”,娶也;“拕”,拿也)龙吟见法庐一口宁波土音,又是开口‘阿拉行里‘,闭口‘阿拉行里’,心里早又转了念头。”上文法庐说的话是地道的宁波方言,作者还特意为一些宁波方言词语作了注解,如妻子叫“老人”,娶媳妇叫“抬老人”,今北仑柴桥、郭巨一带方言还这么说;其中“昼过”解作“下午”不确,当为中午。
(6)清欧阳钜源《负曝闲谈》第十九回:“黄子文跳下车来,叫他明天到华安里来拿钱。马夫不甚愿意,说道:‘老板,马车钱准其明日子到华安里去拕,阿拉格酒钱,是勿能欠格哙。在上海当马夫的是宁波人,其中“拕”、“阿拉”都是正宗的宁波话。
(7)清姬文《市声》第二十六回:“子肃大喜道:,趁着在船上没事,我们凑成一局好不好呢?那二位挨拉朋友,要算得好手。‘要知‘挨拉朋友',就是会唱戏的人,都是宁波原籍,却生长在上海的。一是余小春,一是周大喜。子肃虽说他们是,挨拉朋友,,其实两人说得一口好官话,‘挨拉’的土音早已没有了。子肃要说他碰和好,特提出他是宁波人来。”《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捐班道府,为舍勿要考?单驼得挨拉开心。”“挨拉”也作“阿勒”(见《九尾狐》),通作“阿拉”,宁波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我们,我。今上海话也用此词,颜逸明《吴语概说》谓“一般认为是晚近从宁波借入的“,许宝华、陶寰《上海方言词典》谓“来自宁波话”。
(8)清梦花馆主《九尾狐》第三十四回:“宝玉又道:‘钱老阿肯领奴到里向去白相相佬?”慕颜点头道:,可以可以。横竖其(宁波人自称妻大半日“其”,或称“阿勒女人”)勿在家(读瓜)里,唔到我(读瓦)房里都勿要紧喑。‘宝玉道:’听僚实梗说法,倷怕唔笃大太太格哉啘。'慕颜道:’并勿是怕其,不过免得淘气,遮遮眼睛拉,轧实其是贤惠皓。我讨三个小老婆,其都勿管我(读瓦)咯。倘然我要瞒其,乌糟糟轧仔妹头,拨其晓得仔,其就要娘戏娘倒辱的。’”以上写的是清末沪上名妓胡宝玉与宁波富翁钱慕颜的一段对话。钱慕颜说的是宁波方言,比如“娘戏娘倒辱”,现在还有“娘死娘倒辱人家”的说法(原文戏当做死,白读;辱通詈,骂)。
(9)清毛奇龄《越语肯紫录》:“余姚人皆物之丑者曰堪。或询之,曰:堪者,不堪也,反词。今观隋韵,知为領字也。領音堪,物丑貌。”1915年《象山县志》:“堪,可也,而以不美者为堪。”考《广韵·覃韵》:領、丑皃。堪,任也,胜也,克也。"“領’、“堪”同为口含切。余姚、象山话“堪”有丑、坏之义,本字为‘領',明清白话小说则作“堪”。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那时节寻些事故,不必嚷闹,待我做堪做好,劝他丢开,到是善开交。”清谷口生等《生绡剪》第十四回:“这举人姓毕名荣,性极贪痴,随着人的东西,不论堪好,他要开口讨讨看的。”又:“不管几等秀才,见他时节,堪好横晕饭、竖晕饭,尽情轻薄。”今宁波话“堪”单独不表坏义,但有“堪好”一词,义为肯定、必定,如该只西瓜堪好生咯;大学堪好考勒进咯。“堪好”又可说成“好坏”,其中“堪”正表坏义。俗作“看好”,误。
(10)清于鬯《香草续校书》注《墨子·贵义》“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云:“即犹言何以也。以、有叠韵。今宁波人言有,犹作以音。”按:今宁波“有”不读“以”音,但“又”正读“以”音(又、有古代同音通用),如:上日落雨,今末以落雨;该后生家生勒以长以大。
语言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当中,这种变化是渐变的。但是,语言又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会引起语言的相应变革,方言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文化教育的发展、经济交往的扩大、外来人口的增加、有声媒体的普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宁波方言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大、变化之快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有鉴于此,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宁波方言称为当代宁波方言。下面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简要介绍当代宁波方言的演变情况。
关于宁波话语音(声韵调)简化情况,不再赘述。这里仅从浊音清化、白读弱化两个角度来观察宁波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浊音清化,是指宁波方言中原来读浊音的字受普通话的影响读为清音了。例如:中文系的“系”《广韵》胡计切,关系的“系”(本作係)《集韵》胡计切,都为匣母字,本读浊音[h]声母,今读清音[ε]声母;复原、复辟、恢复、年复一年的“复”,《广韵》有房六、扶富二切,奉母字,本读浊音M声母,今读清音[f]声母;取缔、缔造的“缔”《广韵》有特计、杜奚二切,定母字,本读浊音[d]声母,今读清音[t]声母;朗诵、传诵、诵读的“诵”,《广韵》似用切,邪母字,本读浊音[dz]声母,今多读清音回声母;诉讼的“讼”也是似用切,浊音字,今多读回声母;姓氏“解”《广韵》胡买切,匣母字,本读浊音[h]声母,今多读清音[ε]声母。他如“穴、殊、仲、颂、乎、雅”等字,年轻人现多念作清声母。(www.zuozong.com)
白读弱化,是指宁波方言中原来有文白二读的字,其白读受普通话的影响逐渐消亡而变为文读了。例如:恢复的“恢”,白读[k'ueI53](《广韵》苦回切),文读[hueI53],今白读已经很少听到了;归家、归去的“归”,白读[tεy53]或[ky53],文读[kuc53]现在白读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才说;请柬的“柬”白读[kε53](《广韵》古限切,与拣同音),文读年产],今白读几乎不说了。
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是最活跃、最善变的一个要素。当代宁波方言词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些方言词随着所表示的旧事物消亡而消亡。例如:宁波老话有“缭缴”一词,近人应钟《甬言稽诂·释衣》:“甬之劳役者,系于胸腰之长布,形如缴身带……俗名缭缴。”“缭缴”是旧时男子干活时系在胸腰间的长布带,现在几乎看不到了,这一方言词也就逐渐被淘汰了。“牛车盘”指牛牵水车中带齿轮的大圆木盘,也指装有水车大圆木盘的地方。在抽水机替代水车的今天,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牛车盘”为何物了。“冰厂”是过去储藏冰块的地方,底部长方形,篮球场大小,四周用土垒起来,上半部分盖稻草。现在早已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冷冻厂”(两者功能不完全一样),因而“冰厂”一词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揭袜底”即在袜子的底部加一层结实的布,使耐磨耐穿。现在生活好了,没有人这样做了,这个词也慢慢被淡忘了。“关肚仙”是女巫装神弄鬼替人祈福禳灾的一种迷信活动,随着社会进步,这个词也就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其他如“凉床、火柜、被柜、疥橱、幢箱橱、幢篮、拗斗、挈当、马嘴、褓裙、火熄、火管、火锹、木屐、美孚灯、点亮(指点煤油灯)、拄鞋、缉鞋底”等同语,城镇里的年轻人已经感到很陌生了。
有些方言词说法有了变化,逐渐向普通话靠拢。例如:台风过去叫“风潮”或“风水”,刮台风叫“做风潮”或“做风水”,现在“做风潮”不说了,“做风水”年纪大的人才说,一般都说“刮台风”。个人的图章过去叫“图书”或“私章”,现在“图书”不说了,大多说成“私章”或“图章”。发烧过去叫“劳发”或“肌身热”,现在“劳发”听不到了,中老年说“肌身热”,年轻人一般说“发热”。近视眼过去叫“近嚓(tεi44州艮”或“近觑眼”,现在都叫“近视眼”。胃过去叫“胃家”、“饭包”、“食包”等,现在一般都叫“胃”。虹过去叫“鲎”,现在年轻人不知“鲎”为何物了,都说“虹"。缝纫机过去叫“铁车”或“洋车”,现在多说“缝衣机”或“缝纫机”。手电筒过去叫“电光灯”,现在年轻人叫“手电筒”。老虎钳过去又叫“硬嘴巴”,现在多叫“老虎钳”。菠菜过去叫“菠薐”,现在年轻人多叫“菠菜"。杏儿过去又叫“杏梅”,现在叫“杏子”。粉丝过去叫"细粉"或“粉干”,现在叫“粉丝”。仔细过去叫“仔洁”,现在说“仔细”。过去买米叫“汆米”,买肉叫“斩肉”,买油叫“打油”,买布叫“扯布”,现在则分别叫做“买米”、“买肉”、“买油"、“买布"。表示可能、恐怕意思的副词宁波老话有"莫(mɔ44)"、“莫怕”、“阿防”、“腕数”、“作兴”、“弄勿好”等,现在一般都说“可能”或“恐怕”。
新的方言词不断产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事物、新概念不断涌现,新的方言词也被不断创造出来。例如:第一(开始,当初)、一级(最好)、正式(真的,确实)、感冒(反感,厌恶)、号头(记月的单位,来自上海话)、家头(计算人的量词,来自上海话)、接头(了解情况)、夯头(市井上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坏毛病(癌症的讳称)、恶毛病(癌症的讳称)、外国人(对外地打工者不尊敬称呼)、掏糨糊(把事情搅糊涂)、米(钱)、一般般(一般)、包包(包的爱称)、狗狗(狗的爱称)、伊妹儿(电子邮件,E-mail的音译)、东东(东西,来自网络语言)、钱途(人的财运,来自网络语言)、菜鸟(初学者,傻瓜,来自网络语言)等。其中有关“脑子”的新词语最为丰富多彩,如:搅(go213)脑子(把思路搅浑;用歪理纠缠)、脑子进水、脑子敲秗(iI55)、脑子短路(傻了,呆了)、脑子搭错、脑子错拼、脑子塞煞(以上都比喻或形容脑子出了问题)、脑筋(εi53)粉燥(形容脑袋很笨,思维枯竭),等等。
与语音、词汇相比,语法的变化比较缓慢,但也有一些变化。从词法看,词缀“个”过去用得比较多,如“轻轻个、薄薄个、定定个、儇儇个、健健个、静静个”等,现在后缀“个”已很少用了。相反,有些本来不用词缀的单音词受普通话影响而增加了后缀,如“筷、裤、鞋、袜、兔”等年轻人大多说成“筷子、裤子、鞋子、袜子、兔子”。从词类看,原本丰富多彩的虚词数量在减少,说法在变换。如“暴时”(起初,初次)、“划只(tεi55),,(只是,只有)、“放命,,(格夕卜)、“阴骘”(极其)、“兜心”(完全,彻底)、“笃知”(如果,万一)、“铁爬”(如果,万一)等富有特色的副词和连词如今已不大说了,或换成了其他说法,往往是换成跟普通话接近的说法。再如助词“仔”(相当于普通话的“了”),现在年轻人多说“了”,字通常写作“勒”,如:饭吃仔/勒再讲;大学毕业仔/勒马上找对象。从句法看,老派宁波话有一种用“动补结构+凑”来表示动作重复的句式,如“吃碗凑、加眼凑、买本凑”等。已经不大有人说了,而说成“再吃碗、再加眼、再买本”等。
当代宁波方言的快速变化是社会历史文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建国以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这对方言的冲击和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宁波人的文化索质,从而为更好地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奠定了基础。可以这么说,普通话越推广,教育越发展,人们说普通话的水平就越提高,而说方言的能力就越变弱。现在城里(包括许多农村)孩子从小受到普通话的熏陶,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讲普通话,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地道的宁波话却不会讲了。他们说的宁波话,往往是异化了的宁波话,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普通话的成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所说的宁波话与他们父辈、祖父辈所说的宁波话的差异,正好反映了当代宁波方言的发展变化。
宁波有许多外来人口,解放初就有大批南下干部留在宁波。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作为一个开放城市,吸引了大量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员到宁波工作。至于暂住打工的外来人口为数更多,2007年3月宁波市政府报告中的数据表明,宁波全市常住人口基数为700多万,而外来流动人口已超过290万,占常住人口的41.4%,居浙江省第一。外来人口对宁波方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的方言(主要是北方方言)会影响宁波话;二是由于方言不便交流,促使宁波人使用共同语。这也是当代宁波方言发生变化而向普通话靠拢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宁波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在频繁的对外交往过程中,“石骨铁硬”的宁波活显然成了沟通的一大障碍。正是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使宁波人认识到普通话是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普通话(哪怕是“灵桥牌普通话”)进行交际。这客观上促进了当代宁波方言向普通话靠拢。
广播、电视等有声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为人们学习普通话提供了便利条件。许多宁波人就是通过广播、电视学会普通话、提高普通话水平的。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过程中,自己的母语宁波方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
语言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宁波人特别是青年以下的宁波人越来越感到方言的“土”和普通话的“雅”,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少数人甚至对自己的方言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不愿意说宁波话。语言观念的变化加速了当代宁波方言向普通话靠拢。
此外,当代宁波方言还受到周边地区方言如上海话、杭州话、舟山话等的影响,受到港、台语的影响,甚至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
汉语方言发展演变总的规律和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宁波方言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推广普通话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方言向共同语靠拢体现了由分散趋向统一这种语言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推广普通话,方言向共同语靠拢是大势所趋,毋庸置疑的。但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方言在彰显地方个性、维系乡土情感、丰富语言生活、保存古老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宁波方言也是一样,它既是宁波人的重要交际工具,又是宁波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尽管宁波方言使用范围、使用人数和使用环境等正在发生变化,但它仍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宁波方言影视节目如《来发讲啥西》、《阿国电影》、《讲大道》、《阿磊讲故事》等相继推出并受到宁波人普遍欢迎,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生活多元化的需求和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宁波方言的喜爱和认同。随着宁波经济发展和地位提升,许多在宁波工作的外地人也纷纷学习宁波话,宁波新干线培训学校还开设了宁波话培训班。
为了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好宁波方言,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深入全面地调查和研究宁波方言。依托现有基础,对宁波方言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宁波方言(包括所属各县市区方言)的现状进行过细的调查和描写,彻底弄清宁波方言的面貌。在此基础上,绘制方言地图,出版系列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
其次,利用现代化手段,建立宁波话音像档案,以便将某一时期的宁波方言面貌客观、完整、长期地保留下来。
再次,加大宁波方言的宣传力度。用宁波方言播报或表演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及戏曲等为宁波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由于它们受众广,影响大,客观上对宣传宁波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对其加以支持和扶助;要编写出版介绍和学习宁波话的通俗读物及其电子产品;有计划地组织举办宁波方言讲座;根据需要,增设宁波话培训班。
最后,重视宁波方言的家庭教育。语言要从小学习,而父母是孩子学习母语的最好老师。作为父母,要纠正方言“土”、“俗”的观念,在教育孩子说普通话的同时,也有责任教会孩子世代相传的宁波话,以便更好地传承乡土文化。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1]李新魁.吴语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究,1987(5)
[2]张光宇.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中国语文,1994(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