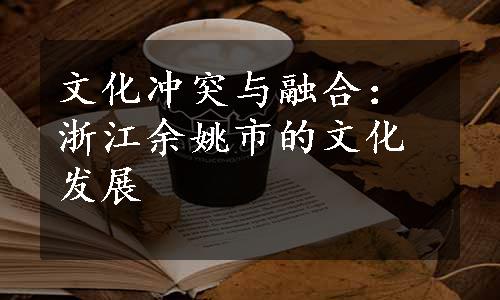
王辉
葛剑雄在研究中国古代至现代的移民史时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放眼当代中国,从中西部等地区流出的农民工对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影响和贡献是全面而深远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农民工与资本、城市、其他阶层群体的冲突与博弈,大都属于经济意义上的劳资冲突。同样,我们谈到农民工的贡献,也大都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没有看到他们对地区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与贡献。
如果说经济贡献在不影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从道德意义上说起,如果说劳资冲突即使谈虎色变但在维护和谐稳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提及,那么,农民工的文化贡献在“素质低”这个带有“污名化”说法的前提下,就几乎从未登上学术和官方的大雅之堂。同样,1990年代兴起的中国农民工研究,大都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社会研究,而不是人文研究,故不免有着“见社会不见人”(费孝通语)的缺憾[1]。
2004年开始兴起的“民工荒”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开始面临“刘易斯拐点”,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民工荒”再次证明了这一点[2]。我们的农民工研究也同样面临转型,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不能只是社会科学一枝独秀,也要注意运用人文学科,因为“农民工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两条腿走路,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农民工。
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从人文学科出发,结合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描述流出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因文化而引起的冲突,并说明这种冲突促进了社会融合,及其在地方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笔者选取了浙江省余姚市作为研究样本。原因有二。第一,从研究者的条件看,1995年以来本人一直生活并工作在余姚,对新老余姚人都非常了解,同时对长三角地区如浙江省其他县市及苏南、上海也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从研究对象看,余姚文化悠久昌盛,自古便有“文献名邦”、“东南名邑”之称,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文化大师皆驰名中外。而且,余姚县域经济很发达,自1990年代起,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纷纷涌入,成为余姚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被余姚社会逐渐认同与接纳的“新余姚人”,并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生态。
本文中提及的“新老余姚人”是以户籍制度来定义的,是一种地方语境中的称谓。所谓“老余姚人”,即拥有余姚常住户口、在余姚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与地方语境中的“本地人”等称谓相同;所谓“新余姚人”,大都来自安徽、江西、四川、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地区,以知识、职业分标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即大学毕业后来到余姚企业中从事知识劳动的知识工作者,如:外贸销售员、技术骨干、人力资源经理、财务会计、办公室主任等等;另一种,就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占了“新余姚人”的大部分。
面对几十万、几百万、上亿并不断分化的人口,任何简单的称谓都会遮掩事实真相,因此,本文中所谓的“新余姚人”,基本上等同于国家语境中“农民工”一说,同时又与地方语境中的“外地人”、“外来人口”、“打工者”、“外来大学生”是同义的。在文中,根据不同语境的行文方便来使用。
本文中的小传统,是指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方基层社区流传的文化,体现在语言、风俗、民间文艺、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地域性、民间性、通俗性、大众性的特点。笔者这个观点,是受海外学者余英时的专著《土与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中国文化,余英时运用人类学家雷菲德(Robert Redfield)的理论认为它存在着“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部分,换言之,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小传统就是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余英时认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余英时又认为,这两种传统与文化包含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依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是儒家,当代中国的大传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历史或当代的大传统是什么,中国各个地域的、民间的、通俗的小传统文化都不尽然一致,正如葛剑雄所说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使文化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以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县级市余姚为例,在广义上,其文化隶属于中国文化,但它同中国其他地方如中西部的地域文化就有很大不同,就是同周边县市如绍兴、宁波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当代余姚籍学者、作家余秋雨在其散文《乡关何处》中描述过这种差异:
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维艰的。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
历史地看,余姚文化的发展同人口流动紧密相关,在东汉和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使北方中原人口迁徙来到了余姚及其他南方地区。先秦时代,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都在中原黄河流域,余姚以及整个吴越的文化皆难与其相媲美。从东汉起,北方中原移民带来了儒家文化,余姚的文化开始兴起发展起来。东汉初,余姚人严子陵获得了光武帝刘秀的推崇;三国年间,余姚人虞都是东吴孙权集团最有成就的学者;唐朝初期,余姚虞氏家族的虞世南受到唐太宗的敬重。到了明代,吴越江南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而越地余姚的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更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级的思想家、文化大师。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余姚迎来了有史以来又一次——远远超过东汉和南宋——人口流动的高峰,这就是民工潮。到了2009年,余姚本地人口83万,外来人口则达到50万[3]。
不过,同样是人口流动,原因却不同,古代是因为战争,当代则是因为经济发展。
浙江经济的特点在于县域经济发达,全国经济百强县中浙江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余姚市就位居全国经济百强县前十名。县域经济实力来自民营经济。从发展历程看,余姚民营企业大多是从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演变而来的。余姚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草根精英,是农民企业家。余姚的许多企业往往位于某个乡镇村庄的境域。而在工业推动下,余姚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便出现许多的文明村、小康村,即社会学意义上的“超级村庄”,如余姚市泗门镇的16个行政村全都进入全国或省市文明村的行列[4]。
余姚县域经济的性质,决定劳动力的分布与配置。
其一,人口分布上,外来农民工到余姚以后,并不全部聚集在余姚市区,而是大量分布在农村、社区。在余姚的许多村庄,外来人口与本村人口持平,甚至数倍于本村人口,就是一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山区村也有外来农民工。
其二,身份制度上,无论是83万老余姚人,还是50万新余姚人,大多是农民,都有着深刻的农村社会经验,具有农村乡土文化的传统。
其三,工人结构上,余姚民营企业(许多都位于农村社区)的工人中,一部分是离土不离乡的本村农民,一部分是离土离乡的外省市农民,数量上后者超过前者。
其四,文化学历上,来自安徽、四川、江西、河南、贵州的50万外来农民工大多只有初中学历,他们所带来的大都不是知识、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等“大传统”,而是全国各省、市、县、乡镇、村的“小传统”。而余姚本地人呢,2008年的一个数据显示,余姚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5.6万人,这同83万常住人口总量相比仍然偏少。也就是说,在余姚,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大多数人都不是什么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对大传统并不特别了解或有所研究、造诣,他们所拥有和信奉的是各自的小传统。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余姚的一些社区,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还是经济意义上的企业社区,其社区内的成员大都是农民——本土农民与外来农民。余姚本土农民有着自己的小传统,外来农民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并多得惊人的小传统。这样,各种小传统与中国大传统是大体相同的,可小传统彼此之间又存在各自的差异。信奉各自小传统的余姚农民、安徽农民、江西农民、四川农民、河南农民、贵州农民之间,必然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产生误解和冲突。并且,差异越大,理解程度就越难,接受容纳的程度就越慢,由此形成的冲突就越多和越大。
本来,余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交流语言是余姚方言。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推动下,余姚人的语言交流受到了两大影响:英语和普通话。
(1)普通话受到抵制和排斥。英语在余姚风行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余姚的乡镇企业家用普通话“走遍千山万水”,但与国际市场接轨后,无论乡镇企业家们——他们大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多么聪明智慧、能说会道,在与外商打交道时,都必须通过英语专业人才来当翻译,替自己的企业打开国际市场。1994年,笔者所在的小路下村的村办厂从西安一所大学一下子招收了20名外贸专业大学毕业生,地方报纸在头版显著位置对此作了报道。2007年6月,一位余姚青年企业家告诉笔者,1996年他毕业时只有中专学历,但也有机会到一家著名乡镇企业从事外贸工作并担任董事长助理,当时英语人才稀缺,初具英语基础的他也符合企业的需要。
普通话在余姚的流行主要是由于新余姚人的到来。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起,推广普通话就已成为中国的语言政策,并以宪法作了规定,但在人口流动不大的地方社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远远没有像方言那样更符合余姚人的交流需要。到了90年代,大量外来人口从全国各地涌来。在某些村镇社区,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人口数量达到1:1、甚至数倍于本地人时,余姚人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自己不太习惯的语言工具。
然而,普通话和英语虽然同时在余姚流行,但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具有优越感与合法性,而是一度受到余姚人的抵制与排斥。长期以来,普通话像英语一样被余姚百姓一律称作“外国闲话”,一声“外地人”在余姚语气中是非常难听的词语,就像当初的“乡下人”、“乡巴佬”在城里人的语气中非常难听一样。2000年,一位外地装潢工人告诉笔者,他在余姚和宁波一些市民家中干活时,当地包头告诉他不要讲“外国闲话”——普通话,以免东家听到后会感到不放心。
中国及世界的历史表明,语言的优势同地区和国家的实力相关。北京话从方言变为“国语”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此前的中国历史上,西周时建都陕西,陕西话才是“雅言”,孔子等儒家土人在正式场合都使用“雅言”来交流和诵读经书。宋代建都开封,讲开封方言也是土人的时尚。南宋都城杭州城中,来自北方特别是首都开封的移民不但数量多,而且包括皇帝宗室、文武高官、富商大贾、文人学士等上层人士,使移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优势,天长日久,原有的杭州方言被一种新的带有明显的开封话特色的方言所取代,以至今日,杭州话还是带北方味的半官话,与毗邻地区的方言完全不同。国外经验也是这样的,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法语才是最有优势的语言。20世纪以后,法语的优越地位被英语替代,但是法国人至今仍然具有自己的语言优越感,看不起英语。
当代中国也是这样的,余姚话、宁波话、上海话、广东话的优越感同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实力相关。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自边缘的、贫困的中西部地区,既不像说英语的老外具有国际背景,又不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上处于上风,自然要受到本地语言的排斥和抵制。
(2)说普通话的困难。余姚话属于吴方言,同以北方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国方言,在发音上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方言中,余姚话可能是最难懂、最难学的一种,同样,在这个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也就更大。余姚老百姓抵制普通话,主要是他们习惯讲余姚方言,很难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如果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很少外出的话,难度就更大。有一些村镇干部,在与外地嘉宾或者省市中央政府的官员接触时,要么习惯性地讲一口余姚话,要么努力地用一口别扭的普通话来介绍和汇报工作,以至让外地嘉宾和省市中央官员如听天书,不知所云,这时,市长或市委书记(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市)竟给自己的下属充当起了普通话翻译。
(3)因为口音而发生误解和冲突。其实,如果没有像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受过专业的语言训练,那么,中国大多数方言区的人,在讲普通话时也不是十分标准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地方口音。许多余姚人在讲普通话时,往往用“姚普”来自嘲。而外地人呢,以在余姚人口较多的安徽人、四川人、贵州人为例,他们讲普通话时也夹杂了地方方言和地方口音。这往往又给对方的理解造成障碍。
时常可以看到,余姚人在饭店里吃饭时,很习惯性地用余姚方言或带有浓厚余姚口音的普通话来指称菜名,而服务员往往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工,由于听错了、听不懂,就往往给端上了另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菜肴,这让余姚人既好气又好笑。
一位余姚企业家曾跟笔者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浙江人到北方城市出差,在一家饭店里要吃水饺,问老板娘:“水饺多少一碗?”这句话本无错误,但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便变成了“睡觉,多少一晚?”
"流氓!"老板娘一听,生气了。
可她的这一句骂人的话,在浙江人听起来,变成了“6毛”。
“好!”浙江人说,“来一碗”。
“来一晚?”北方的老板娘更生气了,便照准浙江人,来了一巴掌。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饮食也不一样,早在古代中国就形成了鲁菜、苏菜、粤菜、川菜等菜系。在不同地方,吃着不同饭菜长大的人,即使已经离开了故乡,但他仍从心理和生理上都怀想故乡的饭菜。《史记》记载,汉高祖得天下后回到故乡,“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席间,刘邦“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日: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晋书》记载,晋代苏州人张翰在京都洛阳做官,见秋风乍起,忽念家乡莼妒鲜美,毅然辞官不做,挂印返乡。
到了当代,余姚——区区一个县级市,居然云集了五十万全国各地的人,彼此之间在饮食上都不尽相同,这必然影响到彼此在私生活中的相处。科塞(Coser)认为,在一个内群体中,关系越紧密的,相互间的冲突也就越剧烈。从一个县级市,特别是一个村庄社区来看,基本上可以把本地人和外地人都视作一个关系紧密的内群体。他们在工作领域由于利益而发生劳动纠纷,在私生活领域则往往因为小传统而发生文化冲突。
(1)新余姚人对余姚饭菜的态度。城市和当地舆论谈到外来农民工时,总是用“融入”和“适应”等词汇来要求。其实,一般人很难甚至无法“融入”和完全“适应”异地的饮食方式,其过程要让人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2008年,一个东北小伙告诉笔者,“余姚饭”同“韩国饭”、“俄罗斯饭”,三者相比,他更适应后两种,可能是东北与韩国、俄罗斯的地理距离较浙江余姚更近的缘故。
(2)余姚人对外地饭菜的态度。余姚人在家乡,无论是家里、饭店里、单位食堂里,都可以很方便地吃到余姚本地饭菜。在平时交往中,讨;论某种饭菜的味道、做法,也是余姚人的交流话题之一。近些年,旅游热兴起,余姚人到四川、贵州、江西、北京、海南等地旅游时,一面很兴高采烈,一面却大谈苦经,主要自己在外面吃不好。为什么吃不好呢?余姚人普遍认为:外地饭菜不好吃。当然不是外地饭菜真的不好吃,否则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承受这种不必要的痛苦。余姚人这样说,是因为长期的生活方式所致。
(3)对待辣椒的态度。余姚本地人和外地人在饮食方面最大的不同,体现在辣椒方面。对江西、安徽、四川、贵州这些中西部地区的人来说,辣椒或带有辣味的食物是生活的必需品,故有这样一句话:“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不怕辣。”而余姚人和宁波人喜吃海鲜——这在全国是排第一的,大多数人不吃辣椒和带有辣味的食品,他们看到外地人满脸大汗,吃着红红的辣味食品,就感到不可思议。
在中国,吃饭还是一种工作方式,很多重要的交易与决策是在饭桌上达成的。如果在宴席上“同桌异梦”,不能尽情享受同样的佳肴,对个人的发展、生意的洽谈、现场的气氛都有着不利的影响。(www.zuozong.com)
在中国,饮食文化还是一种政治文化,与人的地位、权力、财富、声望密切相关,如《老子》中提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把饮食当做一个国家战略。2009年9月,笔者听到一位余姚企业主在饭桌上谈到余姚两家五星级宾馆时认为,余姚有83万人,但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机会进到五星级宾馆吃饭。那么,相对于在财富、地位、权力、声望上皆处于下风的外来农民工说,这个机会就更少。也就是说,新余姚人同老余姚人在一起进餐——尤其是在高级饭店里——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这当然会影响到群体和阶层的融合。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民受到民粹主义般的赞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尤其农民工却受到了“污名化”的待遇,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索质低”。例如,各种政府报告、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中提及农民工、外来人口都千篇一律地认定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综合索质较低”。实际上,很多时候,关于索质的论断,并非基于学历和职业,而是基于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谈到“索质”时,虽然余姚本地人自然而然地具有优越感,但外地人并不完全被动,很多时候,他们也站在自己的小传统立场上指责本地人“素质低”。
余姚——包括浙江和苏南——的男人有一个习以为常的陋行:随地小便。无论是弄堂里、树阴下、屋角边、草坪旁,不管人来人往,男人们内急之时,都可以公然行之。这一点,让外地人不可理喻,尤其一些女性,她们在社区内行走时碰到此景,便倍感难堪。
随地方便是中国农民的传统行为,但表现形态不尽相同。外来农民工因为居住的出租屋和社区内缺少卫生设施,所以公园、工地附近成了方便之处。而且,外来农民工就算在公园、工地附近的空地上方便——不管大便小便,但一定偷偷摸摸,通常是在夜间或早晨,而不会在大白天、众目噗睽之下进行。
过去几年,我们可以普遍看到,余姚农户的漂亮楼房旁大都有一只露天粪缸,村庄道路旁则有着十多只分成一排两排的露天粪缸(在笔者所到的苏南、浙江其他县市也是这样的)。这样的卫生设施,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中西部尽管不比浙江发达,但农村卫生没施是简易的茅房,而不是露天粪缸。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余姚农民家中开始使用抽水马桶。2003年前后余姚市动用行政力量在全市农村整治露天粪缸,但人的习惯并不能一下子革除,许多老百姓因此与村干部发生冲突。到现在,余姚一些农村仍有露天粪缸,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并不喜欢使用抽水马桶,而是习惯于蹲在露天粪缸上方便。
2008年5月,余姚北面的宁波杭州湾大桥建成通车之时,一些国内著名的网络媒体——大都是外省的——对余姚和宁波的男人进行了批评,有的说“国人素质亟待提高,竟有人在杭州湾大桥上小便”。又有一个学者——其文中配有“方便”的图片——则认为“杭州湾大桥检验的不仅仅是国民素质" [5]。
这些批评固然不无道理,但从中也体现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差异。随地方便,之于长三角的农村男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所有生长于斯的人都习以为常和见怪不怪。尽管这种行为已经不合现代时宜,但并不能简简单单地用“素质”来定性,用“习惯”来指称,会更确切一些。
上面所讲的冲突,是文化意义上的小传统冲突,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劳资冲突。这种文化小传统冲突可能会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纠缠,或者说,前者可以从后者身上产生出来,但它的本质性、独立性是不容忽略的。
提及冲突,我们长期以来要么以回避的态度视而不见,要么停留在极端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里。其实,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而冲突也并非都是对抗式的、负而效应的。
中国古代文化对社会冲突有着非常睿智的认识和解决方法。儒家对冲突给予包容和驾驭的态度,《论语》里表明了孔子的态度“君子和而不同”,《易经》里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则以辩证哲学的高度认识到对立面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如《老子》里说道“有无之相生也,高下之相形也,先后之相随也”,“反也者,道之动也”。现代西方社会学家科塞在其代表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中也着重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
事实证明,新老余姚人在小传统文化方面的冲突,是具有正功能、积极意义的,彼此从当初的误解、分歧与冲突,走向了包容、认同与融合,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交际工具,语言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所关涉到的是人(民族)的自我认同”。新老余姚人之间在语言上的冲突和误解,最终还是通过工具性支持,国家的政策导向,而实现了彼此的融合和认同。
(1)新余姚人讲余姚话。新老余姚人的语言冲突,既来自地域的优越感,又来自余姚本地人使用本地方言的便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新余姚人也慢慢适应了余姚的语言环境,并不同程度地学会了余姚方言。按照时间循序,新余姚人到余姚三年、五年尤其十年以后,就可以从一部分听懂到大部分或完全听懂余姚话,并渐渐学会讲余姚话。并且,居留余姚时间越长,对余姚话的理解程度、讲的熟练程度,也就越高。尤其是一些民工子女,他们从小生长在余姚,能讲一口地道的余姚话。起初余姚人很排斥普通话,但对会讲余姚话的新余姚人却感到新鲜和惊奇。为此,2007年6月,余姚市委统战部还举办了一场“新余姚人讲余姚话比赛”活动。
(2)普通话获得合法性。普通话当初受到排斥是地方社会转型前的本能反应,其获得合法性是社会转型成功后的需要。第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到现在20年时间里,新老余姚人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在公共领域、工作领域、私人领域形成直接的、长期的、本质的联系,这样,既强制性地逼使新余姚人放弃自己的方言,也同样逼使老余姚人学会新的语言工具——普通话,否则就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交往造成不便。第二,从公共领域看,国家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以宪法的名义推广普通话,但余姚的官员干部大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在工作中长期接触的干部、群众、企业主也大都是本地人,故没有使用普通话的必要。自90年代起,社会变迁下的人口流动,改变了余姚的语言环境,方言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外语、方言、普通话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地方官员干部,是否掌握外语,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会不会说普通话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再者,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强。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2007年《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出台。这样,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语言政策,既让余姚民众,也让余姚的官员干部开始承认了普通话的合法性。如今,在机关办公室里,余姚的官员干部还习惯于讲方言。但是,在较为正式的会议场合,哪怕是村级召开的会议上,余姚的官员干部都习惯于使用普通话,不管其标准程度如何。在宴席、聊天、会议等场合,哪怕只有一个新余姚人,如果这个新余姚人讲普通话,那么,所有余姚人马上讲起普通话。或者,双方一会儿讲普通话,一会儿讲余姚话,都非常自然。
余姚的饮食如今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一是余姚当地饮食。第二是西方饮食,以城区及乡镇上的“肯德基”、“麦当劳”、“咖啡馆”为标志。第三就是全国各地的饮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从饮食文化上,我们可以看见新老余姚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融合。
(1)新余姚人习惯了余姚饭菜。现在,新余姚人仍一如既往地怀念老家的饭菜,但他们也慢慢地习惯了余姚的饭菜。这种习惯,并不是完全的,而是说,新余姚人习惯了一部分余姚饭菜,对某一部分余姚饭菜仍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怀念也不是完全的,许多新余姚人回老家后也发觉有很多饭菜不太适应了。据一些安徽人说,他们回家之后,发觉家乡的菜肴过于油腻、味道太咸,这无疑是受到余姚的影响,因为余姚饭菜是很清淡的。2008年,笔者在网上与一个已经离开余姚的农民工交流时,他提到了余姚的一些饭菜,并表现了怀念之情。
(2)余姚人接受了辣椒。提到新老余姚人在饮食方面的融合,最主要还是体现在辣椒方面。第一,余姚本地人如今已不再对辣椒给予怀疑和指责,而开始承认这是一种合理的饮食方式。一位1990年代来余姚的安徽农民工说,以前他每次和余姚人吃饭,都要听到“侬安徽人欢喜吃辣的吧”之类的问话,现在听不到了。第二,有许多余姚本地人喜欢上了辣椒。大概2004年前后,新余姚人中间出现了许多个体户,其中较引人注意的当属遍布余姚城区和村镇的“川菜馆”。“川菜馆”以麻辣味而出名,适应所有外地人的口味。另外,市场也刺激了需求,越来越多的余姚本地人也开始涌向“川菜馆”,就像他们在90年代以新奇的心情涌向“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笔者所在的小路下村,就有两家“川菜馆”,小路下村农贸市场内一半以上的店面、摊位都是外地人所经营,其中也有两家专门卖川味的“猪头肉”。2009年9月,一家店主告诉笔者,每天来她们店里的顾客中,有20%是余姚当地人。另夕卜,自90年代进入余姚的西方饮食业也受到了这种地域小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在“肯德基”里也有“辣鸡翅”之类的食品。
农民工现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同质的铁板一块,而是发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在新余姚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个以知识、工作、财产为基础的精英群体,这必然会从质的方面——即“素质”——改变其群体形象。
我们前面从外在行为方面分析了新老余姚人的差异。现在,我们仍以行为——一种塑造外表形象的广义行为,来分析新老余姚人的融合。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划分为两种,一是精神上的不平等,一是生理上的不平等。关于农民工所经受的不平等待遇,学界从户籍制度以及所谓,,歧视,,层面分析得较多,对他们在生理层面所经受的不平等并未注意到。而中国文化里,恰恰一直存在着生理不平等的传统。孔子认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古代史籍中提及帝王将相的外表形象总是以最美丽的词语来刻画和描写。
由于历史文化、经济收入、体力职业等各种因索,农民工在外表形象上同其他阶层群体有着很大区别。在余姚,长期以来,新老余姚人一眼就可以从衣着外表上分辨出来,因为后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的衣服很破很脏,头发乱蓬蓬,背个大包小包,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出现在报纸和电视里的农民工的“标准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掌握舆论权力的主流群体对于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方式之一。
但是,现在——尤其2004年以后,新一代农民工的形象,跟父辈截然不同,他们的发型很时尚,服装也多姿多彩,举手投足都有了明星的派头和气质。因此,2008年宁波市还举办了“新宁波人选美大赛”。
像饮食一样,服装和外表打扮也是一种文化,当农村人和城里人、外地人和本地人,在服装衣着上日益趋同时,表明两者既在经济、职业方面,也在文化方面也走向了融合。
余英时的研究证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大传统,往往是由国家权力作背景,通过学校、寺庙、教师来传播的。而当代,从全国各地涌向余姚的小传统,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完全是基层民众自发传播的,但由于时间较长、人口数量较多,这种自发传播却起到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效果。余英时的研究又证明广,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具有本质联系,一方面,大传统必须流入民间,在基层民众中获得合法性,如儒学在汉代就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另一方面,小传统影响并上升为大传统,如《诗经》中许多诗作本是先秦时代的民间歌谣,经过儒家的整理加工而成为儒家经典。
余姚当代经验再次验证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余姚的各种小传统的文化冲突,不但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其一,在文化意义上,大众性的小传统文化已上升为精英性的大传统文化。余姚及浙江省近年来涌现的“打工文学”即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近年来,在余姚及浙江的报刊中,打工作者的文章占有了一定比例。有的打工作品在全市性文学征文大赛中获得第一的成绩。2007年《浙江日报》举力、“浙江省首届民工文学大赛”。2008年宁波《文学港》、《宁波晚报》等媒体举办“新宁波人征文”比赛。2009年余姚市举办“新老余姚人征文书画比赛”。2008年,在台州的安徽农民工李明亮获得“全国农民工诗歌大赛一等奖”,2009年他成为与浙江文学院签约的首个外来打工作家。凡此种种,都表明外来农民工已从经济性融入上升到文化性融入,从小传统上升到大传统,开始进入到地方的精神共同体[6]。
其二,在政治意义上,这种民间文化已从自发传播上升为官方施行的政策。从余姚、宁波及浙江其他地方政府近年的农民工政策来看,就显示了这种基层小传统对于官方大传统的影响。余姚和宁波从2006年起组织动员外来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至今,余姚已有188个村建立了由一半外地人、一半当地人组成的村级和谐联谊会,宁波市有三分之一的行政村(社区)建立了这样的融合型组织。地方政府在构建社会共同体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营造社会共同性。2008年,宁波镇海区实施“新镇海人意识教育”。2009年,余姚市组织举力、“新余姚人游余姚”活动。余姚及宁波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者如杜建海、王辉等人在其论著中或会议场合上,都明确提出要对外来农民工实施乡土文化教育。
其三,在地理意义上,这种地域性文化碰撞却发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它不但对于农民工输入地,对农民工输出地也同样存在影响。2009年6月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新疆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除了继续加强技能、知识、法律和汉语培训外,还将进一步培训接纳地区的风土民情、生活习惯、企业文化等知识信息”。2009年9月,重庆市南川区向余姚输出首批务工者,南川区政府开展就业前培训时,既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培训,还“介绍了余姚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当地的风俗人情,以帮助务工人员尽快适应新的环境”。2009年9月29日《宁波日报》报道,一位在宁波镇海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回到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石滩乡碾子咀村后,出资3.1万元,建造了一条长110米、宽1.5米,绘有介绍宁波镇海文明建设经验的“文明长廊”。
(作者单位: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季学原.姚江文化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4][美]科塞(Lewis Coser)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王辉.一代人的余姚体验).余姚市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征文
[6]王辉.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2009年民政部农村社区建设理论自选课题
注释
[1]费孝通晚年在《个体群体社会——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一文中,认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有着“见社会不见人”的缺憾。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4页。笔者引用费孝通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农民工研究,是因为,就学科而言,社会科学主要侧重于研究社会。但就问题而言,必须体现人文的方法和意义。
[2]2009年9月,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的工资即使比以前上升了50%,但仍然存在着招工难问题,这说明农民工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同时对文化、休闲、公民权利、知识劳动等需求也更加强烈。
[3]这是余姚官方公布的数据,由于技术及人口流动频繁的关系,地方政府很难确切地统计出外来人口的数量,只能以暂住证办理情况为依据,加上估算,而得出大概的数据。
[4]关于外来农民工与浙江县域经济、农村社区的关系,笔者于2009年上半年完成的一篇论文《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中进行了较为全而的分析。
[5]在百度上输入关键闻,便可看到许多网络媒体对此的报道。
[6]笔者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便关注和倡导“打工文学”,故对上述打工文学事件及打工作家都较为熟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