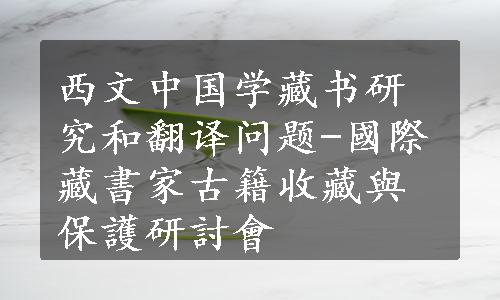
梁启超有名言曰:“今日天下,则必以译书爲强国第一要义,昭昭然也!”中文古籍收藏注重版本、校对(校勘、校雠)、批注、流通(刊印、影印);西文古籍收藏还增加了注重翻译,只藏不译,如藏天书,影响流通和使用。
国内外汉学专家、研究中西关係专业学者研究的课题、论文,超前业馀人士十到二十年。但是,专业人士也存在偏科现象,这有可能影响他们著作和成果的领先地位,目前从中国学著名典籍的译著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1.在汉学名著的翻译方面,专业机构院校回避难点,忽略版本问题
一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历史上可能有很多译本,包括西文中译,也包括中国经典和名著的西译。如《马可波罗遊记》,从1913年到1981年六十八年间,出了六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後所译《马可波罗遊记》较好。
西方汉学三大名著《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由於篇幅宏大,涉及面广博,翻译难度巨大。专业机构和院校则通常绕开难点,比如《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至今没有中译本。
中国学“金字塔尖”名著的翻译,过去二十年由有勇气的个人如何高济、耿昇等翻译出版,何高济毕业於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史研究,80年代移居巴西,生活工作二十多年。他翻译汉学名著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劄记》、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曾德昭著《大中国志》等数十部著作。可惜因版本选择不善,多用後期英文翻译本再转译,所以这些译著仅仅是历史过渡性、临时性的译本,最终将被原文直译本所取代。
以翻译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爲例,温家宝2009年访问西班牙期间作演讲,在回顾中国与西班牙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时曾说:“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此书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何高济译本,是转译自英文译本。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孙家垄教授译本,直接从西班牙原文译成中文。据说,原来的英文译本没有完全尊重原作者的内容和风格,甚至存在漏译和曲解,那麽用英译本转译,也就不如用西班牙本直译,尤其是序後面还有两首十四行诗,更是无法转译。
再以1615年金尼阁所著《利玛窦中国劄记》(又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爲例,这原本是利玛窦晚年用意大利语写的一本在中国传教经历的手稿,此份手稿由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在回欧洲的途中整理並译爲拉丁文,同时增写了有关传教史与利玛窦本人的一些内容。在1613—1614年间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翻译成拉丁文,161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初版,但事实上,金尼阁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国图、上图、罗氏藏书以及北大等主要公藏都未著录,就是在罗马主要图书馆也很少见(仅印500—1 000部),但德礼贤神父编注的《利玛窦全集》最重要,价值最高,是研究利玛窦的必备书籍。
《利玛窦中国劄记》中文译本有三种:(1)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何高济等译本;(2)1986年台北光启出版社与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传教史》刘俊馀、王玉川根据意大利文的译本;(3)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本。文铮译本耗时十馀年,並且是在国内外诸多汉学家和汉学机构的帮助下完成的。何译本是根据1953年英文译本的再版本转译的(1942年,英国学者加莱格尔〔L.J.Gallagher〕以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爲底本译出英文全译本,书名爲《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劄记(1583—1610)》〔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5-1610〕)。台湾译本也被学界所诟病,到目前爲止,文博士(我的朋友)的译本是最好的,但还是缺少利玛窦的信件翻译和德礼贤的诸多有价值的注释,离最完善的版本尚有差距。
再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18世纪欧洲汉学的“三大巨著”之一,是耶稣会出版时间延续最长的著作,从1702年第1卷,到1776年刊出第34卷,用了七十四年。其中16—26卷收载由中国寄来的信。张西平教授说:“(《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早期西方汉学三大名著,成了欧洲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圣经》。”
《耶稣会士书信集》法文版有五种主要版本,中文译本有2001年大象出版社耿昇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著名的还有日文译本,有1970—1974年《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矢沢利彦编译本。多年来,日本学者研究和翻译《耶稣会士书简集》下了很大功夫,遍访欧洲图书馆,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不过日本学者对於中国公、私藏西文古籍善本,却不屑一顾,未必恰当。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日译者的“解说”一文。还有周振鹤《〈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日译本略比》一文,批大象出版社的中译本,品质是相当差的,即使不与日译本作比较,也可以信手举出不少硬伤。矢泽先生所依据的底本是1780—1783年间出版的26卷本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巴黎新版。大象出版社的译本则是根据1819年的里昂十四卷本,显然中日译本所据版本不同。如果大象出版社翻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目的只是在讲故事,那麽翻译个大概也就算了,但显然这套书简集的中译本是作爲学术著作来出版的,那就只能以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要求它。(www.zuozong.com)
日本学者爲此书版本遍访欧洲各大图书馆,但对中国西文藏书怀有偏见,一是因爲20世纪70年代中国未有西文善本概念,但时至今日,也未见其对中国有考证记录。其实据目录,上图藏一部全本34卷32册(是否原版著录不详,待考),上图罗氏藏书存33卷(巴黎原版有再印本,缺1卷),国图藏32卷30册(是否原版著录不详,待考)。此部名著的翻译尚未达到顶峰,应该选择34卷法文一版爲底本,请专业译者、学者精心翻译,才有望纠正之前译本的错误,以还原原著的价值。
2.西文编目和出版的问题
国图、上图西文善本书目中,中国学题材古籍没有单独提出来编目,对於研究中国学这一新的学科有诸多不便,而中国台湾和欧美在中国学科图书专藏编目上,已经形成系统的成果。
本人近年关注有关西文汉学的书目超过400种,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第《中国书目》和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这两部书目,每部收书都接近或超过2万种。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应从书目入手。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讲国学书目如此,海外汉学、中国学也应如此。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讲的第一门课,就是高第《中国书目》这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学书目,傅斯年等人也非常重视这部书目。可是,国人接触西方文化较少,起步讲得太深,学生们大都听不懂。
高校藏书研究,如仅以院校自身爲研究单位,缺乏横向交流,不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徵求社会各界意见,在遇较大课题时闭门造车,容易发生缺漏。如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北大中文系所编辑《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是个时间跨度很大的书目,虽用时二十馀年,收录汉译西学书6 000馀种,出版後专业人士有異议。去年我尝试按《书目答问补注》形式作西学书目补注练习,一年时间补缺、补正、补注2 000馀条。我之尝试练习这项补注,是看到北大中文系杨忠教授在国图讨论会上发言的报道,他忧虑古籍整理非专业化现象,忧虑民间複製古籍出版物劣质。而我认爲北大中文系对社会的忧虑,应该从自身学术严谨性做起。也正是由於公藏出版物存在很多不精,造成私人出版更不精。公藏要是能做到许梿、董康的水准,还用担心私刻私印不精吗?
3.学子治学,西文书引经据典查原文资料困难的问题
鲁迅致台静农信上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爲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爲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现在不用说能像胡适、郑振鐸一样爲治学搜集孤本秘笈,就连鲁迅用的西文通行之本,学子也轻易浏览不到。由於西文中国学藏书资源有限(仅集中於几个大馆),在电子资讯时代可以花重金买入电子图文版,但相关部门出於利益考虑,捨不得公开浏览。国外有大量优秀免费的电子资料网站,量多质精,但多遭遮罩,无法使用。院校部分学者治学,找不到引经据典的原文,以大量转抄的二手资讯应付学术论文,错漏百出,此乃当今大国教育的怪相之一。
比如,前面提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问题,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依旧照搬。又如,维基百科里不少内容是二手和错录的(现在维基时而被封),如很多中国题材的动物、植物著录有误,而西学古籍裡早就辨析清楚。再如,徐光启在上海刊印的《农政全书》裡面有西学译本《泰西水法》,提到祖本,通常从《善本总目》到大院校近年新论文,千篇一律地只提平露堂即是唯一祖本,此话没错,但不够准确。我经初步核对,发现本书牌记有平露堂藏板的印本不止一种,说明平露堂刊本印刷过不止一次。再核对1975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以及网上有关图片资料,都不初印,台版影印书从序开始就是抄录本,而且没抄全,排列顺序也不对。因此,用平露堂藏板印刷的《农政全书》,到底哪种更接近初印,一是需要对比公藏约30部原书後,有可能排列出初印顺序;二是探究历史悬疑,可能揭开崇祯进呈本情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