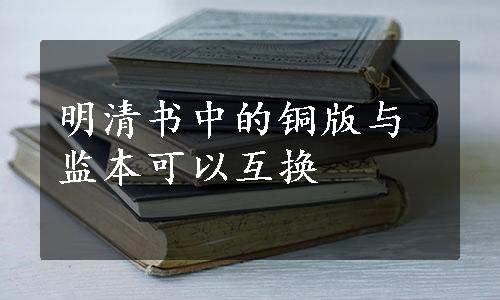
古时国子监的一个职责,是作爲国家出版机构,向社会提供经典书籍的标准文本“监本”。监本的特点是文字经过国家审定,没有错误,也不可更改,即所谓定本。可以肯定,明清出版业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即古代国子监是用铜版来印刷经典的。
清初人陆舜撰《陆吴州集》,开篇是一首《拟御製十三经序》,略云:
朕惟皇祖基命,用肇造我国家。及我太宗,仰承天庥,拓疆展土,奄有万邦。洪惟我幼冲人缵承丕绪……庶几考古定宪,师圣益愚,近法宪章,远通经术……则有十三经,爲易、诗、书、春秋、礼记以及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公羊、穀梁、孝经、尔雅……用特取所谓十三经者,寿之铜版,藏诸太学,以广爲颁行,俾人人务崇实学,湛乎经术……
陆舜生於明万曆四十五年(1617),康熙三年(1664)进士。此文用顺治帝甫登基时口气,当作於入清後不久。可见时人心目中的“太学”(国子监)刻书即爲“铜版”之书。
再来看看流传至今的那些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在中国,这些书不受重视,不在藏书家的收藏之列,但在国外图书馆,它们和其他中文书籍受到同等对待,更容易保存下来並得到详细著录。德国的两家图书馆即藏有数部清代举业书,明确将“铜版”指向“国子监本”。
又如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易经正文》,封面题“道光戊子新镌,铜板易经正文,振贤堂藏板”,卷端题“监本易经全文卷之一”(图3)。属同一套书的还有《诗经正文》,也是封面题“铜板”,卷端题“监本”(图4)。这两部书封面的“铜板”相当於卷端的“监本”,二词可以互换,爲同义词。
图3
图3
图3
图4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4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4(www.zuozong.com)
再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四书章句》,封面题“甲戌年新镌,铜板四书监本,五云楼梓”(图5左),将“铜板”视爲“监本”的出版形态。“甲戌”上未署年号,该图书馆著录爲嘉庆十九年,当有所据。
又如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正文》,封面题“审音辨画校订无讹,裡如堂四书正文”,每卷卷端题名不一,如《论语》题“振贤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图5右),《孟子》题“□□□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全文”,二、三两行则题“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也是将“铜板”视爲国子监本的出版形态(图4左)。
按此《四书正文》的祖本,当爲一个明末刻本。这从卷端的“监韻”、“经魁” 等明代惯用语,以及将“校正”写作“较正”等可以看得出来。校订者当爲广东顺德人陈豸,万曆十九年(1591)举人,历任槁城、福州教谕,福州海防同知。
德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四书正文》,只存《论语》两册,上册卷端题“裡如堂遵依国子监铜板原本四书正文;经魁陈豸廊寰甫校”,下册卷端题“省城醉经楼较正监韻分章分节四书正文”,两册字体、纸张均不相同,实爲配本。由此可见当时此类书标榜“铜版”的风气之盛。
图5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图5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图5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一成不变,使爲科举服务的出版业也陷入停滞,举业用书辗转翻刻,明人编的书到清末还在使用,号称“铜版”、“监本”却错讹不堪,这固然是读书人的悲哀,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表明“铜版”真实含义的难得资料。
这也说明了爲何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时,也没有人对看似重要的“铜版九经”进行考证,因爲那时的人都读着“铜版”书,知道“铜版”的真实含义。只是清末以後,去古愈远,其本义纔渐渐迷失。
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爲一谈,但並不表明这些“铜版”书真的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麽关係。实际上,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係,它们只是书坊浮誇的广告语。在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不被“监本”二字所误导。
至此,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明至清,“铜版(铜板)”一词有纯语言范畴的“确定”、“不可更改”之义;二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印有“铜版(铜板)”字样的科举用书,並非使用铜质印版。出版业标榜的“铜版”书即“国子监原本”,取其“国家定本”、“正确无误”之义。中国印刷史上的“铜版”疑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