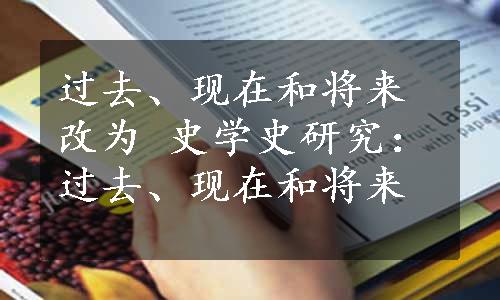
艾都拉多·托塔奥罗
翻译的概念在欧洲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突出位置。“翻译”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意大利语的tradurre,法语的traduire,德语的übersetzen和俄语的perivestì,后两者并不明显源自拉丁词根),都带有一种动态传递的意思: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并不必然但经常需要的是将某些信息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必然而且总是需要的则是将信息从一个时代传递给另一个时代,从一种文化传递给另一种文化,以及在带着其全部隐含假设的前提下,从一种政治体系传递给另一种政治体系。确保传递富有意义一直是历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远远早于人类学家对我们的提醒。这种意义上的传递或翻译与历史写作的传播功能具有密切而内在的相关性:历史学家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研究或写作:他们要让历史向公众开放,即他们要把他们之所见(语源学原本意义上的历史)翻译成一种知识,一种由于在人们之间传递而被多人共享的知识。哈托格(Hartog)让我们记起历史真正的“出生证”,一幅精彩动人的场景,当费阿刻斯的歌手(Pheacian singer)讲述特洛伊被困的故事的时候,尤利西斯哭了,因为当他在听别人把自己的事迹当成故事来讲述的时候,主体的原初身份被破碎了。阿多而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其《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 rung)中虽然没有提及这一段,但他们在谈到尤利西斯和食忘忧草的人(lotus-eater),以及尤利西斯拒绝回到那永恒存在的自然状态的时候,谈的是同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能够叙述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主张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观念。古代晚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所发展出的许多史学特征在20世纪的历史写作中仍然十分流行。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所描述的从以史为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时代到以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为主导的现时代的转变是这一演进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一转变覆盖了整个18世纪,就此而言18 世纪也是现代性的奠基。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日益不安地反思着历史知识和传统时间框架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在18世纪初发现,发展的观念让人们意识到了人们所处的时间维度。但是要把关于人类过去的传统认识翻译进一种以发展为基础并被发展所支配的历史视角中相当困难,有时还极其复杂。以史为师的史观中最关键的根据圣经叙事而来的预设是短小年代纪(short chronology):除非历史有一个人类的尺度并且表现出由上帝确保的深层连贯性,人们才能真正从先辈的错误中学习或者效法他们的功绩。
众所周知,圣经作为真实和正确的叙事的可靠性在18世纪受到了日益增长的质疑,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通常否认它作为史料的可信性。人类始祖既非被造于基督之前4229年,也非4196、4052、3950年,这一点在1750年得到默认。与此并行的是当时认为在非常根本的意义上古典的古代是历史经验的一部分。过去的价值在于为现在提供启示和参照,当时仍有这样的看法。18世纪的历史学家对于以史为师传统的短小年代纪和与过去的连贯性两类范畴都难以适应。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8世纪历史学家的不安体现在吉本(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一书中。在这部著作中,由圣经和教会传统提供的时间框架不断遭到大胆的挑战(还有什么比吉本提到许多民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状态能更好的否弃基督教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的有效性呢?)。很明显,吉本认识到历史在经历发展,而通过对过去更加完整,更加仔细和理性的研究,人类的这种进步就会得到确认。在此意义上,吉本属于并且可以被理解成以历史真实性为中心的现时代的一分子。然而,吉本却又把公元后两三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政府视为完美的典范(吉本在他的赞词中可能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但这不是主要的。在该书著名的38章的附录中,吉本否认了未来东方蛮族将入侵欧洲并且使之从4—6世纪的破败中恢复过来的可能:只有他在过去和自己的现实之间建立了某种一致性,吉本的这种观点才有可能。吉本想被视为现代塔西陀(Tacitus),这是20世纪末期任何明智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声称的。和吉本同时代的很多德国人则持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时间观:比如伽特勒(Gatterer)更为一致地把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事件、人物、国家在时空中全面伸展交织成的整体:伽特勒的时间框架来自圣经,亚当和摩西在一定意义上仍与他同处一个时代。根本不相信圣经的史料价值的施洛塞尔(Schlözer)也不能使自己完全脱离传统的历史时间观念。另一方面,伽特勒和施洛塞尔与他们在哥廷根大学的同事又有很大贡献,他们所推动的学问侵蚀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使以史为师的范式不再合乎时宜。
法国大革命是上述转变被阻断的关键一步(这是我要强调的),无论这转变令人忐忑不安还是欢欣鼓舞: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唤醒了变化,或因为它要为新的时间框架负责,或者创造了进步的观念,而是因为它使得一种新的时间框架的明确化成为可能。新的时间框架在18世纪90年代被陆续提出来:必须说明的是,这最早的尝试很多。虽然一种无人格的、自为的历史进步观念普遍而基本,当然并非没有引起争论(在此必须提到布克哈特[Burckhardt]!),但远早于1989年的19世纪和20世纪,过去的连贯性看来就已经被撕裂多次了。
关于历史过去的普遍的观点的重要性已被忽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始强力反弹。
20世纪最具有世界主义的历史学家之一,意大利人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两篇极好的短文,可以作为分析世界史写作的现状及其所受批评的起点。在其中一篇名为《重访历史主义》(Historicism revisited)[1]的文章中,莫米里亚诺指出了19世纪历史主义中的一个根本歧义:
历史主义由于暗含了相对主义的危险因而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学说。它倾向于破坏历史学家对自己的信心。确实,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当中,被视为历史主义之父的兰克(Ranke)生活得十分惬意。似乎他能毫无困难的把通过翻阅档案而揭露出的个体事实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进程中。如果上帝在个别事实中,我们为什么还关注普遍史?如果上帝不在个别事实中,他又如何存在于普遍历史中?[2]
在另一篇名为《一种关于观念史的彼得蒙特观点》(A Piedmontes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文章中,莫米里亚诺对比了意大利和欧洲、美国对历史写作兴趣的增长,有力地强调,“如果历史学家要在其社会中充当一个负责任的角色而不是观点的操纵者,就不可回避真实性问题”[3]。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文章本身却明确地要将对一个小的地区内极其地方性的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和20 世纪的大规模事件没什么关系——和作者对全世界错综复杂的思想史提出整体看法的野心,以及对历史写作对于真实性问题的贡献做出评估综合起来。彼得蒙特(Piedmont)实际上指的是意大利北部,是莫米里亚诺的出生地。他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世俗化了的犹太人,在成为罗马大学非常年轻的古代史教授之前,他在本地的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古代史。1939年,因为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通过的歧视性的反犹太法律,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并先在英国,后来在美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成为古代史和史学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关于历史难题和事件的整体观点,并不屈不挠地谴责对人类过去的狭隘观点:怪不得他比意大利更合适伦敦和芝加哥的环境。
他的《陌生的智慧》(Alien Wisdom)一书出版于1975年。该书证明,即使像古代史这样其现代形式有着沉重的可追溯到14和15世纪的阐释传统,有着严格的文献学惯例,只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也总能告诉我们一些新东西。莫米里亚诺在书中强调公元前数世纪地中海地区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以及相互的漠视,写出了一段精彩的世界史:
孔子(Confucius),佛(Buddha),查拉图斯特拉(Zoroaster),以赛亚(Isaiah),赫拉克里特(Eraclitus),埃斯库罗斯(Eschilus):这个列表很可能会震惊我的祖父和他那代人。现在它有了一种象征我们历史视角发生变化的意味。或多或少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处理那些一度看来十分遥远的文化,并且从中发现一些共性。[4]
早在二战结束时写给意大利史学家费德里科·查博德(Federico Chabod)的一封信中,莫米里亚诺就已经表达了这种关注,他写到普遍史:
必须被设想为过去那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的历史:如你所说的,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科学、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等。编年顺序的困难可能以这种方式克服,在每一部分(希腊,罗马,中世纪等等)插入一篇导言,取一些类似“希腊(罗马,中世纪)社会的地理和政治背景”的名字,这些文章按年代顺序描绘出政治以及地理的变化。但你如何解决下面的问题?在我看来,任何普遍史都既包含对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文明的民族的关键特征的分析,也包含对其他民族的突出特征的分析。对于后者来说,正是由于我们文明的存在,使得我们能从他们当中辨识出共同人性。希腊罗马让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把我们文明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传递给我们,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感兴趣则是因为作为人类存在(“感谢我们的共同人性[grazie alla comune umanità]),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的价值。很明显,认识到人性的价值是文明统一的起点:是起点而非终结。在此意义上,普遍史是对历史的普遍化的一种贡献。现在,你打算如何结合普遍史的两个方面:即同时既是关于我们文明的历史也是关于我们人性的历史?在两个问题上,你必定会同意我:1.这样的历史应该以普遍史的观念的历史为先导,以弄清目标……;2.针对每一结论的最重要资料必须给出。请让我强调这第二点的重要性,因为不负责任的历史作品的流行很危险,你根本无从知道他们是如何立论的。我们有忘记17、18世纪的智者留给我们的遗训的危险:关注那些资料确认的事实。那些与普遍史相关的资料当然不只是与公元465年的雅典历史相关的资料。[5]
莫米里亚诺为什么在其世界观中着力强调欧洲因素?因为不管过去还是将来,讨论日益增长的对历史的全球特征的认识都不能隐瞒两个事实,这两个事实也正是我这篇文章的起点:1)一般而言,在解释学意义上我们都具有特定的视角,这是我们认识自身、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过去的特殊前提。确定视角是撰写我们所知的历史的先决条件;2)我们看到一种走向本地认同的深层潮流在世界各地产生,交织着全球化在军事、宗教、文化和商业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带来的地区和文化间的相互依存。我认为这两点至关重要。如我们所见,莫米里亚诺毕竟是一位20世纪早期的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他深深确信,历史科学必然和真理问题相关:当然是以复杂有时甚至含混的方式。然而对他来说,在任何历史研究中最核心的仍然是对真实的过去事物的纯粹的诉求。他也确信,史学史表明历史学家发展赋予资料意义策略的各种方式,职业历史学家的整个认识努力蕴含着一种重要意义,相比阅读小说或听音乐,这是一种不同的并且可能是更深刻的重要意义。
有必要强调的是,莫米里亚诺的杰作《陌生的智慧》对地中海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包括某些关键的历史角色错过互动机会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相反,互动的概念,思想的流通和文化的传递,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获得了广泛得多的接受。[6]
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学家通常都把历史考虑成民族史。应该说民族史意味着民族特性合目的性的进步,这种进步通过永恒民族特征的具体化也就是历史来实现,进步的保证在于国家体制中的军事和财政权力的集中并能够运用一套不断增长的对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干预的权力。自从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民族运动兴起以来,历史写作就主要集中于那些强调民族共同体内部同质性的现象上(其实更经常的是想象的同质性),而非强调历史经验中的多样性内容以及文化、群体的汇聚和融合的不同方式。多样性是不可信的,是一种缺陷。
这样一来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就与启蒙时代的人们明显区分开来,后者对非欧文明导致的变化很敏感,并且欢迎和渴望找到关于人性多样的证据。这种敏感和上层阶级日常生活中对非欧思想和物品的经验相一致。正是这种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背离造成了独特的欧洲中心论和对普遍史事实上的种族主义阐释,并把西欧的历史等同于人类的历史,普遍史只是将非欧文化和身份纳入欧洲进步的神圣步伐。
显而易见的政治事件已经表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具有非常有限的解释力,种族主义者的史观成了集体屠杀的蓝图。普遍史已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观念,这种世界史明确、首要地处理不同层面上从经济和贸易到移民到疾病的传播到流行文化形式的扩展等互动过程。[7]随着研究和叙事的重点转向考察人类共同体之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联系,世界史集中研究被传统普遍史写作所忽视的一定长时期的变化。
世界史并非没有经受挑战,这个学科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发展状况仍然存在许多可争议的地方。在受后现代方法尤其是后殖民及下层研究影响的理论探讨中,对非欧历史和世界史研究本身中间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取向的直接拒绝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很明显,就世界史而言,作为后殖民主义攻击的后果,它已经被以一种新颖和有创造性的方式深深地改变了。至少在表面上或部分如此,大多数史学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文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后现代居民。亨廷顿近来作品中关于文明的实质主义观点,大而论之预见人类未来的发展规律,实具有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图不顾任何正直的学术标准。[8]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都受这样一种观点的影响,就是说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复原过去,而是重构过去。我们都意识到,语言(尤其是历史学家的语言)大体上反映文化中存在的权力关系,而对语言的反独裁主义运用十分必要。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这样塑造我们关于过去的理解,能够导向也确实已经导向一些严重的神秘化,并且已经造成一种与我们的知觉相悖的虚假的和线性的时间性。在我们的一般知觉中,时间中存在缺口、断裂,和历史写作应该试图缝合的割断。
我们都对经典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很警惕,对文本的污损及杂烩比不久的过去甚至更为敏感。现在关于经典概念争议之外作为写作媒体的书写本身也受到攻击。根据维维安·索布恰克(Vivian Sobchak)的说法,电影已经获得了一种叠写(palympsestic)特征,这种特征实际上构造了我们关于过去的理解,正如中世纪教堂中的绘画、雕塑和雕刻作品启发历史意识一样。[9]许多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都从福柯的观点中找到灵感,说历史写作在过去庆祝了中产阶级主体的胜利,现在是到了解构它以让那些在经典著作中被抹掉的边缘人群“开口说话”的时候了。从这种认识和道德的立场中底层史和女性主义的研究确实取得它们存在的理由。
在许多与我们理解世界史相关的场合中,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已远远超出对研究主题和描述策略进行更新的要求,开始质疑历史写作的基本假设。对传统方法的挑战由于常有启发和洞见往往能引起注意。因此比较奇怪的是,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在世界历史中漫游》中写道,“作为一门新的学问,世界史相对缺乏争论。”[10]恰恰相反,很多人已经表达了对世界史观念本身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那些讲世界一体化带来的问题的历史学家。
我将首先以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作为这类批评者中尤其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些批评者在美国和亚洲国家都有,他们持一种激进的立场,认为不仅需要考虑社会实在和语言在我们观念中的转变的另一种世界史,而且需要另一种历史。这一立场不仅与规模有限的史学家群体也与普通大众有关,因此值得考察。根据德里克的说法,考虑到世界史的涉及范围以及其边界的无限性,对资料的选择和解释在世界史当中并不重要,因而世界史写作就是构造历史。所以,像布莱特(Bright)和盖伊尔(Geyer)曾经声称的那样,“历史学家不再必须创造一个世界才能研究世界史”[11],就是错误的。世界史学者所研究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胜利,本身就是对那些认为存在其他视角的批判意识的否弃。由于世界史将时间置于优先于空间的位置,它一定要清除所有的地方性时间。由于它站在获胜者一边,它也一定要清除地方性逻辑,从而成为关于世界空间、时间以及权力关系按照欧洲中心论组织出来的东西。世界史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巨量积累的最终产物,而这个世界始于欧洲,以后则是作为欧洲人散居地的北美对其余世界的征服。在此,世界史真正的核心就是欧洲中心论,即使在经受过挑战并进行了修正以后,其范畴也仍然有内在的缺陷。拿阿里夫的话来说,“虽然其声称要达到比以往更公正的理解,但大家仍有争议,当前的世界史学或全球史学在对世界的覆盖上并不比它声称为其灵感和合法性来源的全球化本身更广泛。”[12]对欧洲中心目的论的任何批判由此都是欺骗性的:和科学及发展主义一样,历史本身就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表达。印度心理学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中写道,历史意识“一旦输出到非现代世界,它就不仅倾向于使那些关于过去具有开放的过去观念或者依赖神话、传说、史诗来刻画文化自我的文化中的过去绝对化,同时也使历史的世界观点与我们时代中新形式的暴力、压迫和恶魔崇拜串通一气,并使文明、文化和民族的界限僵化”[13]。
维内·莱尔(Vinay Lal)近来以相似的论调指出,世界史“具有所有‘文化灭绝’,政治去权和破坏知识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多样性的潜在可能”[14]。印度教的印度和“它对作为一种知识的历史的拒绝”表明一种与无书写的历史相一致的认识论的存在,以及事实上它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对历史的拒绝是在现实中生存的一种方式[15]。莱尔认可如下观点,“历史是奴役,这在甘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真正的甘地,而不是那个力图把印度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倒霉同名者——正是这个观点从原则上解释了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史学传统。”[16]“历史是新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教条和征服的模式,它比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受批评的科学更加持续也更全面……放弃历史大概是我们所持唯一的异端,因为这种挑战正是对在今天已成为对人类最有效和最沉重的压迫方式的知识范畴的挑战。”[17]
德里克和莱尔的观点虽然看起来极端但并不孤立。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其《世界史界外的历史》(History at the Limits of World History)表达了类似的关注,他把英国(最终是欧洲)史学在印度的强硬植入和这种史学的贫乏与印度关于深沉而普遍的历史所具有的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观念进行了对比,为了恢复那卑微和寻常事务的历史性(historicality),后者可以像用文学的方式重新看待生活。[18]
这些严肃的指责应该在认识论层面和道德层面上得到认真对待。在此我愿意提出两点以挑战那些对世界史的激进攻击论调。第一点是关于世界史本身的意识形态特征。欧洲中心论取向已成为欧洲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并且成为为各种罪行进行开脱的工具之一。的确,无论经过怎样的世俗化,它发源于基督教关于历史是上帝意图的实现的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对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的批判是从欧洲文化本身中产生的,它远早于也更激烈于殖民地文化中产生的批判,并且与对待人、社会和自然界的世俗化取向并发。这当然不是给欧洲历史文化以道德的优先地位,而是证明了毒药和解毒剂可能共存于同一文化传统中,至少是潜在的。[19]迪皮士·查克拉巴尔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将欧洲外省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表达出类似的态度,他在其分析的开端开宗明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都在本质上是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遗产继承人,而且这一遗产“现在是全球的了”。[20]
对所有可能的欧洲罪行的批判和对矫正他们的请求都很可能被融入到一种语言中,而且根据既定的章程,严格忠实于欧洲启蒙运动首次设想出的关于世界历史的普遍主义取向。我们都在此遗产当中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想遗产既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视角也意味着一种政治改革的计划,它必定会生发出方法的多样性。(www.zuozong.com)
世界史的写作并不例外。从斯坦福大学一队意大利基因科学家做出的关于人类在各大陆的历时分布地图《人类基因的历史学和地理学》(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到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rnández-Armesto)的《千僖年》(Millenium),再到更新的麦克内尔父子的《人的网络:鸟瞰人类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近来的世界史虽然从许多方面看仍然不够,还是表明作为仍然要按“传统的”方式来叙述人类在时空中的发展的世界史,实际上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书写,而无论历史学家本人有什么样的偏见,他们都在实践各种不同的计划并具有不同的叙述、认识技巧和专门知识。[21]全球化确实在不断地激发历史学家展开对世界历史的反思和研究,但很难相信所有不同的世界史都能被包含到同一种立场中。正如莫米里亚诺可能会说的,彼得蒙特的观点具有其独特性,尽管有反对的异议,它同样有权利得到表达和得到科学共同体的严肃对待,只要其遵守公认的规则。史学的诸文化已经或被假定为已经放弃认为自己是唯一能设想集体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信念。这种潜在地存在于各种史学文化中——包括欧洲的史学文化——的自我反思不能被忽视。
第二点是关于历史写作和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的合法性的问题。寻求一种源于资料、能被证实的叙事是任何历史作品的前提。一些方法论假设虽然不断陷于争论和重新定义,仍构成历史话语的公共场所,不管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是指责这些方法论假设不完整不合法的外行都可以进入。牛津历史学家奥斯文·默里(Oswyn Murray)高明地指出,历史是城邦的神话。这一定义既没有将历史在我们经验中的重要性绝对化,也没有质疑其合法性,而是强调了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因素为问题提供假如不是确实可靠也可能如此的答案,而且他承认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作为对目前日益陈腐的民族史一种有吸引力实际上也可行的替代,世界史写作在此争论中尤其有意义。它还将成为一种试金石,判断对历史写作有根本认识论意义的史料选择和使用是否恰当。最后,抛开对这种观点的责难,世界史将为上述不断增长的相互联系的进程提供理性批判的机会,并定义它倾向于重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认同。
(汪 凯 王献华译)
(2008年第1期)
[1]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重访历史主义》(1974年),见莫米里亚诺《古典与古代社会史六论》(Ses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历史与人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I卷,第23—32页。
[2]莫米里亚诺:《古典与古代社会史六论》,第25页。
[3]莫米里亚诺:《古典与古代社会史六论》,第335页。
[4]莫米里亚诺:《陌生的智慧:希腊化的限度》(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57页。
[5]《费德里科·查博德档案》(Federico Chabod Papers),现代与当代史研究中心(Istituto Centrale per la Stori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罗马。
[6]《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G.霍普金斯(A.G.Hopkins)主编,伦敦2002年版。
[7]卢茨·拉斐尔(Lutz Raphael):《极端年代的历史学:理论、方法、倾向,1900年至今》(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Zeitalter der Extreme.Theorien,Methoden,Tendenzen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贝克2003年版,第196—214页。
[8]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塔奇斯通,1997年版。
[9]维维安·索布恰克:《显眼的流苏:变化的图像与历史意识》(The Insistent Fringe:Moving Images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36,no.4(1997),第4—20页。
[10]帕特里克·曼宁:《在世界历史中漫游:历史学家创造全球性过去》(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2003年版,第255页。
[11]C·布赖特和米克尔·盖伊尔:《全球史与二十世纪的全球一体性》(Globalgeschichte und die Einheit der Welt im 20.Jahrhundert),《比较》(Comparativ),4,no.5(1994),第13—45页。
[12]阿里夫·德里克:《混淆隐喻,世界的创造:世界史为什么?》(Confounding Metaphors,Inventions of the World:What is World History For?),见《书写世界历史:1800年—2000年》(Writing World History 1800—2000),本笃·司徒赫特(Benedikt Stuchtey)和艾克哈德·福克斯(Eckhardt Fuchs)主编,伦敦德国史中心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13]阿希斯·南迪:《历史中被遗忘的对偶》(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34,no.2(1975),第44页。
[14]维内·莱尔:《将西方外省化:印度史视野中的世界史》(Provincializing the West:World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an History),见《书写世界历史》,第289页。
[15]莱尔(Lal):《非历史性之历史》(The History of Ahistoricity),见莱尔《历史的历史:现代印度的政治与学术》(The History of History: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in Modern India),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6]莱尔(Lal):《非历史性之历史》(The History of Ahistoricity),第60页。
[17]莱尔(Lal):《非历史性之历史》(The History of Ahistoricity),第67页。
[18]拉纳吉特·古哈:《世界史界外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对这个悖论颇有见识的一个讨论可见卡罗·金茨伯格(Carlo Ginzburg):《历史、修辞和证据》(History,Rhetoric,and Proof),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迪皮士·査克拉巴尔蒂:《将欧洲外省化:后殖民主义思想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 Europe:Pa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1]路易吉·L·卡瓦利–斯佛査(Luigi L.Cavalli-Sforza),阿伯托·皮阿查(Alberto Piazza),帕沃洛·门诺奇(Paolo Menozzi):《人类基因的历史学和地理学》(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千僖年》(Millenium),班顿出版社1995年版;约翰·R·麦克内尔和威廉·H·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人的网络:鸟瞰人类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诺顿2003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