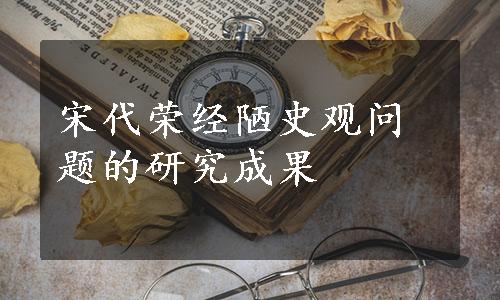
汉代经史分离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经与史都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但是,这种学科的分离发展,却并不表示经史之间因缘关系的割断或结束。由于经籍本身具有史料与史学价值,经学在汉代兴起以后又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而对各门学术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因此它对汉代以后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史学的解读与论证,史学是经学赖以发展的主要凭借。也正因此,人们在讨论汉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史时,经史关系总是成为他们永恒的话题。人们喜欢以经史并论,探讨它们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比较它们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的高低。
从经史尊卑角度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出现尊经卑史的现象当自宋代开始。清代考史家钱大昕堪为此论代表人物,他在为赵翼《廿二史劄记》所作的序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荣经陋史”观念始于宋儒的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史上很有影响、颇为流行的说法。钱大昕通过对经史关系的历史考察,认为经史之间“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佑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在这段话中,钱大昕以目录学为视角,认为从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后,经史开始分途,我们认为这与经史之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分离情况不相符合。同时他又认为,无论是经史未分之际还是经史已分以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听到过“陋史而荣经”这样的说法,直到宋儒王安石废除汉唐注疏之学,倡导义理新学,直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开始贬损史学;后来的道学人士大力提倡心性之学,而当心门弟子读史玩物丧志,于是有了“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训诫;而那些空疏浅薄者们更是以道学诸儒的训诫为托词,只说经而不治史,宋代“荣经陋史”的风气由此兴起。我们认为,钱大昕提出“经精史粗”、“经正史杂”之“荣经陋史”之风是随着宋代王安石新学和理学的兴起而开始出现的,说明他看到了中国学术史上经史观念在宋代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过,钱大昕以“荣经陋史”来概说宋代的经史之学则未免失之偏颇。众所周知,宋代文风昌盛,学术发达,学派众多,仅从经史之学而言,经学由理学的兴起而盛;同样,其史学的发达程度在中国古代也是空前绝后的。与王安石义理新学、二程理学同时并世的有司马光史学;与朱熹理学同时的有袁枢的史学,有以吕祖谦、程亮、叶适为代表的提倡经世的浙东史学,有蜀中二李(李焘、李心传)史学(其中李心传稍晚于诸贤),这些都是在中国史学史上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史家与学派。也许有人会认为,钱氏此说主要是针对宋代义理之学的经史观念而言的。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如果钱氏此说只是反映了宋代义理之学的一种普遍的荣经风气的话,那么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宋代义理之学都是“荣经”而“陋史”的,这一提法是否全面、准确,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宋代义理之学的代表学派无疑要数程朱理学,透过他们的经史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宋代义理之学经史观念的整体把握。二程(颢、颐)的经史观是通过其理学思想而得以阐发的。作为宋代义理之学的重要发展时期,二程理学以“天理”为其最高范畴。二程明确认为,“天下只有一理”[8],“理”是唯一的绝对,是物质世界之外的永恒的存在;同时理又是万物的本源,支配着万物,万物的变化都是天理的体现。与这种天下绝对之理相对应,万物又各有情形,各有其理,这叫作“理一分殊”。人们从万物具体的理,去推究“天下一理”之“理”。从这种天理观出发,二程一方面从求理的角度肯定史学的作用,认为要识“理”,识得历史治乱兴衰之理,就必须要“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9]。另一方面,二程又认为经书是教人道理的,必须先通过读经识得道理,然后才能读史。二程说:“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10]又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得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11]《上蔡先生语录》卷之中记载弟子谢良佐“记闻甚博”、“举史文成诵”,程颢却批评他是“玩物丧志”,意思是说他只知道“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在二程的理学思想中,以经为本、经先史后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www.zuozong.com)
南宋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理学思想,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宋代义理之学体系的建立者。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朱熹也承继了二程的先经后史的经史观。朱熹从万物一理、理一分殊的角度肯定古今历史与事物中存在着天理,要想明理,就必须要读书、读史,朱熹说:“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故,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12]但是,朱熹又明确指出,对于明理而言,经相对于史更为重要。更加强调读经对于明理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是经书全是天理,而史书则不竟然。朱熹说:“《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13]既然史书是三代以下文字,并非全是天理,人们读书明理,就必须要以经为本、先经后史。二是既然史书并非全是天理,如果不以经为本、先经后史,就容易为史所坏。他批评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说:“伯恭(吕祖谦字)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14]朱熹强调要站在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学习历史,才能做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15]因此,他一再指出:“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16]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于二程,朱熹理学更加强调“格物致知”的穷理功夫,而史学正是这种为“格物致知”而应该从事并且能够从中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在史学上下的气力更大,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从上所述可知,作为宋代义理之学的代表,程朱理学主张先经后史、以经为本的经史观念,表现出了明显的重经、崇经、荣经的思想倾向;而这种经史观念的哲学基础,则是其万物一理、理一分殊、理在事先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看来,“天下只有一理”,理在事先,而经学是理,史学是事,故而明理必须崇经、荣经,经先史后。正是由于程朱理学大力宣扬以经为本、先经后史的经史观,这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此后经学风气的兴盛,我们从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内容上唐人考诗赋而宋代易之以经义的变化也可看出这种风气的转变情况。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程朱理学荣经是否就陋史?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程朱理学宣扬以经为本、经先史后是实,但这并不等于就是轻视史学。程朱理学还有一个重要哲学思想是宣扬理在事中、格物穷理,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史事之中有历史兴衰之理,明理既离不开“经训”,同样也离不开“史册”,所以朱熹一再向人申明,他叫人读经并不等于不要人去读史,他说:“昨日有人问看史之法,熹告以当且治经,求圣贤修己治人之要,然后可以及此,想见传闻又说不教人看史矣。”[17]朱熹本人既是理学家,也是史学家,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就是他重视史学的一个最好注脚。[18]由此得出结论,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义理之学的以经为本、先经后史的经史观念,由于程朱理学的特殊地位,对于宋代以后荣经轻史之风的兴起无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至于宋学末流则更是只知空谈性命道理。但是,就程朱理学本身的经史观念而言,说他们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