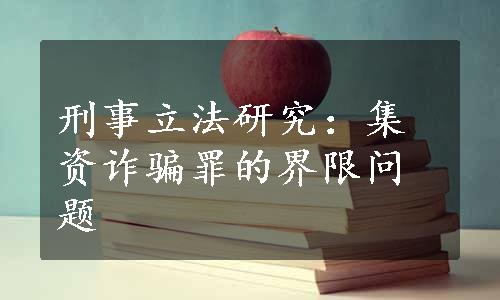
集资诈骗罪的界限问题主要体现在罪与非罪以及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分上。
(一)集资诈骗罪罪与非罪问题
集资诈骗罪是数额犯和情节犯,对于骗取数额较小资金,且情节较轻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判断集资诈骗罪罪与非罪的问题,最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本节前面部分已经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详细阐述,本部分主要结合司法判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案例】庞某被指控涉嫌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被改判无罪案[147]
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南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庞某犯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作出庞某犯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宣判后,庞某不服,提出上诉。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南江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再次作出有罪刑事判决,宣判后,庞某提起上诉,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审判程序违法裁定发回重审。南江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再次作出有罪判决,宣判后,南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确有错误提起抗诉,庞某认为其不构成犯罪提起上诉。
原判认定,被告人庞某在分别与被害人周某1、谭某、张某3业务往来过程中,采取先付款再发货的方式收取货款,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向被害人足额发货,分别向3人写下欠条或借条,并承诺支付利息,案发前未还三人欠款合计为149.79万元。2001年至2007年,被告人庞某分别以代理“小角楼”酒和开办抱国醇酒业缺钱为由,以给付1~5分利息为诱饵,在赵某2等21人处非法收取人民币223.9924万元拒不退还。原判认为,被告人庞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非法收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拒不返还且逃匿,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庞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未返还,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庞某上诉称,对本案涉及的所立条据的金额无异议,最终的金额应以实际还款或以酒抵账的金额为准。我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无非法收取他人货款和借款的故意,也无逃匿,其不构成诈骗罪,请求改判无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借款、欠款是事实,但没有占为己有、拒不归还的意图,主、客观均没有犯罪的故意,有争议的金额不应纳入定案范围,庞某外出并非逃匿。请求判决庞某无罪。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针对合同诈骗罪指控,原公诉机关仅因庞某欠下周某1、谭某、张某3大额欠款及欠据,指控庞某只履行合同极少部分证据不充分。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害人周某1等人向庞某支付足额购酒款后,庞某不足额发货,庞某辩称是平昌小角楼酒类销售公司对酒调价让其在经营中高进低出产生逆向价差致其亏损。认定庞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欺诈行为,拒不退还购酒款的证据不充分;另针对原公诉机关指控庞某逃匿的事实,庞某未在巴中期间与携款逃匿性质不同,不能必然得出其离开属于拒不偿还。针对集资诈骗罪的指控,经查,各借款人在借款前均认识庞某,在案无证据证实庞某采用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向不特定的人进行集资。根据庞某供述、各债权人陈述以及在案书证、证人证言,可证实庞某借款的原因是代理小角楼酒和投资巴中市抱国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厂,经查,庞某的借款时间确实是在其代理小角楼酒、投资抱国醇酒厂的期间内,故借款的事由并未虚构。针对庞某借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的问题,经查,现有证据证实庞某对巴中市抱国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厂进行了投入,酒厂也进行了生产,现有在案证据不能确定庞某投入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与所筹集资金规模的比例,不能锁定资金去向,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庞某在此期间有肆意挥霍,携款潜逃、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逃避返还资金的情形,从而实现非法占有。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庞某构成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庞某所犯罪名不能成立,故撤销原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庞某无罪。
从以上案件中可以看出,对于庞某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观点不同,案件经上诉、抗诉、驳回、再上诉、再驳回等几番波折,最终才被宣判无罪。在对于庞某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问题上,终审判决从三个角度对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进行了评析。首先,针对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行为的问题,终审判决以无证据证实庞某采用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向不特定的人进行集资,认定庞某行为不构成非法集资;其次,针对庞某是否存在“使用诈骗方法”的问题,终审判决以庞某未虚构借款事由而否定“使用诈骗方法”的指控;再次,对于庞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终审判决以在案资金去向证据不足,从而否定了庞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笔者认为,终审判决在中介判决无罪的理由时,将其完全归结于证据不足不够准确,从判决具体理由的列举来看,该案中实际还存在定性不当的问题,庞某的借款行为本身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也是判决庞某无罪的重要理由。
【案例】刘某甲被指控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判无罪案[148]
宣恩县人民法院审理宣恩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某甲犯集资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2014)鄂宣恩刑初字第00087号刑事判决。原审查明,被告人刘某甲于2007至2008年间在利川市开办了柏杨养殖合作社,刘某甲为法定代表人,业务范围为生猪养殖、销售,之后又设立恩施州玉泉养殖专业合作总社。刘某甲在经营过程中,向张某乙、刘某乙、李某丙、何某、贾某等合作社成员借款,之后,在与湖北民族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合作过程中,向该学院教师胡某、肖某、李某甲、宋兴建、王某甲非法发行股票34张,总金额17万元。刘某甲所借款及欠款已全部清偿。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刘某甲开办的恩施州玉泉养殖专业合作总社是一个经济组织,属于企业性质,其机构、制度较为完整。刘某甲在借款时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隐瞒差钱的真相,不能认定其采取了欺诈方法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被告人刘某甲指使陈加林在湖北民族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以发行内部股券的形式在老师处集资的行为是非法的,但该学院与恩施州玉泉养殖专业合作总社有业务合作关系,所集资的对象是该学院的职工,其对象是特定的人,且只吸纳了五个人的资金,合计只有17万元,该行为既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也不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决宣告被告人刘某甲无罪。
抗诉机关宣恩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刘某甲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人刘某甲明知没有偿还能力,仍虚构借款用途,虚假发售企业内部股劵,以高息为诱饵,大肆向社会公众集资,且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造成巨额资金不能归还,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www.zuozong.com)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甲设立合作总社是为了从事生猪养殖的目的是明确的。刘某甲在向宣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合作总社时,虽然没有如实登记合作总社成员,并按照申报的出资额进行出资,但客观上合作总社在设立时是有一定的实物资产的。检察机关所提原审被告人刘某甲在申请工商登记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是以此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为日后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做好铺垫的意见,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并认定,刘某甲在向何某、贾某、肖某、张某甲、张某乙、刘某乙、李某乙借款时,既没有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的手段,也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刘某甲对所借款项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此外,原审被告人刘某甲的借款对象也是特定的人,不属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故原审被告人刘某甲的上述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也不构成其他犯罪。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在以上案件中,一、二审判决对刘某甲判决无罪,同样是基于三个理由,即没有使用诈骗方法、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不构成非法集资行为,二审判决重点针对刘某甲设立合作总社时未按照申报出资以及没有如实登记成员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评价。刘某甲的行为虽然属于欺诈行为,但是不能以此推定刘某甲不具备履行能力,且该欺诈行为欺骗对象系工商登记部门,属于行政违法,与之后借款行为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刘某甲“使用诈骗方法”借款;另外,刘某甲的实际经营行为和借款目的证实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均属于非法集资犯罪,在我国司法解释对于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往往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客观行为等同于非法集资,并有学者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界定为特殊法条和普通法条的关系。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失偏颇。从广义上理解非法集资犯罪,其属于一类犯罪的总称,而不存在非法集资罪这一罪名,从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不存在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之关系;如果对于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狭义理解,将非法集资行为特征等同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特征,则在行为方式上,二者存在部分重合,但仍然不能得出二者属于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之关系的结论。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杂客体;第二,客观上是否使用诈骗方法;第三,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中,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二者的主要因素。我们针对下面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案例】李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149]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某、白某、孙某、刘某等4人犯集资诈骗罪及许某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2013年作出一审判决。原判认定: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李某与白某通过中介在郑州市机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河南快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后又将该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并未实际出资。2011年8月份,郑州市工商行政机关发现快易担保公司非法从事担保业务,要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立即将该公司予以注销。同年8月22日,白某在债权债务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快易担保公司的注销手续,并登报公示。快易担保公司成立后,被告人李某和白某负责日常工作,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某等人以快易担保公司为依托,以高息作为诱饵,大肆进行理财宣传,吸引社会公众到其公司存款。经鉴定,快易担保公司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共计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661336500元(已扣除续存金额75528500元);截至2011年10月31日尚未归还客户总额为237265000元,扣除已付利息17766122元,扣除还本金额24308013元,尚欠客户净额为195190865元。上述被告人非法募集资金后,将90000000元以豫海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案发前已退还40000000元),将70576657元以孙某等个人的名义购买房产20多套,将6709900元用于KTV等处装修,将8087244元用于购买宝马等高级轿车。案发后,部分被告人退还赃款66万元,公安机关追回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32002787元,尚有损失人民币62528078元无法挽回。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李某、白某、孙某、刘某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许某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李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并辩称:李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关于上诉人李某、白某、孙某、刘某及其辩护人“四上诉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李某等在案的十一人以快易担保公司的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购买房产、土地使用权、KTV等经营性活动,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在案证据证实李某等人将少量资金用于购车等挥霍行为,不能确定四上诉人使用了明显的诈骗手段非法占有集资款项的目的,不应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四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并认为,上诉人李某等人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某、白某、孙某、刘某等的判决部分,改判该6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适当刑期。
在以上案例中,二审法院对李某等四人由集资诈骗罪改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由在于,李某等人将吸收资金主要用于经营性活动,仅有少量用于挥霍,故不能认定行为人使用了“明显”诈骗手段非法占有集资款。
笔者注意到,在大量集资诈骗案中,公诉机关均或多或少地存在对行为人挥霍财产的指控。浙江吴英案中,公诉机关指控,吴英将大量珠宝等高价物品赠与他人,还购买豪车,盲目投资期货亏损4700万余元,盲目竞标东阳某地块,致使800万元保证金被没收等,足以说明吴英在肆意挥霍集资款,并适用2010年解释第四条第(二)项“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之规定,认定吴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针对吴英购买豪车珠宝的行为是否能认定其具有恶意挥霍行为,以及由该行为能否认定吴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当时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尽管吴英案判决已经盖棺定论,但现在再来回顾该案相关证据、事实及定性,不得不说,判决中对于吴英的“挥霍”行为定性有失偏颇。而且,即便依照《2010年解释》第四条第(一)项“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之规定,吴英将极少量款项用于个人消费,但绝大部分款项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也不应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该判决结果也不符合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的相关规定:“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款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便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值得强调的是,该纪要规定的“少量资金”在集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明确,这也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同类案例在判决结果上存在的重大差异,有不少案件将其中用于个人奢侈消费的部分资金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而将其余款项金额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另外,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否转化为集资诈骗罪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可以转化。[150]2016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我省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对被告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但后期逐步转化为集资诈骗行为的案件,定罪时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准确区分被告人犯意的转化时间节点,可从被告人供述、集资款的去向、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集资款的管理等方面综合认定。”即是认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转化为集资诈骗罪。笔者认为,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果集资行为人收取款项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么,该行为应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不存在由非法吸收公众罪转化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收取款项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吸收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在吸收资金之后,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吸收资金行为和之后的行为应当分别进行评价,后一行为构成其他罪名的,数罪并罚,故也不存在罪名转化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