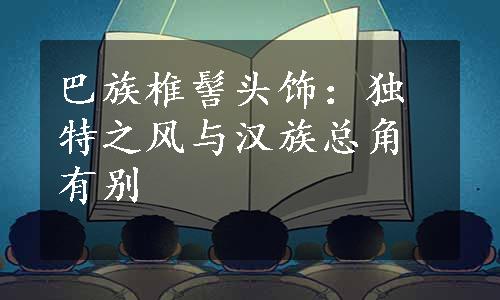
头饰或称发式,即对发的处理,而成为各种互有区别的头式,各民族间就其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发式亦异。谈到西南民族,常以“椎髻”二字作为一般的描写,致使后世无从了解,但从文物图绘中人头的描绘,和古籍中留存的解释,亦可能辨其小有区别之处。《蜀王本纪》谓蜀人“椎髻、左衽”。《南齐书·蛮传》亦言“蛮俗:徒跣,椎髻或剪发”。元稹酬白乐天诗,写通州风俗,有“椎髻抛巾帼”之句,此应理解为巴蜀人同有椎髻之俗。但是否有异于《史记·西南夷传》所称之夜郎、邛都之椎髻,这是值得加以重视的。今天的彝族男子在头的右方,用头巾裹成一支长角的“天菩萨”,若此即为夜郎、邛都等椎髻的遗俗,那就与巴蜀椎髻的形状有相当的区别。巴族曾被称为“弜头虎子”。“弜”,《说文》云“彊也”。彊之一义,应从《释名》卷4《首饰篇》“彊,其性凝彊,以制服乱发也”,加以体会。冬笋坝出土的巴族铜剑、铜矛,于其心手纹上,绘一头上具有双结的人像,如附图,前文已试释此人像为“杜主君”,杜主是椎髻的蜀王。这个双髻形象,有异于彝族单髻的“天菩萨”。时人以“蜀”“叟”“洛苏”(即彝族自称)三者音相近,头椎髻,即认蜀与彝是为一族,似乎尚欠分析。此剑出自巴地,而巴人亦有“弜头虎子”之称,“弜头”是应与此为同一形象,而为男子之头饰。其在妇女,则应为《史记》所称之“冒絮”,晋人已释为巴蜀头巾。《释名·首饰篇》“绡头,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齐人谓之 ”。此应当合《史记》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故事来看。晋人既释冒絮为巴蜀头巾之名,而冒应读如陌,以存其音。即言以头巾敛发于头使上,称为“陌头”,从头解下称为“陌絮”,因此可以提挈文帝。称之为“陌头”“陌絮”,可能起源于巴。《释名》并释“珰”为“穿耳施珠,本出于蛮夷所为,今中国人效之”。现彝族男女犹保存此俗。于此可见民族间之风俗文化交流,相互仿效,其开始甚早。中华民族之融合与凝成,成为又伟大又古老的国家,并非偶然的事。
”。此应当合《史记》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故事来看。晋人既释冒絮为巴蜀头巾之名,而冒应读如陌,以存其音。即言以头巾敛发于头使上,称为“陌头”,从头解下称为“陌絮”,因此可以提挈文帝。称之为“陌头”“陌絮”,可能起源于巴。《释名》并释“珰”为“穿耳施珠,本出于蛮夷所为,今中国人效之”。现彝族男女犹保存此俗。于此可见民族间之风俗文化交流,相互仿效,其开始甚早。中华民族之融合与凝成,成为又伟大又古老的国家,并非偶然的事。
再谈巴族椎髻之风,是否有别于汉族“总角”的头饰。《释名·首饰篇》:“总,束发也,总而束之也。”“总角”亦称“ 角”。今从殷墟安阳出土所雕之玉人双髻,及朝鲜乐浪汉墓出土漆器所绘人物发式来看,其中有绾发而束于头之两角者,蜀人称之为“鬈鬒”,此当为
角”。今从殷墟安阳出土所雕之玉人双髻,及朝鲜乐浪汉墓出土漆器所绘人物发式来看,其中有绾发而束于头之两角者,蜀人称之为“鬈鬒”,此当为 角的形象。至冬笋坝铜剑铜矛所绘的双髻人像,是髻发使上,从头部左右斜出如角,森然挺立,故名之为“弜头”,形状是有区别的。头饰虽属于局部的小事,正以其生活习惯的不尽同,而各有其特殊,未能泥于古之“椎髻”一名,而失其细致的分别。文物工作,而能分析和解释历史,作用亦在此细致和鉴别之处。(www.zuozong.com)
角的形象。至冬笋坝铜剑铜矛所绘的双髻人像,是髻发使上,从头部左右斜出如角,森然挺立,故名之为“弜头”,形状是有区别的。头饰虽属于局部的小事,正以其生活习惯的不尽同,而各有其特殊,未能泥于古之“椎髻”一名,而失其细致的分别。文物工作,而能分析和解释历史,作用亦在此细致和鉴别之处。(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