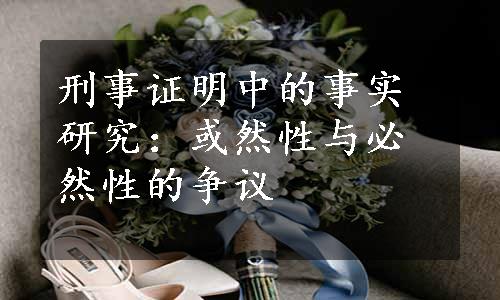
西方国家的定罪标准在理论上常被称为高度盖然性的“真”或“或然性的事实确信”,与此区别,我国的定罪标准则被称为一种必然的真实或“必然性的事实确信”。因此,探讨事实认定的或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是探讨刑事诉讼中的定罪证明标准应是“相对真实”还是“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的一种主要争论方式。坚持“相对真实”的论者常常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认为命题都是或然性的作为论证的根据,而坚持“绝对真实”的论者则大多以否定经验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来进行反驳。论辩双方都没有看到的共同问题是:经验主义认为命题具有或然性具有特定的所指,即其是针对不限于特定时空的普遍命题而言;事实认定是特殊命题而非普遍命题的判定,诉讼中的事实认定离不开普遍命题的运用,但这种普遍命题是一种限于特定时空的普遍命题,为一种“普通命题”。正是因为没有说清楚诉讼证明中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事实确信”及其推理特征,所以,不仅导致没有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证明标准差异上的真正原因,而且,也使得对事实认定推理性质的理解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
有些在证明标准上坚持“相对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论者认为,根据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导源于经验或通过归纳而得到的知识或命题缺乏普遍性和必然性,只是一种盖然性的结论,盖然性的程度取决于占有证据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其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永远也达不到数学知识或命题那种绝对确定性,因此,作为经验性的诉讼证明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正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1]这样的论述大多以哲学家波普尔所举的例子为证,这就是:无论多少对白天鹅的观察都不能确立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命题。相反,在一些坚持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论者看来,需要拒绝经验主义哲学的片面性,因而指出:“经验主义把感性认识作为认识的全部内容,把归纳法作为获取新知识的唯一方法,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人的认知能力,其结果必然是否定认识世界的绝对性……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及对立和统一的方法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必然导致肯定客观真理的可能性……”[2]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者在批评前者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在论据上以一种“主义”来拒绝另一种“主义”,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外在批评”而非“内在批评”[3]的方法。同时,其所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是使用了诸如“演绎”、“分析”、“综合”、“对立和统一”、“本体论”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大词”,并没有真正“以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服人”。因此,这种批评太过简单,可以说基本上只是武断地给经验主义哲学贴上“不科学”的标签,而没有真正指出其为什么不科学的原因。显然,这种批评是无法让对手心服口服的。容易收到实效的批评应是一种“内在批评”。正如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否定必须渗透进对方的据点,用对方自己的理由来否定他自己;如果从别的什么地方来攻击他,则就会引起不便,并且不是真正地击败他。”[4]在笔者看来,以“内在批评”的视角来审视,是很容易发现在证明标准上坚持“相对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论者在这方面的问题的;质言之,根据经验主义哲学,也不能得出事实认定和诉讼证明不能形成必然性或“绝对真实”的判断。经验主义哲学所说的知识或命题的或然性,是就不限于特定历史时空的全称命题或普遍命题这样的“真理性的认识”而言,而没有否定事实认定可以实现“真的”必然性,无论事实是当前的,还是过去的。正如波普尔的真理证伪论,只是说普适性的经验理论从逻辑上无法完全被所有的事实所“证实”而只能被“证伪”,普适性经验理论如果根本不能被“证伪”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不可“证伪”的。[5]波普尔之所以要提出真理证伪论,其目的是要批评传统的经验主义真理观或者说对其进行修正,即其认为真理不过是一种假说,而不是像传统经验主义哲学所认为的那样,真理的辩护条件是要看其是否来源于经验归纳或能否得到个别事实的证实。在“波普尔的天鹅”这一例子中,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未来一定会看到白天鹅,但却在一定条件下能肯定在过去某时某地有一只白天鹅。波普尔所说的特定事实对普遍命题的“证伪”,本身隐含的前提就是对特定事实的认识可以有必然性或确定性的判断。至于说经验知识或命题达不到数学知识或命题的绝对确定性,是就普遍命题的比较而言,不能因此就比较出事实认定的确定性不如数学命题的确定性,这种比较对讨论事实认定的或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按经验主义哲学,经验命题的“真”需要经验对象的检验,因为经验世界是流变的,所以,经验性普遍命题的“真”不可能有绝对的确定性,其确定性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经验对象,而数学命题的结论之“真”仅仅蕴涵在命题的演绎前提里面,因而数学命题不因经验世界的改变而失去其普遍的绝对确定性。由此可以说,经验主义哲学所言的或然性或相对确定性的针对性没有得到论争双方的认真对待。值得指出的是,有的论者既论证说根据经验主义哲学经验判断都是或然性的,但又在一些地方说有些时候“裁判者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真实’”,[6]这种矛盾的说法不免让人觉得莫名其妙。(www.zuozong.com)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经验主义之间的“主义”之争是针对本体论问题,这种争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传统经验主义中有一个笛卡儿式的自足的“自我”或“主体”观念,而且认为经验是一种被动的“反映”,比如,洛克的“白板”论就是典型代表,但是,如前指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家看来,这种自足的“自我”或“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自我”或“主体”是在特定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变化的,[7]也就是说“自我”或“主体”有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或福柯所说的“知识型”,因此,人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总是带着一定的观念图式(非先验的)去“接近”经验现象,而不是“白板”式的“反映”,一切“感觉”或“知觉”都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传统经验主义看来,我们感知到的经验现象(感觉材料)并不是真正的“实在”,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无法认识的本体世界,[8]但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家看来,并不能将世界划分为本体与现象,在经验现象“背后”并没有什么本体世界,[9]因而是以一种常识观念来看待经验现象的实在性,即认为依靠与外物的相互作用就能够确定经验现象的实在性。[10]当然,经验主义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比如经验是被动式的“反映”和将客体分为本体和现象这两种传统的见解就基本上被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所否定。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一样都力图“科学”地对待社会世界,[11]而且二者都强调经验实证是关于现象的知识来源,所以,不管二者在本体论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争执和分歧,也并不影响二者对诉讼证明中的“事实确信”在经验认识论意义上的性质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与辩证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基本一致,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也说,经验认识的任务应当交给“事实科学”,哲学只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12]
应当说,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会承认裁判者在诉讼证明中形成的“事实确信”,有的可能有或然性,有的也可能有必然性。可以说,关于诉讼证明中的事实认定具有或然性还是必然性问题的已有讨论大多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这就是,不恰当地把在诉讼证明中的个别事实证明能否获得必然性“事实确信”的问题与应否以这种“事实确信”作为证明标准的问题混淆在了一起,反对以必然性“事实确信”作为证明标准的论者一般认为在诉讼证明中根本不可能形成这种“事实确信”,相反,有论者因认为诉讼证明能够形成必然性“事实确信”就得出它必然应该成为证明标准的结论。实际上,西方国家之所以将或然性“事实确信”作为诉讼证明标准,其原因并不像学者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西方国家认为任何事实证明都只可能形成或然性“事实确信”。比如,在西方法律中,能够根据司法认知这种立法技术所确定的事实认定一般都是一种“客观真实”或必然性的“事实确信”。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根本上是因司法价值选择的不同,而与在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抉择”没有任何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