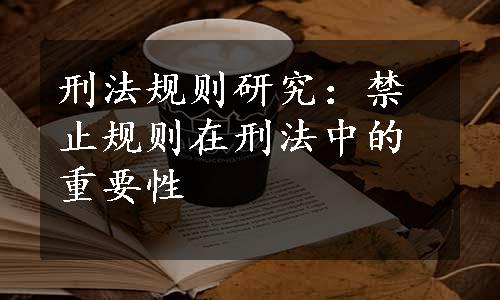
一般而言,禁止规则是指要求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行法规则。完整的禁止规则通常包含“行为模式”和“效力规则”。在民法上,有“强行法优于任意法”的格言。对禁止规则的判断一般遵循如下原则:一是如果既禁止特定的行为,又禁止特定的行为后果,这时行为应该绝对无效;二是如果法律仅仅是对特定的行为模式或者实现特定行为模式的方式加以禁止,但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时就不能简单地判决行为绝对无效,而是需要结合禁止性规则禁止的行为主体、客体与内容进行综合考虑,然后对该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评判。在刑法上,禁止规则主要体现在罪刑规则之中,是罪刑规则中占比最高的规则。同样,其完整的逻辑结构包含相对“罪”的行为模式和相对“刑”的制裁模式。但与民事法律不同的是,它们所解决的不是行为法律效力的问题而是解决罪刑关系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按刑法的逻辑进行的。这种逻辑,一方面,因禁止性规则与容忍性规则的冲突,强行法未必优于任意法。当社会的法律系统在价值选择上倾向于权利本位的时期,特别是涉及诸如宪法权利这样的一些基本权利时,这条格言并不适用。另一方面,在解决其他强行规则与任意规则时,仍然适用这一格言的逻辑,优先适用强行法。
从罪刑规则的结构上看,由于制裁模式(行为模式也一样)对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上体现两方面的机能,(即传统刑法理论所指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机能,既针对社会又针对法律适用者,体现双向约束的机能特征),因而在行为规范的意义上,可以将法律后果的这一部分包含在行为模式广义的范畴内观察,成为刑法调整社会的行为模式的完整“清单”。因此,我们可以从行为模式的角度,观察禁止规则,并以此分析和归纳禁止规则的特点。
为此,有必要观察罪刑规则的组成。从我国刑法立法的情况看,我国刑法分则的法条,在处理罪刑关系上有各种不同的做法。逻辑结构上一般是条、款、项的结构,条的部分是总纲,统辖以下款、项内容。相对这两者,条是属结构,款、项是种结构,是条的下位概念。每一个法条至少有一款,有些法条就是如此。这类法条往往是规定行为的基本模式和派生模式,如我国《刑法》第123条【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规定:“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下划线部分属于基本规则,中划线部分属于派生规则。类似这样的法条没有其他款和项的规定,也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刑法规则。另外,相当数量的法条,除第1款之外还有其他“款”规定,如我国《刑法》第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1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2款、第3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类法条第2、3、4款与第1款的规定处于同一法条之中,它们之间往往具有逻辑、经验或性质、技术上的关联。这类条、款结合的法条,有的或者是第1款规定的基本行为模式在构成要素的一些调整(如上例),有的或者是一种解释性、说明性的技术规则,如我国《刑法》第141条第2款下划线部分【生产、销售假药罪】:“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有的或者是处理更复杂的转化问题,如我国《刑法》第333条第2款下划线部分【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总之,这些条款涉及与第1款关系密切的规范性或者技术性问题,有着各自独特的模式化意义,但它们都是依赖基本规则的附生性规则,不具有完整的、基本的行为模式的典型性。在微观层面,这些附生性规则可以理解为结构性规则,需要通过基础性规则(即基本规则)发挥作用。
除了上述两种条、款结构外,相当数量的一些法条还有项的规定。相对款的规定,项的规定属于种概念,受款和条的上位概念制约,并根据条款主题发挥规则作用,如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www.zuozong.com)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上述八项规定形成抢劫罪的八种派生模式。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除了条、款、项的逻辑结构外,还有各本条之下的条文。用某某条下“之一……”结构表达。各本条与“之一”之间也存在属种关系或者至少关联关系,它们之间往往具有逻辑、经验、性质或技术上的关联,例如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在本条之下从之一到之六,形成6个相对独立的法条,规定了6个罪名。每个法条也可能形成自身的条款项的逻辑结构,如该条之二规定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
(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
(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个法条中,逻辑结构上的条款项一一具备。其规则的性质、地位与功能也需要分别的确定,并与《刑法》第120条联系起来理解。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处理方法,用一个单独的法条,解决其他法条原本可以和应该规定的内容,但因立法技术和行为类性质的原因,集合成一个法条。比如,我国《刑法》第119条【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3]。通过这样的法条,将上述五种犯罪的加重情形和过失犯罪一并解决。另一些法条,本身并没有规定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式,但仍然因为技术上或者类性质上的某些因素成为一条分则条款。如我国《刑法》第149条和第150条[4]。
总之,通过观察与分析我国刑法分则的各条,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分则条文都是关于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式和制裁模式。有些条文并不直接规定具体犯罪的罪刑模式,而是从逻辑上和技术上处理涉及有关个罪规则的其他问题。在规定具体犯罪的罪刑模式中,不同规则的地位、性质、功能和作用并不相同。通常处于各本条第1款前部(如果有派生规则的话)的基本规则,是该罪名下典型的行为模式,是我们分析行为模式的典型样本。基本规则是决定罪名、决定行为性质、具有完整的行为模式的规则。禁止规则是主要的规定方式。
禁止规则的结构与特点分析如下:
禁止规则的结构——从形式上观察也是一体两面的,即分配刑法义务与确定构成指标。从刑法义务(规则形式)的角度观察,这种规则确定的是禁止义务,从行为上观察是要求公民不作为,即不得从事规则禁止的行为。这种行为模式赋予公民的是一种消极义务,只要不去实施这种行为,公民就已经遵守了法律的规定,并受法律保护。相反,如果公民挑战规则,实施了规则禁止的行为,便直接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其行为便触犯了刑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罪行都是如此。从行为模式看,基于对刑法义务的违反,我们可以把这种违反禁止规则的犯罪称为违禁犯,基于构成要件的行为模式,则称为作为犯。这种规则的特点是:规则要求禁止、要求不作为,而违反规则是违反禁止,是作为。两者的规范结构与实践结构正好相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