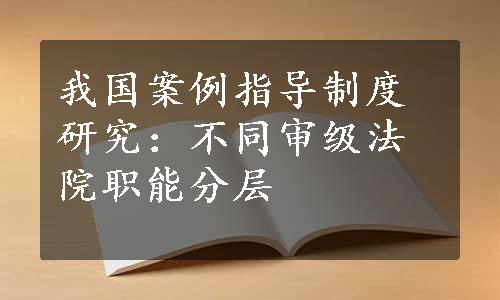
将部分二审终审的案件调整为三审终审主要是从外部框架上就审级制度进行梳理与重构,我国审级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心则在于消除当前四级法院职能定位过于重复、趋同的弊端,即从审级制度内部就不同层级法院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构。目前我国共有四级人民法院,从审级功能的改革方向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三审法院。其中,一审法院的职责重心在于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解决具体矛盾争议;二审法院的审判职责则在于依法对一审的审判活动进行审级监督,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实现二审终审;三审法院的职责定位则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审判业务指导、统一法律适用。而根据这一审级功能定位,四级法院应当相应地调整职能设置。
(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其主要职能应在于通过审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创制公共政策,维护法制统一。根据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越靠近法院组织体系金字塔上层的法院,应越多地承担维护法律统一性的职能。最高人民法院处于法院组织体系的最顶端,机构唯一且权威性最高,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审判指导、统一法制是最高人民法院责无旁贷的职责。基于这种审级定位,首先,应当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条有关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规定。虽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空转条款”,截至目前并未发生过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情形,但这一规定的存在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正确的职能定位。其次,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只针对案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不对事实认定上的争议进行裁决。由此,将最高人民法院从单纯地审查案件事实以及审理大量诉讼案件的诉累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审判指导、统一法律适用工作。
(二)高级人民法院
在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高级人民法院地位较为特殊,既处于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同时又是省级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上级法院。这种特殊的位置决定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向二审终审、依法纠错以及推动辖区内法律统一适用方向发展。而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承担着二审法院的职能,还应具有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因此,首先,应当取消各高级人民法院针对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将各高级人民法院定位为上诉审法院,行使二审终审的职权。通过明确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审功能,强化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推动辖区法院的适法统一。其次,应当强化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纠错功能,增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审查的规范力度,提升申诉审查的质量,在依法纠错的基础上,切实维护好生效判决的既判力。
(三)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我国有400多家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不仅承担着二审终审的职能,同时还就重大、疑难、复杂以及新类型案件承担着一审裁判功能。在整个审级制度中,中级人民法院兼具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双重角色。因此,对于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级功能,一方面要加强其作为上诉审的审级监督职能,通过对上诉案件的规范性审查,充分保障当事人获得第二次救济的程序权利,依法纠正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错误,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增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的裁判质量,强化其作为重大、疑难、复杂以及新类型案件的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定分止争。
(四)基层人民法院
目前,全国大约有3 000多家基层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数量最多,位于人民法院组织体系的最底层。基层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是整个审级制度的前提,基层人民法院能否尽可能将整个案件事实确定下来,将社会矛盾就近、就地化解,不仅关涉到基层人民法院自身功能能否实现,还关系到能否有效控制上诉规模,关系到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能否专注于纠正错误裁判、统一法律适用等。而根据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越靠近最底层的法院越应当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矛盾纠纷;同时,随着四级法院三审终审制的逐步确立,法律统一适用功能的逐渐上移,而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的功能则逐渐下移,由广大的基层人民法院来承担。因此,基层人民法院的审级功能定位,应当是要使其承担起审理绝大多数一审案件的职责,尽可能将案件事实确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注释】
[1]章武生:《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塑》,《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3][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9页。
[4]陈卫东主编:《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6页。
[5]卢佩:《德国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之第三审级司法审查》,《现代法学》2013年第11期。
[6]赵红星:《我国审级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研究》,《河北法学》2010年第10期。
[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8]陈兴良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9]刘克毅:《试论类比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以普通法的运作机制为例》,《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
[10][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11]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12]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德国判例考察情况的报告》,《人民司法》2006年第7期。
[13]张志铭:《司法判例制度构建的法理基础》,《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www.zuozong.com)
[14][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7页。
[15]王志强:《中英先例制度的历史比较》,《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6]何家弘主编:《外国司法判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9—50页。
[17][美]彼得·海:《美国法概论》,许庆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8]陈刚:《我国民事上诉法院审级职能再认识》,《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19]张军主编:《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0]胡伟新:《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考核排名》,《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27日第1版。
[21]宋晓:《判例生成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22]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2016年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 985件,审结14 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由此可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数量之多、增幅之明显。
[23]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4]张晋红:《两审终审的制度性缺陷与适用异化》,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三辑。
[25]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法学》2012年第1期。
[26]陆幸福:《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之证成》,《法学》2014年第9期。
[27]唐震、李鹏飞:《基层法官谈案例援引》,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7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28]张晋红:《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之机理研究》,《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五辑。
[29]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30]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31]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2]冷罗生:《重构我国审级制度的思考》,《求索》2009年第4期。
[33][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34]李爱红:《审级制度的重构与司法公正》,《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