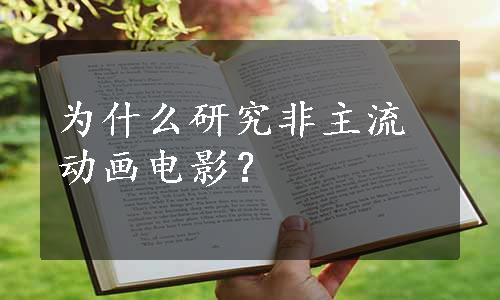
非主流动画研究已经时机成熟——《超级无敌掌门狗:人兔的诅咒》(Wallace&Gromit:The Curse of the Were-Rabbit)掀起的“非主流动画”复兴狂潮。
在2006年第7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英国黏土动画《超级无敌掌门狗:人兔的诅咒》战胜了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与蒂姆·伯顿的《僵尸新娘》(Corpse Bride),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我们不难看出,三部提名最佳动画长片奖的影片中有两部是定格动画,而另外一部则是传统手绘动画片(当然该片也使用了一些CG技术,但是远远谈不上是电脑动画)。而最佳动画短片奖则授予了约翰·凯恩梅卡(John Canemaker)与佩姬·斯特恩(Peggy Stern)联合导演的真人与手绘相结合的动画片《月亮与儿子》(The Moon and the Son:An Imagined Conversion)。这一切足以说明无论是理论界、制片方,还是普通观众,大家都已经开始重视非CG类的动画片了。同时也证明了这些“土得掉渣”的“非主流动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它们正在创造辉煌。
当《超级无敌掌门狗:人兔的诅咒》的导演尼克·帕克(Nick Park)与史蒂夫·博克斯(Steve Box)上台领奖时,戴着巨大卡通领结的他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小型卡通领结戴在了那座奥斯卡小金人的脖子上。瞬间,英国人特有的绅士风度与一丝怀旧感迎面袭来。二人标准的英国口音使人不禁惊讶地发现,这已经是“超级无敌掌门狗”系列作品第四次与奥斯卡结缘了。
在这部影院长片问世之前,这个典型的英国中年男人华莱士(Wallace)和他忠诚的小狗格罗米特(Gromit)已联合主演了3部30分钟的中篇动画片和10部1分钟左右的动画短片。这三部中篇作品:《奇异的假期》(A Grand Day Out,1989)、《错误的裤子》(The Wrong Trousers,1993)、《间不容发》(A Close Shave,1995),又全部与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有缘。《错误的裤子》《间不容发》摘取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而《奇异的假期》尽管只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而未获奖,但是那年的大奖得主依旧是“超级无敌掌门狗”系列作品的导演——尼克·帕克。也就是说,《奇异的假期》是被自己“打败”的。好在“肥水不流外人田”,最终,最大的赢家还是尼克·帕克[该年的获奖作品是其执导的《动物悟语》(Creature Comforts)]。
从1989年到2006年,同一系列作品四次“染指”奥斯卡金像奖并从未空手而归!这在奥斯卡最佳动画片获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当年的米老鼠、唐老鸭都不曾有过如此骄人的成绩(这二位美国超级动画明星也许获得过无数次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但是从未获得过奥斯卡动画长片奖)。
由于太过商业化而向来被艺术家们所鄙视的奥斯卡奖这次并没有钟情于纯三维制作的《四眼天鸡》(Chicken Little)、《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而是全面倒向传统动画的阵营。与近年来电脑动画垄断全球的局面相比,2006年的奥斯卡也许是个暗示或先兆——非主流动画时代已经来临。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招收实验动画与实验电影硕士生,这对于中国非主流动画研究与创作来说无疑是个好兆头。
既然非主流动画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那么,为什么国内动画理论界却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予以响应呢?为什么相关信息如此闭塞?为什么学生对“非主流动画”这一概念毫无兴趣?我不禁要先谈谈中国影视理论界的现状。
首先,“伪理论文章”肆意横行,使本来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影视理论逐渐变成一小撮所谓的“专家学者”“文化精英”的御用品。理论文章越来越成为“伪专家”们卖弄学问、蒙骗无知学生的工具。面对含金量越来越低的影视理论文章,专家学者们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师们”都为读者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博学。杜甫当年追求的“贩浆走卒者皆明其意”的创作标准早已荡然无存。
然而真正对电影本体进行研究的文章却被视为“形式主义”。北京电影学院著名教授周传基老师不厌其烦地四处宣讲视听语言等影视入门理论,但招来的却是一片骂声!中国影视理论家们喜欢大谈特谈电影的哲学内涵与美学特征,但是从不肯踏踏实实研究一下什么样的色彩是观众喜欢的、什么样的声音是使人厌烦的等电影本质问题,最终便产生了“我懂什么,电影就是什么!”的可笑逻辑!我是研究符号学的,于是电影就是符号学;我是研究哲学的,于是电影就是哲学;我是研究文学的,于是电影就是文学;我是研究戏剧的,于是电影就是戏剧;我是研究宗教的,于是电影就是宗教。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电影是综合艺术,于是所有人无论懂不懂电影都可以从中分一匙羹。从来没有人认真地问一句:“电影、电视究竟是什么?影视特性究竟与我所熟悉的研究范畴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是否正是影视所独有的特性?”当你告诉他们影视是声音与光线、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时,他们会说:“这么小儿科的解释岂能登大雅之堂?太简单了!别人一听就懂,那还叫什么理论研究?这简直就是形式主义!”
下面仅举一例来证明国内影视理论研究水平如何: 某学者在其著作中说:“由于历史渊源不同,同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与电视在对视觉效果与听觉效果的侧重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特色。源于无声电影的现代电影虽然有越来越重视音响效果的趋势,但总体上看一直是把视觉效果放在最突出位置上的,至今许多电影理论家仍然认为‘依靠配音却很少能拍出成功的影片。相反,依靠声音往往说明创作者只具有第二流的水平’[2]。但由广播事业发展而来的电视艺术却从一开始就具有喋喋不休的特点。在电视中,音响,特别是语言的功能要比电影中重要得多。”
请问这是哪一年的理论?默片时代吗?“电影是视听艺术的特性”什么时候变成了“视觉第一,听觉第二”了?一边是美国著名摄影师在强调声音对摄影的重要性——“没有声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拍摄”;一边是中国著名学者却在论证“尽管声音没有视觉重要,但是我们电视比电影强得多,因为我们是广播事业的后代”。而电视工作者也没把脸露在点儿上,他们所强调的“声音重要性”竟然只是“语言功能”在影视中的作用。言外之意就是观众可以闭上眼睛“听”电视,因为它和评书联播没啥区别。
在这样浮躁与不重视电影本体研究的学术气氛下,作为电影分支的动画片又怎么可能有良好的理论研究环境?综观国内影视理论文章,只要涉及影视艺术本质总喜欢从亚里士多德甚至他的老师柏拉图说起。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动辄就“从猴说起,大谈特谈原始人如何如何”的文章!我只想问这些作者一句话:“亚里士多德那时候有电影吗?!”如果研究什么都从“劳动创造了人类”说起,那什么时候才能触摸该问题的本质?如果总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影视艺术的先决条件的话,那这世界上什么又不算艺术?把哲学家、美学家的理论庸俗化、费解化使得这些大师在我们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
周传基老师说过:“中国缺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与先锋电影运动。”此话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应该通过这两种电影类型彻底搞清楚电影的本质是什么。因此,我想通过本书完成周老师的一个夙愿。既然我们搞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与先锋电影,那我们了解一下国外优秀、经典的非主流动画总可以吧(更何况很多经典实验动画在真人电影史上也是有一笔的)。
——从《论艺术的精神》说起
非主流动画涵盖于非主流艺术范畴之内。谈到非主流艺术或抽象艺术就不能不提及俄罗斯著名画家与艺术理论家瓦·康定斯基以及他那本旷世名著——《论艺术的精神》。这本书不仅对日后的先锋派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所有从事视觉艺术的人都从中受益匪浅(包括电影、摄影、建筑、雕塑、绘画甚至室内装潢)。我认为《论艺术的精神》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作者对图形、色彩等视觉符号进行了透彻分析。康定斯基在分析这些基本元素时并不局限于视觉概念,而是从听觉、触觉、味觉、动势甚至情感角度加以阐述,使读者全方位了解抽象艺术对人生理与心理层面的影响。这无疑对后人认识与掌握抽象艺术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康定斯基这样描述以下颜色:
黑色——黑色的基调是毫无希望的沉寂。在音乐中它被表现为深沉的结束性的停顿。在这以后继续的旋律,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诞生。因为这一乐章已经结束了。黑色像是余烬,仿佛是尸体火化后的骨灰。因此,黑色犹如死亡的寂静。表面上黑色是色彩中最缺乏调子的颜色,它可以作为中性的背景来清晰地衬托出别的色彩的细微变化。这一点上,它与白色也不一样,无论什么颜色,只要跟白色相调和,就会变得混浊不清,仅剩下一丝微弱的共鸣。
蓝色——蓝色是典型的天空色。它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宁静。当蓝色接近黑色时,它表现出了超脱人世的悲伤,沉浸在无比严肃庄重的情绪之中。蓝色越浅,它也就越淡漠,给人以遥远淡雅的印象,宛如高高的蓝天。蓝色越淡,它的频率就越低,等到它变成白色时,振动就归于停止。在音乐中,淡蓝色像是一支长笛,蓝色犹如一把大提琴,深蓝色好似倍大提琴,最深的蓝色可谓是一架教堂里的风琴。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正是我所谈到的“先锋实验动画”的理论基础与特点。早期的“先锋实验动画家”大多是由画家转行而来的。他们抱着使静态画面运动起来的热情,对色彩、线条、构成等视觉元素进行大胆实验,试图创造一种“听得见的画面、看得见的声音”的全新艺术形式。搞清楚康定斯基的理论,正确认识抽象艺术是我们研究非主流动画的敲门砖。而借助其理论弄懂“先锋实验动画”这一非主流动画中最令人费解的类型,那其他非主流动画类型也就迎刃而解了。
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抽象艺术在中国一直不能被正确认识与接受,甚至被误解为“抽象艺术是远离生活的、缺乏深刻内容的形式主义艺术”。其实抽象艺术的诞生,本是西方艺术发展到某一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它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脉络。抽象主义绘画理论不但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理性哲学和经验哲学有着一定的联系,还明显地受到了德国美学家沃林格尔思想的影响。抽象主义还与印象主义有着内在的因承关系。如果没有成熟的印象主义作为基础,我们将很难想象古典主义的母体能够分娩出抽象主义这样一个新生儿。因此,从哲学和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说抽象主义是没有根据的突发奇想,是肤浅的、表面形式的故弄玄虚。
王宏建主编的《艺术概论》[3]中就此问题有以下阐述:(www.zuozong.com)
在西方,艺术的形式主义研究是一种具体学科方法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用数与节奏的和谐的原则考察音乐、建筑、雕刻等艺术。如研究什么样的数量比例才会在艺术中产生美的效果,发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并认为圆球形是最美的图形。这种偏重形式的研究是后来西方艺术理论中形式主义的萌芽。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也十分偏重对形式美和艺术技巧的探求,苦心研究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寻找“最美的线形”和“最美的比例”,并试图用数学公式将其表现出来。在18世纪的英国,形式主义方法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如哈奇生说:“对象中的美,用数学的方式来说,仿佛在于一致与变化的复比例。”画家荷加斯在其著名的《美的分析》中提出了“会使任何绘画构图变得优雅和美”的一些基本规则:“适应、多样、统一、单纯、复杂和尺寸”,认为“直线和圆弧线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变化,可以规定和描绘出任何可视的物象,因此能够产生无限多样的形式”,并称波状线和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4]在19世纪的法国,就连强调再现自然与表现理想的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也认为艺术的根本在于形式:“形式,形式——一切决定于形式。”[5]
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对艺术形式的构成、艺术语言和材质媒介的研究,成为西方艺术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现代艺术主义诸派各说不一,但都把研究的重点从传统的艺术本源转到了艺术本体——形式自身上,用诸如色彩、线条、音色、节律、媒介、符号等形式因素解释艺术。如克莱夫·贝尔就断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尽管抽象艺术由来已久,但是非主流艺术家们依旧备受世人误解与憎恨。这一现象在非主流动画领域同样很普遍。针对这一问题,康定斯基又给了非主流艺术家们以鼓励,一种借助理论而产生的巨大精神支柱。他将艺术的层次比作金字塔——越是顶级艺术家与艺术品就越少。
“三角形的顶端上经常站着一个人。他欢快的目光是他内心忧伤的标记。甚至那些在感情上和他最接近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们愤怒地骂他是骗子、疯子。贝多芬生前就是一个受尽辱骂的孤独者。”
我们经常强调艺术作品要“雅俗共赏”,但康定斯基的观点则提示我们“雅俗共赏”不应是衡量艺术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相反,走在时代前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往往是“俗不能赏”的。而这一尴尬情况也是我们研究非主流动画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曾经的“中国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说过一句“名言”:“(中国人)真正能看得懂芭蕾舞的也没几个;心甘情愿听交响乐的又有几个?”由此看来,观众是需要培养、引导而不是一味迎合的。若想读懂抽象艺术作品,恐怕也需要和听懂交响乐一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与专业基础。这种修养的得来绝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努力与专业知识的学习。我们应把握抽象视觉语言的原理和规律,多看、多听、多问,使理论与创作、理性与直觉融会贯通,最终达到一种“纯本能反应”的境界——即在进行动画创作时,非主流的外在形式已经成为创作者条件反射般的手段而非刻意追求。而《论艺术的精神》就涉及大量对于抽象艺术语言进行理性分析的内容,因此,《论艺术的精神》是研究非主流动画的入门级“教科书”。
建议在读这本书前认真阅读《论艺术的精神》。
我们做学问之人往往被要求“写文章应该学术严谨、逻辑缜密、态度严肃,应尊重客观事实而不要有太多主观色彩”。然而,什么是客观事实?什么又是态度严肃?以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的客观与否?又以什么标准来评判作者的观点是否主观?难道面无表情、语言晦涩难懂、罗圈话来回说、谁都不得罪才算学术吗?如果这是治学标准的话,我宁愿偏激一点。更何况,就算这种治学原则天经地义、千古不变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它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因为人类的“语言艺术”与“党同伐异的一贯习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阐述某一问题,更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如果我们非要强求所谓的“客观与严谨”的话,那就只会使自己陷入语言与逻辑的迷宫而无法自拔。因为想研究清楚任何一个深奥的问题,都需要从多方面辩证地加以论证与阐述。而所谓“辩证”者,即正反两方面讨论。这一有“正反两方面”就自然容易自相矛盾。作者本来试图全面而辩证地论述问题,但是最终却落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之中。于是只好拐弯抹角地自圆其说,抹杀别人的观点而强调自己的英明。请注意“逻辑缜密”与“诡辩”是两个概念,但是追究到极致时,二者的界限并不分明。
例如,刚才被我奉为经典的康定斯基理论所涉及的视觉艺术外在形式问题,就会被人们理解为“形式主义”。甚至大师也对其表示不满,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曾经说:“没有一件艺术品能单靠线条、色调的匀称或仅仅为了满足视觉刺激而打动人的。”[6]究其争论的原因,无非是“艺术形式与内容孰重孰轻”,而想搞清楚这一庞大的论题则又可以写N本书了。
因此我很推崇周传基老师的观点——“不偏激不成学问”。也许这本书会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它比较“极端”。尽管如此,我仍旧不愿意做“和稀泥”的“和事老”,因为我发现有时候稍微“偏激”一点反而容易接近真理。另外,老子不也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吗?能说出来的“道”不是真正的“道”。按照这一理论推测,我们大家都别写书了。因为一拿起笔就开始为自己和读者设置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与陷阱。与其这样,还不如“偏激”一点,起码写的时候无所顾忌、颇为开心。因此,请记住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话:
“如果真理是一只小鸟的话,文字与语言不仅不能为它插上一对美丽的翅膀,有时反而是一副沉重的镣铐。”
迪士尼出资创办的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不仅是美国第一所提供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高等教育的大学,而且是全美国顶级的动画学校之一。多少年来,好莱坞动画公司的主力军几乎全部来自该校。加州艺术学院的动画专业设置并不像中国这样分为“动画技术”与“动画艺术”方向,而是分为角色动画(Character Animation)与实验动画(Experimental Animation)。顾名思义,角色动画主要培养讲述故事、塑造角色的叙事动画片导演;而实验动画则培养本书所论述的非主流动画制作人才。
由此可见,这样的专业设置是合理并颇见成效的,否则该校也培养不出《圣诞夜惊魂》的导演蒂姆·伯顿与皮克斯(Pixar)老板约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这样优秀的学生。在这样一个由主流商业动画大师创办的学校中居然开设了非主流动画专业,并且据说这些“喝着迪士尼奶”长大的学生竟然大部分都是反迪士尼风格的。资助方不但没有扼杀这股“反动势力”,反而将“实验动画”专业作为品牌大力推广。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实验动画不仅是动画教学必不可少的元素,同时也是主流动画有利可图的试验田。
涵盖实验动画在内的非主流动画对于动画艺术发展有以下几个好处:
1.通过“先锋实验动画”在视听语言、外在形式与技巧上的探索与实践,可以拓展动画艺术的表现手法。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动画最欠缺的。一个大全景,一个长镜头,一个最普通的机位,这就是中国动画的特点——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在拍画。
2.通过“政治动画”对社会变革、政治事件的夸张描述、深刻反省,可以使动画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艺术而绝非“哄小孩”的专用品。
3.通过“成人动画”对各种“敏感问题”的探讨以及使用富有“动画特性”的表达方式,使动画片成为像真人电影一样成熟的艺术形式。从而拓展动画片市场,促进动画产业全方位发展。
4.通过“艺术动画”对各种哲学、美学问题的阐述提高动画从业人员的素质,练好“内功”。任何一门艺术拼到最后都不是看创作者的技巧如何高超,而是对生活的独到认识与良好的个人修养。
5.至于“披着主流动画外衣的非主流动画”的意义所在,就更加一目了然:赚钱!非主流动画并非是大家印象中只会赔钱的“败家子”,恰恰相反,如果把非主流动画观念与技巧因地制宜地转化为生产力,其威力之大绝不亚于任何主流商业动画片。
这也就是尽管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每个学生每年学费高达两万多美元(学费22190美元/年,生活费11500美元/年),依旧还会有那么多学生踊跃而至的原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