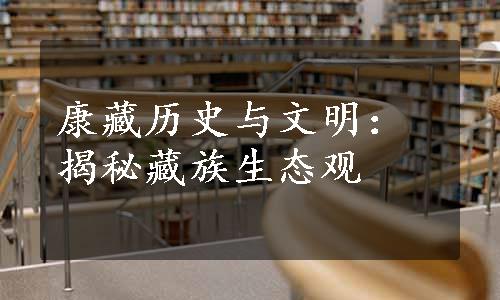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留下了一个千古名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简短、凝练的十个字,概括了古往今来人们探寻与思考“天地人生”奥秘的方向与经纬。然而,关于“天地人生”,比司马迁时代更早的老子则说过一段让我们更为惊叹且意味无穷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倘从今天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老子这段话,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人与环境、人与神、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段话,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源泉。
其实,最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天人合一”和“天地人生”的往往是人类在接近于极限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文化。三江源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接近人类生存极限的地区。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高度3500—4800米,既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也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区,被人们形象地称作“中华水塔”,河流、湖泊、沼泽、雪山、冰川、高寒草甸成为这里最独特的地貌特征与自然景观。在这样一个遍布雪山、冰川、湖泊的高海拔高原湿地区,在其严酷与高寒已臻于人类生存极限的特殊自然环境中,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靠什么来生存?他们在严酷的天地之间怎样表达自己的欢乐与忧伤?他们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来赋予生活以意义?
画册《天地人生》所展示的一幅幅极具震撼力的画面,描绘的正是生活于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天地人生》作者可谓独具匠心,他主要选取了三方面的画面来表现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其一,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即人在天地间的生存状态;其二,婚礼;其三,葬礼。三者均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其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如何对待“生”和“死”,往往关涉其文化的核心,亦最能体现该文化的人生态度及生命价值观。从此意义上说,婚礼虽然只是一个仪式,但却是一个关于“生”的仪式,它象征了生命的起始与延续,因此,婚礼所蕴含的乃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颂扬。葬礼是生者对逝者缅怀,其实质同样体现了对生命的关爱与留念。所以,《天地人生》画册的作者用“人与自然”“婚礼”“葬礼”三者来呈现三江源这一独特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本身已包含了作者对该区域人们之“天地人生”的一种独到的理解与认识,包含了对该区域人们生命之意义的提炼与思考。这或许正是作者能捕捉到一幅幅如此摄人心魄、极具震撼力之画面的原因。
藏族是三江源地区主体和世居居民,占当地人口的90%以上。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一代代顽强地在这里繁衍生息,也一代代延续着自己的文化。从世界范围而言,藏族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地域民族。由于世界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屋脊”,从此意义上说,藏族为适应高原地域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及其独特文化无疑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记得若干年前,我在拉萨遇到一位法国青年,我们坐在一块儿观看大昭寺门前藏族信众磕长头的情景,我问他为什么来西藏,他回答说,他来西藏,是想看看生活在世界上最高地方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想些什么?他的回答让我悟到,高原地域特点乃是藏族同其他民族相比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藏族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的价值所在。在文学作品中,藏族常被诗意地描述为“离天最近”“离太阳最近”的人。但高原环境毕竟是严酷的,在青藏高原环境中,空气中的含氧量常常仅为内地50%—60%,一些高海拔地区甚至不足内地的40%。高寒缺氧、植被稀疏和“物产寡薄”,也是造成青藏高原地旷人稀的原因。三江源地区更是一个地域广袤、人烟稀少之地,三江源地区土地面积占全青海省的43%,人口占10%,而生产总值却仅占青海省的3%,足以说明其生存环境之严峻。
三江源地区除东部和南部有少量耕地外,大部分为高海拔牧区,绵羊和青藏高原所独有牦牛几乎是这里最主要的牲畜种类,藏人更是唯一能怡然自得地在这里生活的大地主人。这里的藏人被同胞称作“卓巴”(即“牧人”),他们具有藏族牧民所特有的坚韧、勤劳和乐观的性格。透过《天地人生》中摄取的一幅幅藏族牧民在冰天雪地中放牧与生活的场景,我们看到,在人迹罕见的莽莽雪原之中,在苍茫的天穹之下,藏族牧人静静地放牧着他们的牦牛与绵羊,由于厚厚的雪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的牧草,牦牛和绵羊为了吃到从雪地中艰难裸露出来的草,不得不满山遍野地散布开来,形成极为开阔、壮观的放牧场面。尤其让人感触的是,在高海拔且几乎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白茫茫雪原上,黑色的牦牛散布于天地之间,它们全然不理会正在飘洒和增多的积雪对其生存的威胁,仍执着而悠然地吃着草,这景象让人着实震憾于在臻于极限的自然环境中生命的顽强。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动物品种,也是世界上生存于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牦牛主要生活于青藏高原海拔3000—6000米的高山草甸地带。在夏季,牦牛的活动地域甚至可到海拔5000—6000米的地方,直抵雪线下缘。在青藏高原上,无论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峰、山间盆地、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等各种高寒环境中,均可见到牦牛的身影。牦牛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可谓无与伦比,具有惊人的耐苦、耐寒、耐饥、耐渴能力,同时是高原上不可替代的运输工具,牦牛善走陡坡险路、雪山沼泽,并具有很好的识途本领,并能避开陷阱择路而行,能游渡江河激流。因此,牦牛被人们称为“高原之舟”“高原之魂”。从很大意义上说,牦牛是藏族人民赖以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存的最重要的生物基础。一般说来,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基本上为纯牧区。藏人在纯牧区的生存一切方面均离不开牦牛,他们喝牦牛奶,吃牦牛肉,以牦牛粪为唯一燃料取暖煮食,住牦牛毛织成的帐篷(唯有此类帐篷在高海拔地区最能御寒),穿牦牛毛皮做成的衣服和靴子,用牦牛毛皮制成的口袋盛物,迁移流动(当地俗称“转场”)也以牦牛为运载工具。在高海拔牧区,牦牛承载起了藏族牧人衣、食、住、行、烧的各个方面,在农区牦牛还是耕地能手。可以说,如果没有牦牛,藏人绝不可能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区生活。所以,在世界屋脊,在离天最近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高海拔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牦牛这一独特、坚韧、顽强的生物品种,藏人则依赖于牦牛在高海拔地区创造出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从一幅幅反映三江源地区藏族牧人生活状态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极为简单、粗放,白天他们赶着牛羊在广阔的旷野里放牧,夜晚则以牦牛毛织成的帐篷为家,帐篷里除了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具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女人永远是帐篷内外最忙碌的人,她们承担着挤奶、打酥油茶、照料小孩和全家饮食等日常事务,男人和小孩则都是天然的牧人。其实,按时下的商品价格计算,当地牧民绝不算穷,一户拥有数十或上百头牦牛及数百头羊的牧民,其家产往往达数十或上百万元。但这样的数字对他们并无太大意义。要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生存,他们那种看似简单、粗放且显得原始的生活方式就是必须的、最合理的,也是最能与高原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对自然的敬畏与尊从是藏族文化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在藏人眼中,高原上大部分山都是“神山”,大多数湖泊都是“圣湖”。藏族对“神山”“圣湖”的崇拜是绝无仅有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藏族仍然保留着匍匐于地亦步亦趋磕长头转“神山”“圣湖”的习俗,这代表了当今人类自然膜拜的极致。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与尊从是藏族祖祖辈辈在青藏高原生活所积淀下来的文化经验,代表了藏人对于处于极地的高原自然环境一种独特理解与认识,凝聚着其生存的智慧。从这个意义说,在三江源地区,GDP这样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人在这里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根本的生存之道,这不仅是建立三江源保护区的意义所在,也是当地人之“天地人生”给我们的启示。(www.zuozong.com)
不过,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单色调的。尽管藏族作为三江源地区主体和古老的世居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在当地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但目前在所划定的三江源保护区范围内尤其是黄河上游一带,除藏族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民族,他们是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和汉族,这些民族大多是后来因某些历史原因陆续迁入的。这些民族中,以蒙古族同藏族的生活方式最接近,二者均以高原牧业为基本生计,所生活的区域海拔较高。其余的民族则多以农业为生计,且多分布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地带。这些民族的迁入,不仅给三江源地区带来生存模式与文化的多样性,也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在蒙古草原上,当地牧民判断草原的优劣有一个简单方法,观察在1平方米之内草的种类,草的种类越多说明草原越好,越少则说明草原质量下降。这说明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物生命力的一个标准,即生物之生命力与物种多样性直接相关。其实,文化也同样如此,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相关。在《天地人生》画册中,我们看到了三江源地区不同的生存方式,既有游牧,也有农耕,我们也看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婚礼与葬礼。毫无疑问,文化的多样性赋予了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活更多色彩和更丰富的内涵。恰如三江源是世界高海拔地区中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一样,在这里文化多样性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特点,这同样是我们理解三江源地区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视角。
此外,尽管三江源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了生存的艰辛,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简单、粗放和几近原始的一面,但是,当地人们的生活基调却并不是灰色的。在这里,人们仍然存在充满喜庆、欢笑、热烈、温暖、幽默、欢愉的生活。如果说,简单、粗放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尊从与适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后者所体现的则是人在严酷自然环境中对于自身以及生命的态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当地人完整的生活图景。给人印象极深刻的是一幅幅当地不同民族的喜庆的婚礼场面,婚礼上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新娘、新郎幸福羞涩的面容与缀满装饰品的华丽盛装,桌子上盛满的各种美食、糕点,都无不展现着这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乐观与豁达,展现了他们在严酷环境中对生命的挚爱。按人类学的观点,仪式总是最具文化意蕴的,它不仅是人们创造出来用以平衡自己的需求,赋予单调的生活以意义,同时也最能反映人们内心的企盼与愿望。在三江源地区,隆重婚礼更是充满和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与对生命延续的期盼。画册中呈现的一幅幅喜庆、热烈的婚礼场面,正反映了三江源地区人们的一种生命态度及文化价值观。这样的婚礼,放在内地其他地区也许很平常,但在三江源这样一个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却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它们也使人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的意义和力量。文化是什么?其实就文化的功用而言,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文化是人们适应其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和智慧,也是能够给拥有此文化的人们带来最大幸福感的一种生态方式。在三江源地区,尽管严酷的自然环境使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得不趋向简单、粗放甚至原始,但是简单和粗放的生活却远不能窒息和淹没人们内心的生命欢悦、爱的表达以及对美的渴求。婚礼和葬礼都成为人们表达和寄托这些情感与愿望的最佳方式。画册中有一幅画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塞满整个院落,从房前屋后直到房顶全被红红的辣椒所覆盖。辣椒并非果腹之食,而只是一种佐食的调料,但辣椒却能增添刺激、兴奋和热烈,给平淡的果腹之食带来浓烈的滋味。事实上,这个火红辣椒塞满整个院落并给人强烈视角冲击力的画面极具象征意义,颇能代表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性格——尽管自然环境严峻,却并不以果腹为终,仍然选择了充满着生命欢悦、爱的表达与美之渴求的喜庆、热烈、欢愉的生活。
同样让人深切体会到江三源地区人们生命态度及生命尊严的是一幅幅描绘当地葬礼的画。画面中透露出的肃穆与庄严,一张张凝重、哀伤的面容,凸显了生者对逝者的无限缅怀。但最让人感怀的是三江源地区藏族的天葬。天葬是体现藏族独特生命观的一种葬式。在藏族的生命观念中,同躯体相比,他们更看重人的灵魂,因而他们采取了让鹰鹫吃掉尸体,以此将死者的灵魂带到天上的独特葬式。这种葬式所蕴含的那种对生命的释然、洒脱与“天人合一”观念,不仅实现了“天”“人”之间的循环往复,也带来了人与当地自然环境的高度融洽。从地理条件讲,三江源高寒地带既无树木也缺乏石材,且冬季冻土也完全无法实施土葬。所以,就当地的自然环境来说,天葬不仅是最绿色、最与环境融洽的葬式,同时也可能是当地唯一和最合理的一种选择。当我们看到画册最后所展现的漫山遍野覆盖于天地之间并分别代表天、风、火、水、土五要素的蓝、白、红、绿、黄五色经幡迎风瓢动的壮美画面,我们不由得感叹人类文化之伟力。透过画册中一幅幅摄人心魄画面,我们看到,文化就这样因特殊自然环境应运而生,但又与自然环境高度融洽和匹配。这真是一种极高的生存智慧,也恰好印证了老子在数千年前说出的那句名言——“道法自然”。这一点可能正是三江源地区人们的“天地人生”及其文化生命力所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