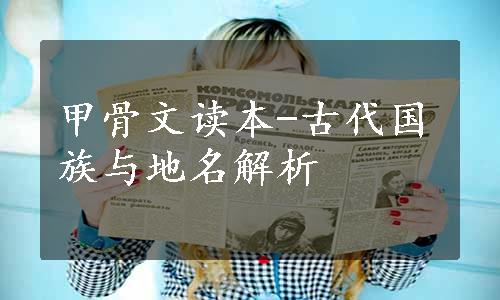
1.工方
【图版】
(1)
(2)
(3)
(4)
(5)
(6)
(7)
【释文】
(1)癸未卜, ……
……
癸巳卜, 贞:旬无忧。王占曰,有求(咎)[1],其有来艰[2]。气(迄)至[3]五日丁酉,允有来
贞:旬无忧。王占曰,有求(咎)[1],其有来艰[2]。气(迄)至[3]五日丁酉,允有来![]() 西。沚
西。沚 告曰,土方围(?)于我东鄙[4],
告曰,土方围(?)于我东鄙[4], [5]二邑。工方[6]亦侵我西鄙田。王占曰,有求(咎),其有来艰自西,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艰自西。
[5]二邑。工方[6]亦侵我西鄙田。王占曰,有求(咎),其有来艰自西,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艰自西。 友角[7]告曰,工方出,侵我示
友角[7]告曰,工方出,侵我示 田[8]七十五人。
田[8]七十五人。
癸卯卜, 贞:旬亡忧。王占曰,有求,其有来艰。五日丁未,允有来艰。饮[9]御自强圉[10],六月。
贞:旬亡忧。王占曰,有求,其有来艰。五日丁未,允有来艰。饮[9]御自强圉[10],六月。
…… ……
……
……五月。
(2)…… 贞:工方出,不隹(唯)我……
贞:工方出,不隹(唯)我……
壬子卜, 贞:工方出,隹(唯)我……
贞:工方出,隹(唯)我……
……争贞:沚 称册[11],王比[12]伐土方……
称册[11],王比[12]伐土方……
(3)……有异[13],吉,受又(祐)。其隹(唯)壬,不吉。
(4)癸酉卜,争贞:王 (勿)逆伐[14]工方,上下弗若[15],不我其受……
(勿)逆伐[14]工方,上下弗若[15],不我其受……
(5)□丑卜, 贞:令戉[16]来……戉罙伐[17]工方……七月。
贞:令戉[16]来……戉罙伐[17]工方……七月。
(6)丙辰卜, 贞:曰,工方以
贞:曰,工方以 方敦[18]吕,允……
方敦[18]吕,允……
(7)丁酉卜,亘贞:工 王事[19]。
王事[19]。
贞:王曰,工来。二告。
【著录】
(1)=《合集》6057正[31] (2)=《英藏》545正 (3)=《英藏》545反 (4)=《合集》6201 (5)=《合集》6379正 (6)=《合集》8610正 (7)=《合集》5445正
【注释】
[1]求:字形象一种多足虫,古称“蛷”。此处读为“咎”,表灾害之意。
[2]艰:危害。
[3]气:甲骨文写作上下两长横,中间一短横。此处读为“迄”,意思是终于、终究。“迄至某日”相当于说“后来到了某天”。从癸巳开始数,丁酉是第五天。另一条卜辞是癸卯日占卜,丁未是第五天。
[4]鄙:指边境城邑。《左传·隐公元年》郑国共叔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据杜预注,鄙即郑国边邑。
[5] :字形表示用戈勾取草木。学者释读为“捷”或“翦”,表攻取、俘获之意。
:字形表示用戈勾取草木。学者释读为“捷”或“翦”,表攻取、俘获之意。
[6]工:甲骨文作“ ”、“
”、“ ”,从工、从口。甲骨文字“从口与否每相通”,为行文便利,直接释写为“工”。[32]本版卜辞占卜西部边境会不会有麻烦。如癸巳日占卜,商王根据龟甲上的裂纹,判断西部将有不好的事发生。到第五天丁酉,西部“沚”地有人来报告,工方侵扰当地农田。工方的势力范围可能在今山西石楼、陕西绥德一带。或认为此字是羯鼓之侧视形,释为“曷”,读为“羯”。
”,从工、从口。甲骨文字“从口与否每相通”,为行文便利,直接释写为“工”。[32]本版卜辞占卜西部边境会不会有麻烦。如癸巳日占卜,商王根据龟甲上的裂纹,判断西部将有不好的事发生。到第五天丁酉,西部“沚”地有人来报告,工方侵扰当地农田。工方的势力范围可能在今山西石楼、陕西绥德一带。或认为此字是羯鼓之侧视形,释为“曷”,读为“羯”。
[7] :商王朝西北方的古代国族。就字形而言,音符是
:商王朝西北方的古代国族。就字形而言,音符是![]() (延展阅读B、C),甲骨文写作
(延展阅读B、C),甲骨文写作![]() ,西周金文写作“
,西周金文写作“ ”。在此读为“徵”(和澄清的“澄”读音相同),今陕西澄城一带。汉代以前称“徵”,例见《左传·文公十年》、《史记·河渠书》等。
”。在此读为“徵”(和澄清的“澄”读音相同),今陕西澄城一带。汉代以前称“徵”,例见《左传·文公十年》、《史记·河渠书》等。
[8]示 田:指“示
田:指“示 ”这地方或“示”、“
”这地方或“示”、“ ”两处的农田。《合集》6063反有地名或国族名“示”,或读为“祁”,隶今山西晋中市。
”两处的农田。《合集》6063反有地名或国族名“示”,或读为“祁”,隶今山西晋中市。
[9]饮:人从酒器中饮酒的表意字。
[10]自强圉:强,此处是地名。圉,此处可能指受到监禁的人。“圉”字所从的“ ”,象一种枷锁,在卜辞中有钳制、胁迫、夹击等意思。后面残辞有“
”,象一种枷锁,在卜辞中有钳制、胁迫、夹击等意思。后面残辞有“ ”字,很可能就是对工方进行夹击的意思。此处辞意不太清晰,或认为“自”字之前有缺字。
”字,很可能就是对工方进行夹击的意思。此处辞意不太清晰,或认为“自”字之前有缺字。
[11]称册:或认为是双手举册,接受册命之意。或认为是称述、传达商王之命令。
[12]比:协同作战(参看本章“妇好”条)。
[13]异:字形表示以手持槌敲打橛杙。甲骨文中多读作奇异的“异”。作名词时,指不同寻常的情况、景象等。
[14]逆伐:迎击。《孙子兵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杜牧注:“敌在高处,不可仰攻;敌倚邱山下来求战,不可迎之。”或理解为阻击。《周礼·夏官·田仆》“设驱逆之车”,郑玄注:“逆,衙还之,使不出围。”围指猎场,打猎时有专人负责拦截那些试图逃出狩猎范围的猎物。“衙”是“御”的通假字,表示拦截、阻击。
[15]上下弗若:上下,代指天地神明。《书·召诰》:“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孔颖达正义:“举天地则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若”字作“ ”、“
”、“ ”,象一人理顺头发,此处表顺利之意。卜辞之意,工方来侵,但商王不宜亲自出战,因为得不到天地神明保护。商王出战,对我方没有好处。
”,象一人理顺头发,此处表顺利之意。卜辞之意,工方来侵,但商王不宜亲自出战,因为得不到天地神明保护。商王出战,对我方没有好处。
[16]戉:象斧钺之形。这里是一个方国名,曾遭工方入侵(如《合集》6373)。此处可见商王朝联合戉的力量一起伐工方。
[17]罙:写作“ ”、“
”、“ ”,表示手探入容器底部取物。在和战争有关的卜辞中的“罙”,有学者读为“探”,探伐是试探性地攻击;也有学者读为“深”,深伐是深入敌方阵地作战。
”,表示手探入容器底部取物。在和战争有关的卜辞中的“罙”,有学者读为“探”,探伐是试探性地攻击;也有学者读为“深”,深伐是深入敌方阵地作战。
[18]敦:挞伐之意。卜辞说,工方调动 方的力量攻打吕地。辞中“以”字可以理解为“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传:“凡师,能左右之,曰‘以’。”工方能左右
方的力量攻打吕地。辞中“以”字可以理解为“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传:“凡师,能左右之,曰‘以’。”工方能左右 方的兵力,可见工方势力极强,凌驾于一般方国之上。
方的兵力,可见工方势力极强,凌驾于一般方国之上。 具体地望不明,其字形,是“鬲”的象形文中有“辰”,读音大概和“辰”相近。
具体地望不明,其字形,是“鬲”的象形文中有“辰”,读音大概和“辰”相近。
[19]卜辞之意,商王占卜说,有事要处理,工方代表会来协助。[33]
【延展阅读】
武丁在位某年五月的一天,商王命 例行占卜,看未来十天内边疆是否平安无事。商王根据龟甲上显示的裂纹,认为西方将有不祥之事。第五天,西部沚、长两地相继有人来报告工方入侵(《合集》6057正),这无疑是对商王朝主权的挑衅。
例行占卜,看未来十天内边疆是否平安无事。商王根据龟甲上显示的裂纹,认为西方将有不祥之事。第五天,西部沚、长两地相继有人来报告工方入侵(《合集》6057正),这无疑是对商王朝主权的挑衅。
沚原来是商王国西部的敌对国(如《屯南》4090称之为“沚方”,曾是个独立方国),后表示臣服。商王曾派人去当地镇抚(如《合集》175),也曾到该地行猎(如《合集》9572)。武丁在位时,该国有位名“ ”的人在商王朝做官,地位较显赫,《合集》5945称之为“伯
”的人在商王朝做官,地位较显赫,《合集》5945称之为“伯 ”(花东卜辞的“伯戓”,裘锡圭先生认为是“伯
”(花东卜辞的“伯戓”,裘锡圭先生认为是“伯 ”,也就是“沚
”,也就是“沚 ”),表明其身份是诸侯。甲骨文中涉及沚
”),表明其身份是诸侯。甲骨文中涉及沚 的卜辞超过300版。他曾经参加祭祀商先王太甲的活动,并在祭祀典礼中“称册”(《合集》6087正、6134等)。可以说“沚”是商朝西部防卫工方等势力的一道屏障。犹如晚商时代的“崇”,是防范关中周人势力的屏障。沚地遭工方侵扰,商王势必要有所行动。
的卜辞超过300版。他曾经参加祭祀商先王太甲的活动,并在祭祀典礼中“称册”(《合集》6087正、6134等)。可以说“沚”是商朝西部防卫工方等势力的一道屏障。犹如晚商时代的“崇”,是防范关中周人势力的屏障。沚地遭工方侵扰,商王势必要有所行动。
商王朝先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工方挑起战争的不恰当行为。《合集》6160说沚 称册“
称册“ 工方”(A),“
工方”(A),“ ”字罗振玉先生释读为“
”字罗振玉先生释读为“ ”。《说文》:“
”。《说文》:“ ,告也。”何琳仪、黄锡全先生认为是“册”的分化字,并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说法:“简牍曰册,以简告诫曰
,告也。”何琳仪、黄锡全先生认为是“册”的分化字,并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说法:“简牍曰册,以简告诫曰 。”于省吾先生读“
。”于省吾先生读“ ”为“刊”,有砍杀之意。李学勤先生认为,卜辞说
”为“刊”,有砍杀之意。李学勤先生认为,卜辞说 某方国,就是宣告某方的罪责。“
某方国,就是宣告某方的罪责。“ 工方”就是发表声明谴责工方。亦即《国语》祭公谋父所言“文告之辞”。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派遣朝中将领“以众伐工(方)”(如《合集》26、28等)。
工方”就是发表声明谴责工方。亦即《国语》祭公谋父所言“文告之辞”。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派遣朝中将领“以众伐工(方)”(如《合集》26、28等)。
(A)
(B)
(C)
工方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武器装备很不错,青铜质地的头盔、兵器都已齐备。山西柳林曾出土青铜头盔、矛、斧和钺(图D、E、F[34]),李伯谦先生把这一批青铜器归为石楼—绥德铜器群B类,并认为是工方遗物。
(D)
(E)
(F)
知己知彼,是作战要点。甲骨文中常常见到商王命人侦察敌情,也许还有专门的侦察机构。当时有人对敌方进行“目”(《合集》6194)、“视”(《合集》6167)、“望”(《合集》6189)的活动,大概都是侦察、刺探其活动规律、行进路线、作战计划等。笼统而言,目、视、望词义相通。区别而言,“目”为注视,相当于今天说的“盯住”;“视”有观察、察看之意;“望”有刺探之意。所获情报会及时反馈给商王。有时是一般性的内容,报告工方“出”;有时是“大出”或“亦出”(如《合集》6118,关于“亦出”,胡厚宣先生说是大举出动或夜晚出动);此外还会跟踪报告其所到之处,如“工方至于原”(《合集》6128)、“至于臿”(《合集》6131正)等。
为获神明保佑,商王还向他们汇报工方的动向。例如《合集》6131正就有“告工方于示壬”、“上甲”两位先公先王的刻辞。每次敌军入侵,派何人出征应战,也需慎重选择,有时商王会御驾亲征(《合集》6096正:“工方出,王自征。”)。
关于作战方式,缺乏详细资料。卜辞有时仅说“伐”,有时说“步伐”(如《合集》6292),胡厚宣先生说是步兵作战。学者一般认为,商王朝的车兵到武丁时才逐渐出现,廪辛、康丁以后才成规模。“步伐”就是“伐”。商朝军队编制及规模,甲骨文所见至少有三“师”、“旅”等,如:
(G局部)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
(H)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
(G)
(G局部)
(H)
例(G)是《合集》33006,辞中有左、中、右三个师。占卜说商王命三师开拔(该例是武乙时期的卜辞,也有学者认为“作”是创建)。例(H)辞中“登”(征用)的战士,就有一万三千人,这条卜辞不完整,征讨对象不详。旅是商朝的一种军事编制,但各“师”、“旅”具体人数不详。例(H)辞中有一万人来源于“旅”,恐怕还只是王朝军队的冰山一角。
商王朝作战时还扶植、联络西部其他方国。这些方国大概也饱受工方入侵之苦,例如“ ”,《合集》8529记工方进攻“
”,《合集》8529记工方进攻“ ”,《合集》3327记商王“比
”,《合集》3327记商王“比 侯”,即联合该方国迎战。
侯”,即联合该方国迎战。
学者认为,从甲骨文看,经过长期征战,到武丁晚期,工方的威胁已基本解除。
2.土方
【图版】
(1)
(1局部)
(2)
(3)
【释文】
(1局部)王占曰,有求(咎),其有来艰,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艰自北。 妻竹[1]告曰,土方[2]侵我田。十人。
妻竹[1]告曰,土方[2]侵我田。十人。
(2)丁酉卜, 贞:今早[3]王廾(供)人五千正(征)土方,受
贞:今早[3]王廾(供)人五千正(征)土方,受 (有)又(祐)。三月。
(有)又(祐)。三月。
(3)……戊辰卜, 贞:王循土方。[35]……
贞:王循土方。[35]……
【著录】
(1)=《合集》6057正、反 (2)=《合集》6409 (3)=《合集》559正
【注释】
[1] 妻竹:第一字是甲骨文中的地名。竹是商王朝北方方国,或认为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到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这一区域。妻,在这理解为“配偶”。指出嫁到
妻竹:第一字是甲骨文中的地名。竹是商王朝北方方国,或认为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到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这一区域。妻,在这理解为“配偶”。指出嫁到 地的竹国之女。
地的竹国之女。
[2]土方:商王朝北部的强大国族。例(1),占卜预测有从北方来的灾难,结果就是土方入侵。第二例可见,商王朝曾经征用五千人的兵力和土方作战。经过征伐,土方后来一度臣服于商王朝。第三例表明,武丁可以到土方势力范围内巡行视察。
[3]早:字形从![]() ,是草的象形文,在甲骨文中作时间名词时,读为“早”。花东卜辞有时间名词“
,是草的象形文,在甲骨文中作时间名词时,读为“早”。花东卜辞有时间名词“ ”,也读为“蚤”,早、蚤通用。古人作战常在早晨。周武王灭商,《尚书·牧誓》及青铜器铭文都说是“甲子昧爽”,也就是甲子这天的早晨。(www.zuozong.com)
”,也读为“蚤”,早、蚤通用。古人作战常在早晨。周武王灭商,《尚书·牧誓》及青铜器铭文都说是“甲子昧爽”,也就是甲子这天的早晨。(www.zuozong.com)
【延展阅读】
兵者,不祥之器。但战争一旦爆发,如果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就只能处于被动。下面简单举例说说甲骨文时代的兵器。
戈。甲骨文中从“戈”的字较多,武力的“武”即从“戈”。甲骨文作![]() ,金文有
,金文有![]() ,更具象形意味。字形中上端的横画表示戈头,其它笔画包括了戈柄
,更具象形意味。字形中上端的横画表示戈头,其它笔画包括了戈柄 、彤沙等部件。“戈”字除去戈头的部分,甲骨文写作
、彤沙等部件。“戈”字除去戈头的部分,甲骨文写作![]() ,表示戈柄,也就是后世所谓“柲”。在柲上安装大斧是“钺”字“
,表示戈柄,也就是后世所谓“柲”。在柲上安装大斧是“钺”字“ ”;安装锯子是“我”字“
”;安装锯子是“我”字“ ”、“
”、“ ”。据学者统计,商代出土的格斗兵器中,戈数量最多。如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119件,妇好墓出土91件。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小屯北地F10:3发掘到一件用蚌壳制作的戈(下图A1、A2),戈头与柲绑缚在一起,[36]前锋折断,残长3厘米;戈柄作棍状,下端呈锥形,可能有
”。据学者统计,商代出土的格斗兵器中,戈数量最多。如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119件,妇好墓出土91件。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小屯北地F10:3发掘到一件用蚌壳制作的戈(下图A1、A2),戈头与柲绑缚在一起,[36]前锋折断,残长3厘米;戈柄作棍状,下端呈锥形,可能有 ,全长7.7厘米。学者据此分析,商代戈的安装方法是:在柄的上端凿长孔,孔下刻浅槽,将内插入孔中,再把下阑嵌进槽内。使用时,戈可以直接敲击敌人的身体,这种方式称为“啄”(例B,字一般释为“伐”);也可以像使用钩子一样,用下刃及胡部割伤对手,这种方式称为“钩”。因此戈又被称为钩兵(勾兵)或啄兵。
,全长7.7厘米。学者据此分析,商代戈的安装方法是:在柄的上端凿长孔,孔下刻浅槽,将内插入孔中,再把下阑嵌进槽内。使用时,戈可以直接敲击敌人的身体,这种方式称为“啄”(例B,字一般释为“伐”);也可以像使用钩子一样,用下刃及胡部割伤对手,这种方式称为“钩”。因此戈又被称为钩兵(勾兵)或啄兵。
(A1)
(A2)
(B)
弓箭。弓箭是远距离杀伤性武器。1963年,在山西朔州峙峪村旧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石质箭镞,距今已有28 000年左右。[37]弓由弓背、弓弦两大部分构成。弓背中央握持之处称为“弣”,俗称为“弓把”。两端系弦处称为“箫”,或称“弭”,多是骨、角质。从弣到萧这一段弓体叫做“渊”。古籍写作“ ”。
”。 的中央叫做“隈”,古籍又写作“威”。
的中央叫做“隈”,古籍又写作“威”。
“箭”古称“矢”。箭头部分称为“镞”,古代又称“镝”。考古发掘尚未见完好的箭杆,箭镞则较常见,仅殷墟王陵区M1001就曾出土6 583枚。据研究,商代的箭镞多数是骨质。郑州商城城郊的一个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出土过一批骨箭镞,经鉴定,半数以上是用人的肋骨和肢骨制成的。盛箭的容器古称“箙”,又称“矢箙”,字形作“ ”(《集成》846),表示容器内盛放箭矢,古书作“备〔備〕”。殷墟西区车马坑M43出土过一件,整体呈圆筒形,底部平整,内有10枚箭镞,箭头向下定在箙底。当时应是箭镞向下存放在箙内,可惜箭杆已经腐朽。
”(《集成》846),表示容器内盛放箭矢,古书作“备〔備〕”。殷墟西区车马坑M43出土过一件,整体呈圆筒形,底部平整,内有10枚箭镞,箭头向下定在箙底。当时应是箭镞向下存放在箙内,可惜箭杆已经腐朽。
干盾。干盾属于典型的防御性装备。商代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都有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牌的字形,如《合集》7768“ ”。甲骨文中“干”字作“
”。甲骨文中“干”字作“ ”,上部为装饰物,中间为盾牌,下端是
”,上部为装饰物,中间为盾牌,下端是 (用来把盾牌树立在地面上的尖锥),简化作“
(用来把盾牌树立在地面上的尖锥),简化作“ ”。盾牌的象形初文写作“
”。盾牌的象形初文写作“ ”,简化作“
”,简化作“ ”、“
”、“ ”。甲骨文有“戎”字,是戈和盾放在一起,如“
”。甲骨文有“戎”字,是戈和盾放在一起,如“ ”、“
”、“ ”、“
”、“ ”,其中“盾”部分的演变轨迹,和“干”字中“盾”的部分以及独体的“盾”字演变轨迹相似。
”,其中“盾”部分的演变轨迹,和“干”字中“盾”的部分以及独体的“盾”字演变轨迹相似。
甲胄。甲胄用于防身,也是常见武器装备。甲,《广雅》:“铠也。”现代习称“铠甲”。《说文》冃部:“胄,兜鍪也。”现习称“头盔”。甲胄有用皮革或金属制作的。皮质的甲不易保存,但考古工作者曾在殷墟发现皮甲彩绘漆纹留在泥土上的印痕,研究者推测是一块胸甲,保护胸腹部及两肋。头盔以皮质的为多,青铜质地的商代头盔也有多例标本。除殷墟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北京房山琉璃河、内蒙古赤峰美丽河、辽宁锦西乌金塘、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地的商周墓葬中都出土过青铜头盔。头盔的顶部有一个竖直向上的空管,用来插羽毛等装饰物。山西的考古工作者也在当地商代墓葬中发现了头盔,研究者认为属于西北游牧民族遗物。下图(D)是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头盔,[38]图(E)是学者据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复原的甲胄。[39]
(D)
(E)
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人头骨标本中,有几具颅骨上有圆形穿孔,不排除是戈、矛类兵器留下的创口。汉画像石中的“胡汉交战图”再现冷兵器时代作战情景。如下图,[40]画面最右侧是一个胡人骑兵,他被身后赶来的汉兵用戈头勾住而失去重心,身体向后仰,手中的弓箭也已脱落。后面还有一个汉兵张弓搭箭直奔而来。这个胡人骑兵必死无疑。
和平是大家所期待的。但人类发展到现在的历史阶段,以为从此再不会有战争,多少也有点一厢情愿。
礼仪性的武器,这里以钺为例。
钺,古人说是“大斧”。《说文》:“戉,斧也。”《广韵》引《说文》:“戉,大斧也。”《书·牧誓》陆德明音义:“钺音越,本又作戉。”汉代以后的训诂学资料中,斧和钺已经混而为一。例如《文选》李善注引用当时能见到的一些训诂学者意见说:“斧,钺也。”斧钺本身可以用于砍杀(F,斧头之下的人脑袋已经被砍掉,《集成》1011)。商代钺的实物(G,藁城台西遗址出土),如殷墟妇好墓发掘获得的两件青铜钺,一件长39.3厘米、刃部宽37.3厘米,重8.5公斤,器身接近肩部的位置,以雷纹为地,衬托两虎扑向一个人头的纹样(H);另一件长39.5厘米、刃部宽37.5厘米,重9公斤,器身接近肩部的位置,也是雷纹为地,衬托龙形纹样。两件青铜钺肩部纹样的下方和刃部之间,靠近纹样的位置铸有“妇好”铭文。
(F)
(G)
(H)
斧钺象征着权力,既可以用来代表王权,还可以用来施加惩罚。有名的虢季子白盘铭文就说:“赐用钺,用征蛮方。”虢季子得到周王赏赐的钺,相当于代表周王,专行征伐。
3.羌方
【图版】
(1)
(1局部)
(2)
【释文】
(1局部)其呼戍[1]御羌方于义 [2]
[2] 羌方,不丧众[3]。
羌方,不丧众[3]。
于泞,帝乎御羌方,于之 [4]。
[4]。
……其大出。
(2)贞 [5]不其获羌。
[5]不其获羌。
【著录】
(1)=《合集》27972 (2)=《合集》188正
【注释】
[1]戍:古文字象有人有兵戈,会戍守之意。这里指戍守的人。
[2]御:阻击、拦截。卜辞说,商王命守军在“义 ”这个地拦截羌方,会俘获羌方的人,而我方没有人员伤亡。
”这个地拦截羌方,会俘获羌方的人,而我方没有人员伤亡。
[3]丧:损失。众:商朝自己的军队。
[4]占卜认为,在“泞”这个地方能够俘获羌方。甲骨文的“泞”,学者认为或是古代荥泽附近,今河南修武一带。
[5] :商王朝西部的方国,与商王朝时战时和。学者或释“敖”。或释“失”,并认为甲骨文“失侯”(《合集》10923)即《逸周书·世俘》之“佚侯”,活动范围在今河南洛阳一带。
:商王朝西部的方国,与商王朝时战时和。学者或释“敖”。或释“失”,并认为甲骨文“失侯”(《合集》10923)即《逸周书·世俘》之“佚侯”,活动范围在今河南洛阳一带。
【延展阅读】
羌,在卜辞中多是一个泛称,即后来所谓的“东夷、西羌、南蛮、北狄”中的“羌”,统称在汉民族政权以西的异族。古籍中有“姜氏之戎”,沈长云先生以为就是古代的羌族。而“羌方”则专指商王朝西边的一个方国,和前面介绍的工、沚等方国一样,商人和羌人作战所动用的兵员数量极多,用羌人作牺牲,也格外常见。数量多时用到三百个羌人。
陈梦家先生已经指出:“关于卜辞用人牲祭先王的记载,应和安阳西北岗陵墓附近的成排的与零散的小墓相联系,这些小墓当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后杀用了的人牲。”他实际是说西北岗那些小墓中埋葬的人牲中必有大量的羌人。
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人头骨标本有398个,绝大部分出自商王大墓旁边的人头坑或小型墓葬(据标本上的出土标签判定,有337个均出自西北岗东区三座大墓西侧的99座小墓,所谓小墓,有86个实际是“人头坑”),主要当是用于殉葬。这些人头骨的来源,杨希枚先生曾提出三种可能:
(1)殷王朝对外征战时俘获的异国族属,或竟从战场携回的敌首。凯旋归来,告捷于先王,因用以殉葬,并耀示武功。如果是俘虏,则可能是戮于宗庙或王墓之前,再分其头体而葬之。(2)殷王朝治下的罪犯或奴属,而后者中当可包括异国的俘虏。(3)殷先王生前宠幸的陪臣,甚或宗属。就一般伦理观念而言,当以前两种情形最为可能。
和陈梦家先生的结论差不多,倾向认为西北岗人头坑和小墓中的头骨可能本是羌人首级。
杨希枚先生认为西北岗这些人头坑中的头骨,和另外那些无头人骨坑中的体骨有相应关系。这很有道理。虽然把这些头骨还原到相应的体骨上不易操作,但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西北岗的这些头骨很可能是就地砍下来的人头,而非从战场拖运而来。
作战时肯定不方便取敌人首级。就商代武器装备而言,就可看出在战场上获得首级所面临的技术困难。一方面,当时作战所使用的格斗兵器主要是戈、矛,而割取首级应用刀剑。作战过程中显然很难停下来更换武器去取首级。另一方面,战士穿甲带盔,需要除去这层保护,才能较便利地割下首级。而且,和火器时代的战斗相比,冷兵器不易一击致命,负伤的人不会安静地躺在地上等着被斩首,而会挣扎求生甚至反击杀死对方。这都增加了交战过程中斩首的难度。
首级并非总是被胜利者带走,因其并非便于携带之物。宋代有名的“万人敌”李显忠,少年时代追随父亲作战,以一人之力杀敌十七,“取首级二”而返。事见《宋史》本传。正因为战场上的首级不是悉数作为战利品带回,所以引发了虚报战功的案例。《晋书·王濬传》记载,西晋灭吴时,周浚击败吴国张悌,斩首二千,虚报一万,后来又派吴刚到洛阳,想偷偷修改战报。事发之后要追查实际战果,王濬建议说,吴主孙皓已经投降,张悌有多少兵员,可向孙皓查证。当时或许根本没有带回首级。否则又何必去问孙皓?此外,也可能按法律规定不得带回敌人首级。在可以用首级换爵位的秦国,就有明文规定,敌军首级可换爵位,但达到大夫级别后,不允许再带敌人的首级回来。《商君书·境内》:“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简7:“故大夫斩首,迁。”本身已是大夫却在阵前斩取敌人首级拿回来邀功的,一律流放到边境地区。
带回敌方首级,还要防备其他没有获得首级的人来抢夺。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31—33是一份爰书,根据战士甲的描述可知,案件发生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6年)秦军攻占邢丘之后。战士甲目击战士丙用剑刺伤战士丁,夺取丁所获的一枚首级。
就整个战争的胜负而言,有价值的只能是那些具有一定身份的、最好就是敌对方首领的头颅。传统小说中经常写“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我刀下不斩无名之将”等说词,就含有这种确定身份的意图。《两汉书》中,有时也通过记录斩获单于首级宣示对匈奴作战的成功。而战败之际,地位较高的人也会想如何避免自己的首级落入对方手中。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述吴楚之战,楚方左司马戌在雍澨与吴方交战时受伤。因为他曾高调地和吴王打过交道,无论如何也不想成为吴王的俘虏。他自度没有生还的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让随从带走自己的首级。于是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割下司马的头然后用衣襟包裹,藏好司马的身躯,将其首级带离战场)。[41]
首级落入敌手,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战国策·赵策》曾说,韩、魏、赵联手灭知氏,赵襄子和知伯怨仇最深,所以他拿知伯的人头“为饮器”。后来《史记·大宛列传》写匈奴攻破大月氏,也用月氏王的头“为饮器”。什么是“为饮器”?或说是用头骨来喝酒,或说是用来接便溺。还有被放到蒸锅里蒸煮的。1999年,安阳刘家庄M1046出土一件铜甗,内盛人头骨一具,或者就是某异族首领的项上人头。这件装着头骨的铜甗现陈列在殷墟博物苑(A[42])。至于成批战俘的首级,处理就相对粗糙。据考古工作者介绍,西北岗出土的这些头骨,还有不少能看到比较整齐的刀砍痕迹(B[43])——割首并非总是照着脖子砍,从图片看,当时显然是胡乱一刀,从脸部砍下去的。
(A)
(B)
4.人方
【图版】
(1)
(1局部)
(2)
(3)
(3局部)
(3局部摹本)
(4)
【释文】
(1局部)乙卯卜,贞:王其正(征)人(夷)方[1]。亡(无)(灾)。
(2)癸亥王卜,贞:旬亡忧。在九月。王正(征)人方,在雇[2]。
(3)丁巳王卜,贞: 巫九
巫九 [3],
[3], 人方率伐东或东[4],典东侯
人方率伐东或东[4],典东侯 人方[5],妥(绥)余一[人[6]。余]其比多侯,亡左自上下于
人方[5],妥(绥)余一[人[6]。余]其比多侯,亡左自上下于 示。[44]余受有佑。王占曰:大吉。……彡……王彝在……宗。
示。[44]余受有佑。王占曰:大吉。……彡……王彝在……宗。
(4)……人(夷)方伯[7]……祖乙伐……
【著录】
(1)=《屯南》2370 (2)=《合集》36485 (3)=《合集》36128、《新发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45] (4)=《合集》38758
【注释】
[1]人:读为“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夷方,包括周代所称的东夷和淮夷。
[2]雇:地名。夏商之际有古国名“雇”,被商汤征服。《诗经·商颂·长发》:“韦雇既伐,昆吾夏桀。”该古国的地理位置,传统上认为在今河南范县一带。甲骨文的“雇”作地名,是商朝征伐东夷路线上的地名,学者以为在今河南原阳县一带。
[3]此四字词义不明,可能是占卜仪式中的习惯用语。
[4]或:学者或读为“国”,或读为“域”。国、域两个词音义都很近,例如《周礼》“山国”、“土国”、“泽国”,“国”都是“地域”的意思。此处“东或”是指商王朝东部疆域。![]() 字不识。或释“禺”,读为“遇”,适逢之意。率:猛然。卜辞说,现在夷方攻打我东部各诸侯国的东边。
字不识。或释“禺”,读为“遇”,适逢之意。率:猛然。卜辞说,现在夷方攻打我东部各诸侯国的东边。
[5]典:《广雅》:“主也。”典东侯,指商王作为主帅带领东国诸侯的部队,去和东夷作战。 :谴责(参看本章“工方”条)。
:谴责(参看本章“工方”条)。
[6]绥:使之安宁、安定。《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余一人:帝王自称。《国语·周语上》:“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韦昭注:“天子自称曰‘余一人’。”
[7]夷方伯:夷方的首领。伯,《说文》:“长也。”“伐”是砍下用作牺牲的人头来祭祀。这条写在人头骨上的刻辞大致是说,用夷人首领的人头来祭祀祖乙。
【延展阅读】
《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纣王忙于和东方的夷人作战,虽然暂时打赢了,却输掉了自家的王朝。
夏商周三代,东方夷人地位十分特殊。例如,夏王朝的劲敌“后羿”、“寒浞”都是东夷人。后羿一度“因夏民以代夏政”。夏朝末年,“诸夷内侵”(《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是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商人灭夏的动向是自东向西,因而有学者认为,夏桀最后很可能是往西北逃,最终死于今中条山一带。[46]
商纣王征伐夷方,甲骨文有不少资料,根据那些时间、地点,学者复原了“征夷方路线”。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殷墟卜辞研究》(1957年出版)书中所附如下征夷方地图,眉目清晰。图中左侧出发点是“殷都”;右上方“ ”,郭沫若先生释“齐”,指今山东临淄;右下方的“
”,郭沫若先生释“齐”,指今山东临淄;右下方的“
 ”释为“林方”,仅仅说是淮夷,没有说具体地点,从地图上看大致是今江苏泰州一带。由于甲骨文中的很多地名都不能落实(有的文字尚且不能释读),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释为“林方”,仅仅说是淮夷,没有说具体地点,从地图上看大致是今江苏泰州一带。由于甲骨文中的很多地名都不能落实(有的文字尚且不能释读),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如果夏人和东夷的冲突只是传世文献的“故事”,那么商人和东夷的不良关系,从传世文献和甲骨文来看都比较明朗。商朝和东夷的战争时间长,规模也不会小——商王御驾亲征,不可能孤军冒险。上揭(4)直接刻在人的头骨上。从刻辞内容看,这是一位东夷军事头领的项上人头(参看第四章“洹”条)。
据统计,人头骨刻辞现已知有15片,北京图书馆藏有7片,其拓片著录如《合集》38761、38762、28759等。故宫博物院(拓片著录为《合集》3875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拓片著录为《合集》38760)、上海博物馆(拓片著录为《合集》3876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拓片著录为《合集》27741)、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拓片著录为《怀特》1914)、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各有一件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系河井荃庐旧藏,原有两片,另一片原物下落不明,拓片著录为《合集》38763。有刻辞的头骨无一完整,大概在当时被有意敲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