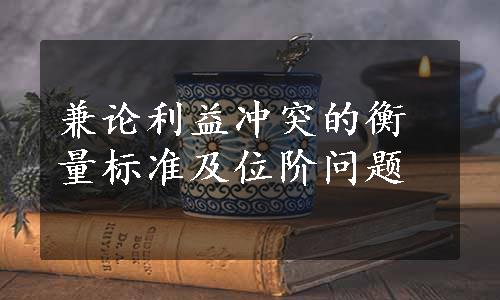
本书研究所有权限制是以利益评价为基点的,如前所述,所有权和其他权利一样本质上是由利益构成,而所有权限制实质是利益冲突的安排。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利益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率的捷径无疑是列出利益谱系,画出权利的完整位阶或利益谱系,优位利益、低位利益逐一据权重顺序罗列,当出现权利(利益)冲突时一查该谱系则孰先孰后分秒立见,犹如做加减算术题那么简单。[6]尽管权利(利益)位阶的理念也得到相当多数学者的认同,[7]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一般而言生命权要优于身体权和健康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优于财产权,[8]然而,任何权利(利益)之间存在绝对优先序位的这种想法是将复杂事务过于简单化处理了,注定只能是臆想,本书认为,权利(利益)之间尽管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固定的,也不是可以事先预设的。
首先,权利(利益)谱系是无法列出的。在公法领域,列出权力清单尚属难事,更何况在“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的私法领域,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外,还有大量难以类型化的权利存在,如自然权利、推定权利、道德权利等,权利的这种复杂形态注定谱系中被列举的权利范围不可能是周延、完整、确定的。其次,更难达成的是排序本身,理论上虽有基数排序(cardinal ranking)和序数排序(ordinal ranking)两种可能的方式,却都是不够现实的。基数排列是给每个权利一个数值(0~1之间)来代表它在权利谱系中的重要性或等级,数值一旦确定则高数值的权利于低数值的权利而言有绝对优先性,而一旦某个权利的数值确定,比如在所有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设所有权为0.5,隐私权为0.6,在个案看来,商业大厦的玻璃墙上暴露对面居民楼居民生活细节这样的隐私内容的情况确实非常好解决,隐私权因数值更高而轻松胜出,然而,这样专横的价值判断的结果是隐私权和所有权只要发生冲突,隐私权每每必胜,哪怕对隐私权极小的一点伤害而所有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情形下也是如此,数值高的权利无论何时都要得到最高的保护,最后就会造成明显失衡的结果。序数排列比基数排列绝对性要求更低,是通过比较一对或多个权利来确定相对的优先性,权利的序数排列也与基数排列有着同样的问题,将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后会造成僵化的应用,不符合现实正义的要求。基于这两点理由,完整、绝对、呈凝固状的金字塔形态的谱系是不可能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涉及复杂的价值判断问题。而这些并不是作为方法论的利益位阶单独就能解决的。因此,利益谱系或位阶属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领域,是一个永恒的法律哲学的难题,所谓的利益层次不过是存在和依附于“基本权利华丽外表”(panoply of basic rights)之下的美好幻想。[9](www.zuozong.com)
尽管我们不能从权利或利益本身推导出确定的“事先限制”排序结果,但是法官还是可以在充分考虑地缘、时间和个案上的动态差异的前提下,逐案进行处理,这正如霍姆斯所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平衡的边界并不能事先通过某个普遍适用的公式来决定。但是这条界线上的各个点,或者说建立这条边界的手段,则是由处于这条界线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案件判决所固定下来的。”[10]霍姆斯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也提醒了我们“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理论上无法证成的不代表现实中就无解,霍姆斯这句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法律条文本身已是立法者某种价值判断后的结果(end result),法律的本质是法律共同体在相互对且均被承认的利益中,通过事实和经验的汇集而作出的价值判断。既然立法者在制定规范之时就已经考虑过每一规范中所涉及的利益,也就是说,立法者在立法之时已经做出过利益冲突的判断,决定了赋予价值的利益及牺牲的利益。[11]那么,立法者这样判断的逻辑可以被法官提炼出来,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再次被利用,在法律解释中进行符合法治精神的逻辑推理。诚如利益法学之父赫克所言,法律解释的基线是“法官应受制定法的拘束”,法官应为立法者的“仆人”,但法官不应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考虑到“法律的精神与意义”,为主人利益状态“设身处地地思考”地“思考式服从”,要“评价地形成诫命”。[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