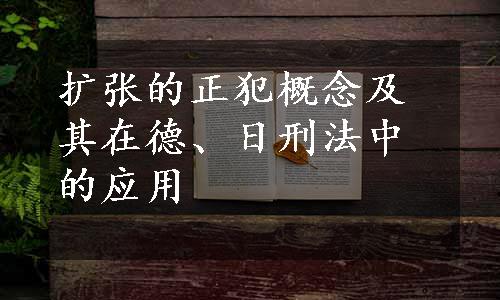
一、正犯的概念和种类
(一) 正犯的概念
1. 正犯的定义。犯罪行为,根据其主体在实施犯罪中的作用,可以分为正犯与共犯两种形态。什么是正犯呢? 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李斯特指出: “通过实现构成要件而破坏或危害法益的是正犯。”[1]日本学者山中敬一认为: “所谓正犯 (Täterschaft),指行为人自己充足构成要件要素的场合。换言之,自己实现刑法分则中记述的‘实施……的’之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的,是正犯者 (Täter)。”[2]在德、日等国刑法中的正犯,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刑法中均称为实行犯。俄罗斯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等写道: “直接实施犯罪的人,即实际完成刑法典分则规定的作为某一犯罪要件的行为的人,是实行犯。”[3]
2. 扩张的正犯概念与限制的正犯概念。扩张的正犯概念,在德、日刑法理论中也称为统一的正犯概念。德国学者耶赛克说: “统一的正犯概念,将在构成要件的实现上起原因作用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是正犯。在全体的现象中该人的协力给予怎样的意义不加考虑。”[4]通常认为,意大利刑法典第110条、1968年奥地利刑法典草案第11条等是采取统一的正犯概念的立法。根据限制的正犯概念,“正犯只是亲自实行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人,仅仅通过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惹起结果,不能给正犯奠定基础”[5]。教唆犯或帮助犯是刑法设定特别的共犯形态,意味着将可罚性扩张到相当于构成要件之外的行为。德国刑法典第25~27条,瑞士刑法典第24条、第25条,日本刑法第60~64条等被认为是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的立法。根据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我们认为限制的正犯概念为可取。
(二) 正犯的种类
正犯,用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李斯特认为: “这里主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 1. 正犯首先是指单独违法地且有责地实施了实行行为,单独实行构成要件之犯罪人 (单独正犯) ……2. 正犯还指虽非因行为人自身的行为,而是通过其他人 (甚至是被害人自己) 而实现构成要件之人 (间接正犯)。”[6]日本学者内田文昭指出:“正犯以直接单独正犯为基本型,可能采取种种形态。例如,单独并且以自己之手实行杀人者,成为杀人罪的直接单独正犯,由于以他人为工具而利用之实行杀人者,称为杀人罪的间接 (单独) 正犯; 数人共同实行杀人的场合,能够称为 (直接) 共同正犯,如果数人共同间接实行杀人,就称为杀人罪的间接共同正犯。进而在与间接正犯的关系上,能承认称为自手犯的正犯形态,在与共同正犯的关系上,能承认称为同时犯的形态。”[7]综上所述,正犯的种类,基本上可以正犯的人数为标准,分为单独正犯与共同正犯; 以是否直接实行犯罪为标准,分为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
二、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区别
共犯从广义上讲,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狭义的共犯,又被称为加担犯或从属犯,仅指教唆犯和从犯。如何区别正犯与狭义的共犯,在外国刑法理论上有很多学说:
(一) 以因果关系论为基础的区别说,可分为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主观说以因果关系的条件说为基础,认为由于所有的条件作为原因是等价的,因而依据因果关系不可能区别正犯与共犯,区别的基础在于行为者的意思。主观说又有故意说与目的说或利益说之分。“故意说认为以‘实施自己行为的意思’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叫正犯,以加担于他人行为的意思而实施的场合叫共犯……目的说或利益说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益实施行为的场合叫正犯,为了他人的目的、利益实施行为的场合叫共犯。”[8]主观说不顾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根据主观方面来区分正犯与共犯,根本不可能区分清楚。因为犯罪乃是行为人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统一。有些西方刑法学者也对主观说提出尖锐的批判,指出这种学说不仅不能区分正犯与共犯,有时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某甲从商店为自己的妻子乙窃取了珍珠项链,若其妻子未参与任何行为,会得出甲仅是盗窃从犯,此案并不存在正犯的错误结论[9]。
“客观说立于原因说的立场,认为对犯罪的结果给予原因者为正犯,不过是给予条件者为共犯。”[10]而且由于它把实施成为结果发生的行为当做实行行为,认为实行行为只能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从而归结为正犯就是实施实行行为的人,共犯就是实施实行行为之外行为的人。这种学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企图从客观行为的特点上区分正犯与共犯,但是,如所周知,犯罪分为行为犯与结果犯,对于行为犯,并不要求一定结果的发生作为构成的要件,因而把造成结果发生的原因的行为与实行行为等同起来,显然不够恰当。
(二) 以构成要件为根据的区别说,又有限制的正犯论和扩张的正犯论的对立。限制的正犯论主张不通过他人而由自己直接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者是正犯,而参与犯罪但并未直接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者是共犯。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皆指正犯而言,不便对共犯适用,因而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共犯及其刑事责任,使对正犯的刑罚能扩张适用于共犯。这种学说的早期见解,以某些理由把间接正犯列入正犯的范畴; 后来的解释,又把相当于间接正犯的情况包含在共犯的范畴之内[11]。我们认为,这种学说以是否由自己直接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客观标准,它为区分正犯与共犯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根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如把间接正犯列入共犯的范畴,忽视正犯与共犯主观要件的区别等,都是这一学说的不足之处。
扩张的正犯论认为,“凡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的实现,给予任何条件者,都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者,都认为是正犯”[12]。换言之,一切共犯本质上都不失为正犯。法律对数人协力实施的犯罪,所以区别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在于限制本来应视为正犯的人,以便对他们在刑罚适用上有所区别。在他们看来,共犯概念是实定法的产物,实定法在刑罚的评价上对教唆犯规定“依照正犯处罚”,对从犯规定“按照正犯的刑罚予以减轻”,对刑罚幅度作了限制,所以,从实定法的意义上讲,正犯就是除教唆犯和从犯以外成为实施构成要件原因的人。“根据这种学说,共犯规定不是刑罚扩张原因,莫如作为刑罚缩小原因来把握。”[13]在我们看来,这种学说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因为它把一切共犯看做实质上都是正犯。虽然它承认在实定法上共犯与正犯的处罚有不同的规定,但这并不能把共犯与正犯区别开来。因为实定法对正犯与共犯的刑罚的不同评价是法律效果的不同,不是正犯与共犯构成的区别; 相反,必须将正犯与共犯的构成区别之后,才能相应地作出对他们的刑罚的不同评价。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法律后果来区别正犯与共犯,这就犯了逻辑颠倒的错误。
(三) 目的的行为论的区别说。目的的行为论者从把握行为的实体出发,以所谓目的的行为支配的存在,为正犯概念的标志。这种观点被称为目的的行为支配说。它主张通过有无目的的行为支配来区分故意行为中的正犯与共犯,认为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仅仅存在于故意行为中; 在过失行为中,对忽略必要的注意而导致构成要件结果的人,均以正犯论处,所以不存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关于目的的行为支配的内容,其说不一,有的置重于目的的实现意思 (Welzel),有的则重视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之目的的统制 (Maurach)”[14],即客观的行为支配说。所以目的的行为支配不只是故意,也不只是由于因果性而造成的事实,而是“计划的意思的客观化”(Gallas)。换言之,目的的行为支配意味着行为人对其认识到的情况有实现意图,采取适宜于完成构成要件的结果——行为人行为的结果的手段、方法,实施由行为人支配、统制可能性的外部行为。这种客观化的目的的行为支配就是正犯的一般性要素。目的的行为支配说,虽然力图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综合地加以考察,但目的的行为论作为行为的学说就不科学,因为它只能说明故意行为,而不能说明过失行为,以此学说为基础说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也就很难提出科学的根据。按照这种学说,目的的行为支配之有无,是正犯与共犯区别之所在; 这样,共犯行为即帮助及教唆,由于没有目的的行为支配,认为不是正犯。可是,故意的教唆或帮助行为也是故意行为,是承担故意之目的的实现意思的行为,教唆者与帮助者,关于其加功行为,亦不外是目的意识的支配者,所以仅以目的的行为支配之有无,区别正犯与共犯是困难的。而且所谓客观性行为支配,究竟意味着“现实性行为支配”,还是意味着“可能性行为支配”,也使人搞不清楚。
(四) 综合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主观说。与此学说相近的见解,早在19世纪末叶就有学者倡导,至20世纪60年代,复由鲍克曼 (Bockelmann) 所发展。在日本则由木村龟二所主张。木村说:“我认为首先不论正犯或共犯都应解释为实施了意味着现实的或可能的行为支配的构成要件行为即实行行为者,从而,区别正犯与共犯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实施实行行为,而在于实行行为决意之性质的区别之中,正犯指基于自己的决意实施实现构成要件行为者,共犯是通过他人的决意实施实现构成要件行为者。此时,以自己的决意单独实施的,是单独正犯,共同实施的,是共同正犯。通过他人的决意实施行为的场合,使当时没有实施行为决意的他人产生该种决意,通过他人的决意实施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为教唆犯; 通过已经具有实施行为决意的他人的决意而实施行为的,应认为是从犯。”[15]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相对来说是比较可取的; 但它过分强调主观的决意,而忽视客观的实行行为,甚至说: “我认为不论正犯或共犯都实施了实行行为,因而正犯和共犯仅仅是实现构成要件的态样的区别,以实行行为的有无作为区别正犯与共犯概念的标准是不妥当的。”[16]其实,正犯的实行行为是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实行行为,而共犯的“实行行为”是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各种被修正的构成要件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对正犯实行行为的加担行为。所以实在说来,共犯的行为不能说是实行行为。
三、间接正犯
(一) 间接正犯的概念
“所谓间接正犯,指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行犯罪的情况。”[17]就利用他人实行犯罪之点来说,间接正犯与共犯相类似; 但被利用的他人,在间接正犯的场合一般不构成犯罪,在共犯的场合则构成犯罪,因而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既与共犯不同,又非直接正犯,因而就间接实行犯罪上命名,称之为间接正犯。间接正犯在立法例上,始于德国1919年刑法典草案,该草案第26条规定了间接正犯的含义,并规定应依正犯处罚。1976 年联邦德国刑法典第25 条第1 款规定: “……假手他人实行犯罪,依正犯论处。”1974年日本刑法修改草案第26条第2款规定: “利用非正犯的他人实行犯罪者,也是正犯。”
间接正犯既是利用他人实行自己的犯罪,所以,如何具体地认定,往往从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从利用者方面,在这方面有“工具理论”(利用他人作为工具者是间接正犯)、“行为支配论”(支配他人行为者为间接正犯) 等。二是从被利用者方面,在这方面,或者认为被利用者的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 或者认为被利用者是正当行为者或过失行为者或无责任能力者等而被作为工具; 或者服从于利用者的行为支配,因而构成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在刑法上有无承认的必要,在学说上存在着争论。
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认为,共犯即教唆犯和从犯从属于正犯的犯罪而成立。正犯不构成犯罪时,教唆犯和从犯即不构成犯罪,因而也就没有处罚的根据。有责任能力人利用 (教唆或帮助) 无责任能力人或无犯罪意思人实施犯罪时,由于实施犯罪的人无责任能力或无犯罪意思,从而不构成犯罪; 依照共犯对于正犯从属性的理论,利用他人犯罪者,他人不构成犯罪,因而也就没有处罚的根据。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与利用工具犯罪无异,如果不加处罚,又与犯罪应予处罚的法理不合,于是不把利用者即教唆者或帮助者叫做教唆犯或帮助犯,而名之曰间接正犯,借以调和客观主义共犯理论的矛盾。而在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看来,共犯是数人共犯一罪,只要行为共同,即属共犯,无所谓从属性; 共同犯罪人中,即使有无责任能力人或无犯罪意思人,对于共犯的成立则不发生影响。因而利用 (教唆或帮助) 无责任能力人或无犯罪意思人的行为实施犯罪,仍不失为共犯,自应按共犯负责,丝毫没有承认间接正犯的必要。1988年修订的韩国刑法第33条规定,对间接正犯,依共犯处罚。即“对于因某种行为不受处罚者或者按过失犯才处罚者,予以教唆或者帮助而使其犯罪行为发生结果的,依照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处罚”。当前在日本,不少学者都把间接正犯认为是正犯的一种。如西原春夫说: “间接正犯与直接正犯同样是正犯的一种形态。”[18]间接正犯是正犯之一的观点在日本已经成为通说。
(二) 间接正犯的正犯性
间接正犯需要根据固有的正犯概念论证其正犯性,换言之,确定能够包含间接正犯的“正犯”概念是必要的。如何论证,学者间意见不一,主要有以下不同见解:
1. 行为支配说。此说认为,“间接正犯的场合,背后者为了行为的实施将他人作为工具利用,而且由于其‘优势’,获得与直接实施同价值的行为支配”[19]。针对此说,川端博指出: “然而,如已看到的那样,在‘行为支配’的观念方面有疑问,以此为基础给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提供根据,是不妥当的。”[20]
2. 实行行为性说。此说在日本被认为是通说,团藤重光、福田平、大塚仁、内田文昭等均持此说。如大塚仁写道: “间接正犯的正犯的性质的实体,在该场合被认为存在与直接正犯无异的实行行为性。即在背后的利用者的行为中,主观上具有实行的意思,客观上使被利用者的行为实现一定的犯罪,即可以看出来包含能够招致侵害、威胁法益的现实危险性这一点。”[21]川端博对此评论说: “本来所谓正犯,应认为指亲自实施有实现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性’的行为的人。间接正犯与直接正犯相同,实施有实现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的行为,所以被认为是正犯。我们认为这一立场是正当的。”[22]
3. 规范的障碍说。此说被认为是补充通说的一种见解,为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所主张。依照此说,打算利用的他人,从规范上看,是否成为犯罪实现的障碍成为标准。“即使是他人,他不能成为规范的障碍时,其利用与以自己之手实现犯罪是同样的,于此能承认正犯性。他人能成为规范的障碍时,因为作为法秩序在这里不能承认一方的利用关系,所以等到被利用者着手于犯罪的实行 (共犯的从属性)才承认犯罪 (共犯) 的成立。”(西原春夫) 因此,不能成为规范的障碍的人,特别是无责任能力者的利用,在 (1) 法的适用的划一性,(2) 绝对不被处罚者的利用的意义上,因为成为自己自身的实行行为的理由,常常在认为是间接正犯这一点上,其特征被表现出来。对此,植田博士认为,此说作为间接正犯的说明原理具有说服力,但是作为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标准,对使至于欠缺规范的障碍的利用行为 (强制、欺罔、权威的利用等) 及被利用者的形态的分析更为必要[23]。(www.zuozong.com)
比较上述诸说,我们认为,由于“行为支配”的观念不明确,行为支配说确实难以说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实行行为性说,从间接正犯的行为的性质具有与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相同的性质,因而认定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它没有结合间接正犯的特殊性来分析,似有所欠缺。规范的障碍说,从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作为工具犯罪这一特点分析,以被利用的他人是否成为规范的障碍为标准加以论证,这就弥补了实行行为性说的缺陷,具有说服力; 只是对规范的障碍缺乏清楚的说明,不免使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三) 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
间接正犯在如下场合成立:
1. 利用无责任能力者。这是间接正犯最典型最基本的形态。日、德刑法学者认为,具有责任能力是责任的前提条件,从而无责任能力者的行为是无责任的行为,利用无责任行为的场合,就成为解释间接正犯的根据。例如教唆精神病人伤害自己的仇人,或教唆幼年人偷窃别人的财物等,都是间接正犯。因为被利用者的精神状态有严重障碍或者还不成熟,因而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其身体的活动,只不过是被人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所以利用者具有正犯性。利用已经达到与成年人同样的成熟程度的未成年人能否成为间接正犯? 对此,日本不少学者给予否定的回答。如团藤重光主张: “即使是无责任能力者,已有是非辨别能力的 (例如12、13岁的少年),使之实行犯罪的,是教唆犯。”[24]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 “……所谓精神的道德的成熟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不仅实务上进行判断极为困难,而且也违背刑法把责任能力限定于划一的14岁以上的旨趣”[25]。
2. 利用缺乏构成要件的故意。这就是所谓利用不知情者的间接正犯。例如把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名誉的信,托不知情的人转交给被害人,构成诽谤罪的间接正犯。医生为了达到杀人的目的,将装有毒药的针交给护士为被害人注射,构成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被利用者不知情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受到利用者的欺骗无法了解真相,也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在被利用者无过失的情况下,构成间接正犯,虽为主张间接正犯的学者所公认,但在被利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是否能构成间接正犯,还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持否定说。如德国刑法学者毕克迈耶 (Birkmeyer) 认为: 过失犯的过失在心理的责任论中是责任条件,过失行为不是无责任的行为,而是有责任的行为,因而利用他人过失行为的场合,例如有杀人故意的医生,利用护士的错误,致使护士将毒药误认为正当之药交给病人,由于过失使病人死亡的场合,与利用无责任能力的行为全然不同,因而应当构成过失犯的共犯,不能构成间接正犯[26]。日本学者植田重正也认为,只要被利用者存在过失,利用者的行为就是他的共犯,而不是间接正犯。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持肯定说。如德国刑法学者弗兰克(Frank) 说: 对于利用他人过失行为的场合,承认间接正犯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因为如果把这种场合解释为共犯,尽管共犯者有故意,可是共犯者的责任,由于从属于作为正犯的过失犯,仅仅限于负过失的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他以作为共犯从属性结论所产生的处罚的不平衡为理由,承认间接正犯[27]。日本学者大塚仁也指出: “被利用者既然没有构成要件的故意,不问有无过失”,都是间接正犯[28]。此外,还有人采取折中的见解。如日本刑法学者泉二新熊认为,被利用者既然有过失而无故意,仍然应当以利用者为间接正犯,但对被利用者不妨作为过失犯的单独正犯予以处罚[29]。
此外,利用无故意的场合,这种故意是否限于特定犯罪的故意,也是一个问题。如利用者对被利用者隐瞒重的犯罪事实,被利用者以犯轻罪的意思犯了重罪的场合,对于重罪是否构成间接正犯? 例如甲明知是现住建筑物,谎说是非现住建筑物而教唆乙烧毁它,乙误信为非现住建筑物而对它放火。在这种场合,甲对烧毁现住建筑物负怎样的责任就是问题。对于重罪,乙不过是单纯的工具; 虽然在有人如团藤重光、青柳文雄等看来,甲构成重罪的间接正犯,然而有些学者如中义胜、西原春夫等却认为这种看法是不适当的。西原春夫指出:“结果是对现住建筑物放火的同一放火行为既然有故意,乙已经不是甲的工具,甲、乙成立共犯关系,作为共犯的错误的一种情况,甲应当认为是现住建筑物放火的教唆犯,乙则负非现住建筑物放火的正犯的责任。”[30](按日本刑法第108条规定对现住建筑物等放火处死刑、无期或5年以上惩役。第109条规定对非现住建筑物等放火处2年以上有期惩役。) 我们认为西原春夫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
3. 利用有故意的工具。所谓有故意的工具,指被利用者有责任能力并且故意实施行为,但缺乏目的犯中的必要目的 (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或者缺乏身份犯中所要求的身份 (无身份有故意的工具) 的情况。利用这种被利用者的行为,能否认为是间接正犯,虽有争论,但德、日多数学者都承认这种利用行为成立间接正犯。其理由是,为了成立共犯,正犯要具备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为了成立共同正犯,则以其全体成员具备全部构成要件要素为必要,从而,利用有故意的工具,既不能成为教唆犯,也不能成为共同正犯。
所谓利用无目的有故意的工具,即以一定目的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利用者有该种目的而利用无该种目的的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例如日本刑法第148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必须以行使为目的才能构成; 如果隐瞒行使的目的使他人代为制造假币,他人无行使的目的,利用者即构成伪造货币罪的间接正犯。对于这种情况,久礼田益喜认为: “因为在这种场合,被利用者大多知道利用者的目的,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共同正犯或从犯的关系。然而,果真自己没有这样的目的又不知利用者有这样的目的而实施行为者,由于不能独立成为犯罪人,对此,就利用者一方面说,可以构成间接正犯。”[31]
所谓利用无身份有故意的工具,即以一定身份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利用者有该种身份而利用无该种身份的人实施犯罪的情况。这种情况能否构成间接正犯,在学说上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肯定说,如日本刑法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 “问题虽然在于有身份者利用无身份者作为工具能否实现犯罪,但是应当认为有间接正犯成立的余地(通说)。在该种场合,应当认为利用者是间接正犯,被利用者是从犯。”[32]例如公务员的妻子是缺乏成立身份犯所要求的身份的人,如果单独实行是不会予以处罚的; 然而与作为丈夫的公务员共谋利用其职务而收受财物的场合,与单独实行不能同样看待。这种场合,通说认为丈夫是受贿罪的间接正犯,妻子是从犯。有的主张否定说,如中义胜教授认为: “在这些场合,因为被利用者是知情的,其‘工具’性不能不留有疑问吧。”[33]
在德国还有所谓“有故意的帮助的工具”的观念。这是指完全有故意,并且具备作为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所必要的目的等,但缺乏正犯者的意思,而仅仅作为他人的从犯而实施行为者。利用这样的工具的场合,由于“工具”一方面有故意,一方面参与实行,所以有认为是与利用者的共同正犯的见解; 但是“工具”的意思仅仅限于帮助,把他的行为看做正犯是不恰当的。在行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相适合的范围内,由于不过只能承认是帮助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而利用之者,解释为构成间接正犯是适宜的[34]。显然,这种观点实际上离开了主客观的统一来观察问题,结论自难认为恰当。
4. 利用适法行为。适法行为是本来不构成法律规范禁止对象的行为,即不具备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和原是禁止对象但个别场合被认为正当化的行为,即存在正当事由 (违法阻却事由) 的行为。前一种情况能够构成间接正犯,固不待言; 即使后一种情况,一般也认为能构成间接正犯。利用被利用者的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职务上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而犯罪的场合,被利用者的行为虽然没有违法性,但利用这种行为的行为,依然具有违法性,构成间接正犯。日本的审判实践也持这种观点。如日本大审院大正10年 (1921) 5月7日的判决说: “受孕妇嘱托堕胎的人,自己施行了堕胎手术,未发生堕胎结果时,孕妇的身体发生异状,为欲遂行堕胎,故向医师请求取出胎儿,因而使医生为了对孕妇的生命实行紧急避险的必要,不得已而取出胎儿。此种情况,该医生不构成堕胎罪自不待言,但受托堕胎的人,由于其犯罪行为——自己的堕胎手术而发生上述的紧急状态,同时,以其发生为契机而请求医生取出胎儿,在其行为与取出胎儿之间有因果关系 (换言之,不外是利用医生的前述的正当业务行为而遂行堕胎者),所以应以堕胎罪的间接正犯论之。”[35]
5. 利用非刑法上的行为。刑法上的行为是基于意思支配可能的态度,因而像反射运动或睡眠中的行动,像非基于意思支配可能的活动或在绝对的强制力之下的行动,都不是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活动,从而都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行为。利用他人的这一类的行为,能否构成间接正犯,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学者持否定说。如德国学者弗兰克、麦兹格等认为,把他人的反射运动或物理的强制下的动作作为“无生命的工具”或“死工具”加以利用的场合,因为与使用单纯的工具的单独正犯没有差异,从而没有特别叫做间接正犯的必要[36]。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 “被利用者在难以抵抗的强制下进行的身体活动,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说是刑法上的行为。其利用者,对基于被利用者的身体活动而惹起的事实,宜解释为亲身直接实现者。虽然仍有强制,但未能压抑被利用者的意思的程度时,由此而实现犯罪,不是间接正犯,而应视为教唆犯。”[37]有些学者则持肯定说。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说: “像利用他人的反射运动的场合那样,利用他人的纯粹物理的力的场合,是否值得用‘间接’正犯之名是一个问题。然而,间接正犯也是正犯的一种形态。由于其在刑法的处理上不发生差别,我认为索性不妨把凡是利用他‘人’的活动的场合,广而言之,都称为间接正犯。”[38]
(四) 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时期和终了时期
1. 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时期。由于间接正犯是由利用者的利用行为与被利用者的结果惹起行为复合而成立的犯罪,所以依什么行为认定其着手实行时期自然成为一个问题。即依被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认定其着手实行时期呢? 还是依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认定其着手实行时期? 对此理论上有很多主张: (1) 认为间接正犯着手实行的时期,应依被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来决定,即被利用者现实开始犯罪的身体活动之时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之时,这是客观说的见解。因为依客观说看来,利用者的行为不外是犯罪的预备。这种观点在德国曾经成为通说,如弗兰克、希布尔 (Hippel) 等都持这种观点。(2) 认为间接正犯着手实行的时期,应依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来确定,即以利用者开始对被利用者实施诱致犯罪行为之时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之时。从主观说的观点理解实行着手的概念,自然以此说为妥当。但在采客观说的学者中,也有采取这一说法的学者。在这一部分学者看来,被利用者单纯作为工具被利用时,被利用者不可能有实行行为,因而应当以利用者的行为为标准来确定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德国学者迈耶、麦兹格、李斯特等,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植松正、团藤重光、大塚仁、牧野英一等都持这种看法。这一见解现在在德国已代替前一看法而成为通说,在日本也居于支配的地位。(3) 认为一般情况下以利用者有诱致行为时为着手,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间接正犯则以被利用者开始身体活动时为着手。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观点。它不论在德国或日本都不占重要地位,并且受到一些刑法学者的批评,如大塚仁即指出: 这种立场“是适应间接正犯的形态区别实行的着手时期的折中说,在放弃统一的标准这一点上是不恰当的。在上述那样理解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的观念的范围内,即使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场合,也没有特别采用个别标准的必要”[39]。
2. 间接正犯实行的终了时期。间接正犯实行的终了时期,大体上与实行的着手相同,存在着两种见解的对立: 一种见解认为背后的利用者的诱致行为的终了时期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终了时期,大场茂马持此说。另一见解认为被利用者的犯罪行为的终了时期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终了时期,威尔哲尔持此说。日本的判例虽然采取后者的立场,但日本学者认为: “在规范主义的见地来看,只有在背后的利用者的诱致行为中才能找到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就这一点说,不能不支持前者的立场。”[40]
(五) 自手犯
所谓自手犯,指以间接正犯的形式不可能犯的犯罪。换言之,“自手犯是为了实现犯罪需要,正犯者自身直接实施犯行,采取利用他人的间接正犯的形式不能成立的犯罪”[41]。从因果论的观点来看(李斯特、大场茂马等),或从所谓扩张的正犯论的立场来看 (宫本英脩等),一切犯罪都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因而否定自手犯的概念。可是,犯罪是否成立,不可能仅仅根据因果关系加以论定,扩张的正犯论则忽视犯罪行为的类型的意义,因而这两种见解都是不恰当的。从构成要件的内容的意义来看,在规定以一定的行为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始作为犯罪而处罚时,一定的行为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对于这种犯罪就是必要的。这种刑法规范的特点在于利用他人不可能发生对法益的侵害。按照这种犯罪所根据的规范的特殊性,自手犯的概念自然应当予以肯定。现在这种肯定说在日本刑法学界已经成为通说。那么,自手犯可否成立间接正犯呢? 这就是以一定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无身份者利用有身份但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该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因缺乏一定身份不能成为直接正犯,可否构成间接正犯呢?学说上也有不少争论。
1. 积极说。认为任何犯罪都可以成立间接正犯,即使以一定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果无身份的人利用有身份但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该种犯罪,这种无身份的人就构成间接正犯。如妇女唆使精神病患者的男子强奸其他妇女,构成强奸罪的间接正犯。德国的玛拉哈、弗兰克,日本的宫本英脩、藤木英雄等都持这种见解。
2. 消极说。认为以一定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果缺乏这种身份,就与构成要件不合,即使利用有身份但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该种犯罪,该种犯罪本身不能成立。日本刑法学者正田满三郎说: “既然是身份犯,因为行为主体的特别地位,是以犯罪的违法性、有责性进而其可罚性为基础的,所以被利用者有身份的场合,除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场合外,我认为原则上消极说是正确的。”[42]
3. 折中说。认为不能构成直接正犯的犯罪,能否构成间接正犯,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写道: “不能成为直接正犯者,是否不能成为间接正犯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分别情况而论: ①一定身份作为犯罪的要件,系法律出于仅仅处罚有其身份者的行为的意思。在这样的场合,不能成为直接正犯者,应当说不能成为间接正犯。②有一定的身份者由于缺乏犯意或者能力,其行为不能发生法益侵害,在这种场合,利用他也不能构成间接正犯。例如受贿罪可以认为是其适例。受贿罪是侵害公务员清廉的行为,如果公务员丧失责任能力或者缺乏利用其职务收受贿赂的犯意,公务员的清廉不会受到任何损害,所以对于这种犯罪不能认为构成间接正犯……③在一般场合,一定的身份作为犯罪的要件,是因为其身份成为法益侵害的事实上的要件。所以没有这种身份者利用有这种身份者时,由此发生法益侵害的事实,从而可以构成间接正犯。例如妇女不能作为直接正犯犯强奸罪,但可以利用无责任能力的男子侵害其他妇女的贞操……”[43]比较上述诸说,当以折中说为妥。
自手犯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 真正自手犯与不真正自手犯。所谓真正自手犯,指不论在什么形态中都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的犯罪。不真正自手犯,指具有一定身份、目的等资格者利用不具有该身份、目的等资格者,虽可能构成间接正犯,但相反的情形下,估计是不可能的犯罪。真正自手犯在身份犯中可以举出伪证罪。再者,一般的举动犯 (行为犯) 中也存在真正自手犯,例如像吸食鸦片罪就是如此。与此相反,不真正自手犯为数较多。首先在身份犯中如受贿罪等,公务员虽然可能利用非公务员实行犯罪,但非公务员利用公务员实行犯罪却是不可能的。
(2) 实质的自手犯与形式的自手犯。所谓实质的自手犯,指像上述一些犯罪那样,间接正犯的犯罪形态实质上不可能的犯罪。与此相反,所谓形式的自手犯,指实质上间接正犯的犯罪形态是可能的,而仅仅在法律上排除这样的犯罪形态的犯罪。换言之,刑法把某一犯罪类型的间接正犯的情况作为另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独立加以规定的场合,叫形式的自手犯。例如,日本刑法第156条规定了公务员制作虚伪文书或变造文书罪,第157条规定了使公务员对公证证书原本等作不实记载罪,这样,第156条之罪为间接正犯的情况,已作为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并且其法定刑比第156条规定得还轻,所以不应再认为是第156条之罪的间接正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