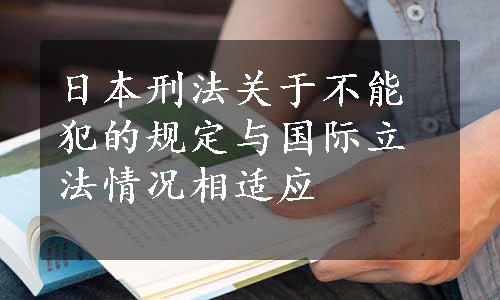
一、不能犯概述
(一) 不能犯的立法例
对不能犯,只有一部分国家的刑法典作了规定。不能犯的立法例,主要有两种不同情况:
1. 对不能犯不罚
奥地利刑法典第15条第3款规定: “犯罪行为如因欠缺法定之特定身份关系,或依行为之性质,或犯罪之对象,不能完成犯罪时,其未遂犯及未遂之参与行为均不罚。”
现行日本刑法未规定不能犯,但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25条却作了规定: “行为依其性质一般不能发生结果的,不以未遂犯论处。”草案的规定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它反映了日本刑法学者的基本观点。
2. 对不能犯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一,将不能犯与迷信犯分别加以规定,对不能犯减轻处罚,对迷信犯免除处罚或不罚。如瑞士刑法典第23条 (不能未遂) 规定:“行为人实行重罪或轻罪所采之手段或客体不能完成重罪或轻罪者,法官得依自由裁量减轻其刑。行为人因无知而为行为者,法官得免除其刑。”又如泰国刑法典第81条规定: “意图发生法定犯罪之结果而着手实行,因其所采之手段或犯罪之对象,确无发生结果之可能者,视为未遂犯,依其所犯之罪1/2处罚之。因迷信而为前项行为者,不罚。”
第二,只规定对不能犯减轻或免除处罚或者免除或减轻处罚,而对迷信犯未特别加以规定。如韩国刑法第27条 (不能犯) 规定:“因实行的手段或者对象错误,致使结果不可能发生,如果存在危险性,仍予处罚。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又如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规定: “行为人由于对犯罪对象和手段认识错误,在性质上其犯罪行为不能实行终了者,法院得免除其刑罚,或减轻其刑罚。”
从上述立法例不难看出,各国刑法对不能犯的理解和如何处罚很不一致,刑法明文规定对不能犯不处罚的,只是少数国家。
(二) 不能犯的概念
1. 日本刑法学者关于不能犯的定义
日本刑法学者在研究不能犯时,一般都对不能犯下了定义。现介绍几个权威学者的定义如下:
团藤重光写道:“……采用在定型上不能使结果发生的方法的行为,因为从实质上看毕竟欠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完全不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应当说不构成未遂犯。所谓‘丑时参拜’那样的迷信犯,是其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行为称为不能犯或不能未遂。”[95]
大谷实认为: “行为为了成为未遂,仅仅形式是符合构成要件是不够的,终于未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没有这样危险性的行为,称不能犯。即所谓不能犯 (不能未遂),指行为人虽以实现犯罪的意思实施行为,但其行为的性质上发生结果完全不可能的行为。例如实施‘丑时参拜’以咒杀人的场合属之。”[96]
板仓宏说: “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即使以实行某种犯罪的意思实施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上完全不能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由于不能说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不成为未遂犯。这样的行为叫不能犯。在德国虽然称为‘不能未遂’,但由于从开始就是没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不成为未遂的行为,因而称为不能未遂是不确切的措词。”[97]
山中敬一指出: “所谓不能犯,指就规定有处罚未遂的犯罪,主观上虽是着手实行但现实并无至于既遂可能性 (危险性) 或者由于可能性极低实质上欠缺实行行为性,作为不可罚的未遂的行为。”[98]日本学者对不能犯的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把迷信犯作为不能犯,并认为不能犯不具可罚性。
2. 德、法刑法学者关于不能未遂的阐述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等在所著《德国刑法总论》一书中对不能未遂解释说: 不能未遂“是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为目的的行为人的行为,由于事实的或法的理由,在所存在的情况下,不能至于既遂的场合。客体的不能、手段的不能或者主体的不能的场合属之。”[99]
法国刑法学者卡·斯特法尼等在所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一书中对不能犯作了论述。他们写道: “在刑法上,‘不能犯’是否构成‘未遂’? ……初看起来,‘不能犯’与未得逞的犯罪 (开枪杀人,但由于行为未能瞄准对象而未打中) 是很相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犯罪的所有事实上的行为均已完全实行,但由于行为意志以外的情节而未取得结果。但是,在‘未得逞的犯罪中’,实际上有可能产生犯罪结果,而在‘不能犯’中,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我们是否可以将‘不能犯’视同‘未遂’? ……在法律有规定的某些情况下,对此作出回答是不困难的。但是,有时‘不能犯’是不应受到处罚的……有时情况则相反,法律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罪进行惩处……”[100]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德国学者对不能犯未遂的定义与日本学者不同。不同之处在于: 它没有提出不能犯未遂的行为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因而是不可罚的行为。法国学者虽然没有对不能犯下定义,但其论述表明与德国学者的观点相接近,而与日本学者的观点明显存在差异。这基本上与有关国家关于不能犯或不能未遂的立法情况相适应。
(三) 不能犯的本质
什么是不能犯的本质,日本学者大塚仁有所论述。他说: “关于不能犯的本质,虽然有将它解释为是不可罚的未遂的见解 (草野豹一郎《刑法讲义 (总论)》第309页以下),但不可罚的未遂不限于不能犯的场合 (第44条参照),所以莫如说欠缺惹起构成要件的结果的危险性的行为是不能犯。”[101]板仓宏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有认为不能犯的本质是不可罚的未遂的见解……但不能犯是不构成未遂的,即使不是不能犯,也有不可罚的未遂——在各本条,只有规定处罚的未遂才能处罚,未遂并非全部都能处罚 (第44条),因而认为不能犯是不可罚的未遂的见解不正确。”[102]在板仓宏看来,不能犯是其行为在性质上,完全不可能使发生结果,因而不能说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场合。这一观点当前在日本属于通说的地位。从日本学者对不能犯的理解来看,应当说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
但从德、法两国学者对不能犯的理解来看,前述对不能犯本质的论点值得研究。因为德、法两国学者并不认为不能犯完全不具可罚性。所以德国学者耶赛克等认为: “不能未遂的处罚这个历来的争论问题,在今日本质上限于不能说完全没有损害一般人的安全感,不能未遂也是可罚的,在这个意义上,最终予以解决。”[103]至于免除处罚或不处罚的不能未遂,其行为当是完全不会损害一般人的安全感才可能认定。
二、关于不能犯的学说
关于不能犯的学说,亦即不能犯与未遂犯区别的标准的学说,可谓见仁见智,学说林立。德国学者耶赛克列举的学说有: 客观说、构成要件的欠缺和印象说。日本学者西原春夫列举的学说有: 事实的不能说; 法律的不能说; 危险说,又分为具体的危险说、抽象的危险说、客观的危险说; 主观说。大塚仁列举了七种学说,即: 绝对的不能、相对的不能说,法律的不能、事实的不能说,主观说,具体的危险说 (客观的危险说),抽象的危险说 (主观的危险说),印象说,定型说。山中敬一评述了六种学说后又提出自己的见解,即: 绝对的不能、相对的不能说,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欠缺说,主观说,抽象的危险说,具体的危险说,客观的危险说,其中还论述到三种修正的客观的危险说,二元的危险预测说,此系山中敬一教授的见解。参考以上诸家意见,现对如下一些学说加以述评:
(一) 绝对的不能、相对的不能说
这是根据费尔巴哈的思想发展、形成的学说。采用事后观察的方法来认定,即事后观察所实施的行为,从行为的客体或结果的性质看,结果的发生被认为绝对不能的场合是不能犯,被认为相对不能的场合是未遂犯,也称旧客观说。所谓“绝对不能”,指犯罪对象不存在 (如要杀害的人已经死亡),或者使用的犯罪工具、手段没有效力(如用无毒的药物去毒杀人)。所谓“相对的不能”,指犯罪对象虽然存在但不在行为人所认为的地点,或行为人使用的方法或手段虽然是有效的,但由于行为人使用不当不能发生效用 (如使用毒药的分量不够,不能将人毒死)。换言之,客体或手段不论怎样的情况都不适宜于犯罪完成的场合,是绝对的不能; 客体或手段一般地虽然宜于犯罪的完成,由于具体场合的偶然情况而不适宜于完成的场合是相对的不能。前者由于是客观上没有结果发生的危险的行为,是不能犯; 后者由于其行为能引起客观的危险性,是可罚的未遂。
费尔巴哈是最早提出不能犯问题的人。在他看来,关于未遂犯,犯人的行为与作为其目的的犯罪结果立于原因结果的关系是必要的。从所实施的手段或对象看,没有结果发生危险的场合,作为不能犯应当承认不罚性。继承费氏理论的是米特梅尔 (Mittermaier)。他首先认为欠缺法律上必要客体的场合,不能构成该犯罪。其次关于犯罪手段,限于该具体场合不能发生结果的,应与其行为性质上不能发生结果的相区别。前者是相对的不能,后者是绝对的不能。所以,这后者的场合与客体不存在的场合,同样作为不能未遂,应当承认不罚性。其后巴尔 (Bar) 对此进一步加以注释,指出行为的客体绝对的不存在的场合,例如想杀害的人是尸体即使用任何手段也不能导致杀人的结果,因而是不能犯; 目的物只是不在预想的场所,或者所用的手段在相对的意义上不能产生结果的场合,不是不能犯,而是未遂犯[104]。
在日本早期刑法学者胜本勘三郎、大场茂马都采此说。今天日本刑法学界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几乎没有,但在法国还有学者持这一观点。
对绝对的不能、相对的不能说,不论在日本或在法国都有学者提出批评。日本学者竹田直平指出: “所谓绝对的不能与相对的不能的区别,由于判断对象的范围所取的方向如何,也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以杀人的意思射击时,被害者已经死亡,事后即使被证明,然而试考虑行为之时向生存可能的人实施行为的状况时,不是绝对的不能,而是相对的不能。反之,由于被害者穿有防弹衣,子弹不能贯穿的场合,限于就该具体的客体观察,则不是相对的不能,而是绝对的不能。又,关于客体的不能与关于手段的不能的区别也不明确。例如,误认为在着弹距离之外的人是在着弹距离之内而射击的场合,可以认为是对客体的不能,也可以认为是关于手段的不能。并且此说,只是重视行为后被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对行为人意思中的计划,认识想定的情况,没有说明不包括在危险性判断的考虑之内的理由。”[105]法国学者卡·斯特法尼等针对此说也指出: “这种折中的办法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在不能犯之间设立起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不同等级,并且丝毫不考虑‘不能犯’的行为的意志,从而有可能使那些已表明对社会有危险的人逃脱惩罚。”[106]这些批评,我们认为确有道理,但并不能说明此说完全没有意义。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采取这一理论,表明了它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值得给予适当的注意。
(二) 法律的不能、事实的不能说
在法国学者中有的学者主张将不能分为法律的不能与事实的不能,以取代绝对的不能与相对的不能的区分。所谓“法律的不能”,指缺乏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 (如妇女没有怀孕、受害人已死亡等)。所谓‘事实的不能’,指行为人使用的方法、手段不能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对象不在行为人所认定的现场。法律的不能的场合是不能犯,事实的不能的场合为未遂犯[107]。对于此说,法国学者的解释并不一致。有的学者如Roux把法律的不能与事实的不能的区别,解释为同前述的绝对的不能与相对的不能的区别意义相同。另外的学者如Gar-raudr把法律的不能解释为与德国学者所说的构成要件的欠缺同一意义。例如,他这样论述: 在堕胎罪中胎儿是犯罪的法定要件,所以对没有怀胎的妇女实施堕胎,是不能犯。在盗窃罪中,客体为他人之物是本罪的法定要件,所以将自己之物误认为是他人之物而窃取,也是不能犯。在毒杀罪 (原法国刑法典第301、302条) 中,毒物的使用是法定的要件,所以误认为砂糖是毒物而投入对方饮料中时,是不能犯[108]。此说存在的缺点与绝对的不能、相对的不能说大致相同,因而法国学者对两说有同样的批评。日本学者对此说也有意见。大塚仁在同时指出上述两说的缺点时说: “在绝对不能、相对不能说与法律的不能、事实的不能说中,其不能的观念应当说是不明确的。”[109]此说在日本的影响很小,比较而言,其价值也较为逊色。
(三) 主观说
主观说,指如有表现实现犯罪意思的行为,不问是否有危险性,都认为是未遂犯的学说。此说由德国学者布黎 (Buri) 等所提倡,威尔哲尔 (Welzel)、玛拉哈 (Maurach) 等亦持此说。布黎认为,按照未遂的处罚根据求之于行为人的意思的危险性的见解,行为人有犯意,如有其犯意的实现行为,可罚的未遂就能肯定。在日本,有的学者称此说为纯主观说,宫本英脩、江家义男等学者力主此说。在宫本英脩看来,未遂的处罚根据,应求之于性格的危险 (犯罪反复的危险),所以既然有作为犯意之飞跃的表动的实行的着手,不问其原因如何,即认为是可罚的未遂,作为原则不承认不能犯,仅仅限于迷信犯的场合,认为不构成犯罪。如果以自然的方法犯罪,结果不发生时,通常应当说构成未遂犯[110]。对主观说,不少学者给予批评。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指出: “主观说由于未遂犯的可罚求之于犯意的客观化 (向外界的表动),因而不能犯成立的余地极窄,结果的不发生仅仅基于重大的无知的场合,才认为是不能犯。这也是向结论的妥当性的妥协,理论不一贯。作为理论的归结,这样的场合在犯意也客观化了的意义上,虽有未遂犯的成立,但得减轻或者免除其刑 (德国刑法第23条第3款)。然而,一般人客观上不感觉危险的行为,也承认违法性那就是意思刑法。”[111]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犯罪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在研究不能犯时也不能离开这一原则。主观说过分强调了犯罪的主观要件,限制了不能犯的范围,难以给不能犯作出科学的说明,因而为多数学者所不取。(www.zuozong.com)
(四) 抽象的危险说
抽象的危险说,为德国学者瓦琴费尔德 (Wachenfeld) 所主张。依照瓦琴费尔德的说明,所谓抽象的危险,意味着对法律秩序的危险,所谓具体的危险,指对一定的客体的危险。日本学者牧野英一、木村龟二、齐藤信宰等均持此说。此说将未遂犯的可罚性的根据,求之于行为人的意思的危险性,以行为当时行为人认识了的情况为基础,根据一般的见地,判断有无客观的危险,有结果发生的危险的,是未遂犯; 没有结果发生的危险的,是不能犯。从而,投与不足致死量的毒药的场合,固然是未遂犯; 即使把砂糖误认为毒药而投与的场合,行为人意图“投与毒药”,由于从一般人的立场看,感到结果发生的危险,也认为是杀人的未遂犯。但是,如果把行为人主观上认识的情况作为现实的事实来考察,抽象的任何危险也没有感到的场合,认为这是不能犯,不承认未遂的成立。例如,行为人投与砂糖量大,误认为投与大量砂糖能杀人的场合,由于从一般人的观点看不会感到任何危险,其行为是不能犯。所谓“丑时参拜”作为杀人方法的迷信犯,作为原则是不能犯。抽象的危险说,由于只是以行为人的犯罪意思中被认识了的情况作为危险判断的基础,所以又称主观的危险说或行为人的危险说[112]。需要注意,抽象的危险说与主观说不同,两者虽然都是以行为人认识了的情况为基础,但后者根据行为人本身的认识来判断,而前者是根据一般人的见地来判断。所以后者又称纯主观说,前者又称主观的客观说。此说虽然得到日本权威学者的支持,但今日仍然受到广泛的批评。例如,大谷实教授指出: “抽象的危险说以犯罪实现的危险为危险性的内容客观上来把握,虽然是对主观说的缺陷的纠正,但因为只是以行为人的认识乃至计划的内容为基础判断其危险性,仍然没有跳出主观主义的范围。”[113]前田雅英教授写道:“然而,如果犯人认为危险的事物包括在内,客观上完全没有危险性的行为也成为处罚的情况是不妥当的。”[114]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
(五) 具体的危险说
具体的危险说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和希皮尔 (Hippel) 等所提倡的学说,与绝对不能、相对不能被称为旧客观说相对应,此说又称为新客观说。它“以行为当时一般人可能认识的情况与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情况为基础,立足于一般人的见地具体地判断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认为肯定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场合,为未遂犯; 否定的场合,为不能犯。在从事前的立场,以其当时的情况为基础从一般人的立场判断危险这一点上,与抽象的危险说虽然相同,但不只是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也以一般人可能认识的情况为基础这一点,与抽象的危险说不同。”[115]依照具体的危险说,意在投与毒药杀人,但误认砂糖为毒药时,如果一般人认为是毒药的场合,以是毒药为基础判断,则有结果发生的危险,是未遂犯。否则,如果一般人可能认为是砂糖时,根据一般人的立场判断,投与砂糖的行为对结果发生没有危险性,是不能犯。又如,行为人误认尸体为活人,开枪向其射击的案件,如果一般人也认为尸体是活人时,从一般人的认识看,存在结果发生的危险性,是未遂犯。如果一般人可能认为是尸体时,感到不存在结果发生的危险性,是不能犯。此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折中说相符合,在日本得到泷川幸辰、佐伯千仞、平野龙一、植松正、藤木英雄、福田平、大塚仁等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的通说。如植松正教授明确提出: “具体的危险说是应当支持的学说。”[116]但此说也因为存在某些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木村龟二教授指出:“问题在于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与一般人可能认为的情况不一致的场合以其中哪一个为基础进行危险判断不明确,在这个意义上此说是不充分的。”[117]西原春夫教授针对具体的危险说写道: “……在行为当时一般人不容易看清的场合,结果与‘行为人的认识情况’相同的东西成为判断的对象,不可否定会得出与抽象的危险说相同的结论。”[118]具体的危险说存在的问题,一如上述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只如此。既然进行危险判断的基础不明确,那就既可能扩大未遂犯的范围,也可能限制未遂犯的范围。
(六) 客观的危险说
日本学者中山研一认为: “此说将未遂的处罚根据求之于向现实的法益侵害的直接的危险,从而行为只要客观上含有结果发生的具体的危险,成立可罚的未遂; 不是这样的场合,认为是不可罚的不能犯。”[119]山中敬一指出: “以行为当时存在的所有客观的情况为基础,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判断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危险被肯定的场合是未遂犯,被否定的场合是不能犯,是客观的危险说的原则。然而实际上被称为客观的危险说的,也是各式各样的。”[120]客观的危险说究竟包含哪些学说,学者意见不一: 前田雅英认为包含纯粹客观说、狭义的客观危险性说与绝对不能、相对不能说。山中敬一认为包含旧客观说 (即绝对不能、相对不能说)、新客观的危险说、纯客观说、修正的客观的危险说。但在书里山中教授论析了后两种学说,下面仅对纯客观说与修正的客观的危险说加以述评:
1. 纯客观说,纯客观说主张,考虑存在的所有具体情况包含行为后的情况在内,于事后纯科学地判断危险性,有危险性的是未遂犯; 否则是不能犯。
前田雅英教授为了读者便于了解不能犯的各种学说,曾列表加以说明。现转录如下,以供参考[121]:
纯客观说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学者多有批评。如山中敬一指出: 如果根据忠实于客观的危险说的主张,是否有可罚的未遂成立的余地就成为疑问。全部考虑事后判明的情况,如果以此为前提判断危险性,危险性被肯定的情况就很少。夺警官的手枪射击杀人的场合,如果偶然是没有装子弹的空枪,那么客观上杀人就是不可能的,就是不能犯。此外,误认为装入标记氰酸钾瓶子中的砂糖为氰酸钾用以杀人,使饮用达不到致死量的毒药; 将离开客体的方向定为目标用手枪射击,如果考虑全部的具体情况,客观上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就不存在。既然结果不发生,就都成为不能犯[122]。前田雅英进一步指出:“像纯客观说那样,极端彻底坚持‘结果无价值判断’,于事后用科学的标准进行判断,因为结果不发生的情况有其根据而不发生,所以很有可能所有的未遂犯都成为不能犯,那样,与处罚未遂的现行法明显相矛盾。”[123]我们认为上述批评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纯客观说与纯主观说相反,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考虑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意思,违背了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极大地限制了未遂犯的范围,不利于对犯罪的有效的惩治。
2. 修正的客观的危险说,又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假定的事实说。此说系日本学者山口厚所主张。他认为在侵害结果没有发生的场合,判断有无具体的危险,应当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首先,立足于事后的立场,如果法益侵害没有发生,即以此为前提。其次,考虑取代现实存在的事实,大体上怎样的事实存在,法益侵害——根据科学的因果法则——会发生。问题是现实不存在的(假定的) 事实,可能认为有何种程度的存在。最后,可以说具体的危险基于考虑‘根据科学的因果法则能使法益侵害发生的事实——虽然是现实不存在的——可能认为有何种程度的存在’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应将现实存在的事实置换为假定的事实,根据其存在的可能性具体判断有无具体的危险,而且不能不这样进行判断。”[124]同时,这个假定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根据纯客观的、科学的立场判断,必须根据通常性、一般性的观点判断,即这个判断应当不是从“单纯的一般人”的立场,而是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考虑该具体的情况,尽可能符合事实来进行。简言之,此说主张,在法益侵害没有发生的场合,以现实并不存在的 (假定的) 事实取代现实存在的事实,考察假定的事实有何种程度的存在,并以这样的事实为判断的基础,于事后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判断有无侵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对山口厚的假定的事实说,山中敬一教授作了如下的评价:“这一修正说,虽然主张事后判断,其实是了解事前判断情况的。与具体的危险说的区别,只在于不考虑主观的情况这一点。并且假定的事实是否能够充分判断成为哪样,再者,根本上是否能有‘假定的事实’,在不能犯的判断中是否重要,应当说都没有给予说明。”[125]山中教授的批评,确实指出了这一修正说的主要问题之所在。
第二,客观的事后预测说。此说系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主张。他写道: “危险性的有无虽然是以实行行为时存在的客观情况为基础,以实行时为标准,法官以一般的观点科学地合理地判断,但是连一般人所具有的‘不安感’也考虑则没有必要,它是从行为时看‘合理的 (科学的) 结果发生的概率的判断’。这样的表现与事后的客观的判断似乎没有差别,然而……行为时的客观的合理的判断与事后判断是不同的。但这个‘概率’到什么程度作为未遂犯处罚,则因国家或时代而异。”[126]山中敬一针对此说有如下的评述: 此说主张以行为时为标准,以一般人的观点,科学地合理地判断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此说是从事前立场的事后预测。并且这个客观的合理的判断,行为人的主观不作为资料,应以客观的情况为基础来判断。客体不能的场合、客体完全不存在的场合,虽然不成为未遂,但认为“死人”是“活人”实施杀害行为的场合,不能说完全没有客观的危险性。此说由于已认定行为时的事前判断,相当脱离客观的危险说的标准。然而事前判断并没有被贯彻。例如客体不存在的场合,就不是事前判断。最后山中教授评价说: “此说使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恣意地相混淆。”[127]不仅如此,此说以科学的“概率”进行判断的主张,也给人们带来困惑。因为“概率”达到什么程度作为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的标准,以及如何判断是否达到某种程度的“概率”,前田教授都未作出明确的阐述; 即使作了说明,在实践中也使审判人员很难操作。因而此说没有赢得多少学者的支持。
第三,一般的危险感说。此说系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所主张。依他的观点看,危险概念本来包含有某种价值的、评价的要素,作为它的标准不是纯粹科学的物理法则,而是 (科学的) 一般人的危险感问题。以客观上存在的情况 (没有装子弹的空手枪或者没有达致死量的毒药) 为前提,根据社会经验上一般是否感到危险,感到危险的场合是未遂,没有感到的场合是不能犯。对于此说,山中敬一评论说: 根据此说,即使是空手枪,如果用这种手枪对准,任何科学的一般人也都有“危险感”; 又对科学的一般人来说,如果没有达到致死量,即使饮下毒药,也都没有“危险感”,结果,成为依据“一般人的危险”这个完全不明确的标准之说,好好的客观的危险说,就丧失了明晰性[128]。的确“一般的危险感”是一个不明确的标准,根据这个不明确的标准,自然很难将未遂犯与不能犯区别开来。所以,此说也很少有人采用。
(七) 二元的危险预测说
此说为日本学者山中敬一所提出。他认为:为了成立未遂犯,首先,以行为当时科学的一般人可能认识的情况与行为人本人特别知道的情况为基础,从事前的立场,判断该行为能否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其次,有必要以行为后判明了的情况为基础,从事后的立场,判断在被害法益的作用领域中,是否发生了具体的法益侵害的危险。关于是否不能犯,基本上这样两个判断也是必要的。
1. 事前的具体的危险判断。首先,作为事前的判断,应当以科学的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性及行为人本人的认识为基础,考察客观的具体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要有科学的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性,因为碰巧被害人的头盖骨薄的场合,就不能以行为人本人特别知道的情况为基础。在这个判断中,通常以盗窃的目的将手伸入他人的口袋的行为,在事前看有危险性。使饮下达不到致死量的毒药,用没有装子弹的手枪射击,用精巧的仿制枪射击也是危险的。即使没看见人在睡,向好像是空床射击也是危险的。然而本人即使认为“是人”,科学的一般人看来,决看不到人,向分明是“地藏菩萨”那样的东西射击的行为则没有危险,可以说这是与具体的危险说相同的结果。然而在这个事前的造成危险的判断中,对不能犯的判断还不能完全确定。
2. 假定的因果预测判断。此说是沿行为人的行为的因果经过,考虑从实行行为以前的全体现象的流程,根据实行行为时的结果发生的客观的盖然性多么大来判断。现实的因果经过,事后结果没有发生是业已确定的,在到其实行行为的阶段,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客观的可能性,在结果发生的客观的盖然性高的场合,在实行行为时具体的危险状态存在,肯定为未遂; 在极低的场合,则成为不能犯。例如,在空床的事例中,实行行为时即使确定是空床,但这以前,被害人虽然在那个床上睡,碰巧当时去到隔壁房间的场合,客观的盖然性不能否定。然而被害人1个月前去海外旅行的场合,则没有客观的盖然性。用枪射击杀害躺在床上的人,即使几分钟前已死亡的场合,因为人活着的客观的盖然性不能否定,则肯定有客观的危险性。简言之,实行行为时具体的危险状态是否存在的判断,在从此以前的因果预测中,考察与实行行为时的客观情况不同的情况形成的可能性,根据在实行行为时,虽然现实结果未至于发生,然而至于发生的客观的盖然性能否判断是高的盖然性来进行[129]。
此说的核心问题是实行行为时具体的危险状态是否存在,据此认定是未遂犯或不能犯。而这种具体的危险状态指结果发生的客观的盖然性接近高的状态或者结果发生的假定的盖然性高的状态。要判断具体的危险状态是否存在,就要考虑事后判明的所有情况,来判断结果发生的客观的盖然性。这样就归结到对盖然性的判断,与前田雅英所主张的对概率的判断近似,因而前田教授的客观事后预测说所存在的缺陷,山中教授的二元危险预测说也同样难以避免。
(八) 定型说
定型说又称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欠缺说,系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等学者所主张,认为行为人实施基于定型上是不能的方法的行为,从实质上看,欠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不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因而不构成未遂犯,而构成不能犯。如小野清一郎说: “把行为及其情节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是否存在着实行行为,决定着未遂犯的有无。在不能确认作为包含实行行为之关键的结果发生的危险的场合,因其不存在实行行为,也就没有未遂犯了。这或者说就是不能犯……”[130]团藤重光说: “最后我们不得不到定型说的立场。旧的绝对不能说,认为行为本身性质上发生结果绝对不能的场合,可以说作为观点近于定型说。草案第25条规定: ‘行为其性质上全然不能发生结果时,不以未遂犯处罚。’宜认为基本是成为定型说的观点。”[131]定型说受到大塚仁的支持。他说: “这样,一方面以定型说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具体的危险说为基础,从而可以区别未遂犯与不能犯。”[132]但也受到学者的批评。如山中敬一指出: “此说与其说是以结果发生的实质的危险性为不能犯的判断标准,不如说是以形式的行为的定型性为不能犯的判断标准,但定型的判断标准不明确这一点是个问题。”[133]我们认为,此说以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础,有可取之处,但怎样判断是否定型,则缺乏应有的说明,不免给实际操作带来困难。
(九) 印象说
印象说为德国学者巴尔 (Bar)、麦兹格 (Mezger) 所主张。根据此说,行为在外部给人以侵害法秩序的印象,危害法秩序具有实效性这个一般人的法的安全感时,是未遂; 不能给予这样的印象的行为,是不能犯。它虽然可以将具体的危险说的观点,从一般预防的见地,转换为社会心理的观点,实际上与具体的危险说不怎么有差异。例如,根据印象说,从他人空口袋中掏取金钱的行为,因为侵害法秩序,危害法的安全感,所以不是不能犯,而是盗窃未遂。即使根据具体的危险说,大概得出同样的结论[134]。据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书中所载,此说今日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学说[135]。但它在日本影响不大,许多著作大多没有论及。大塚仁评论此说时认为: “印象说,在印象的概念中虽然有稍微不明确之处,但实质是可以说它是以与具体的危险说同样的内容为目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大体值得支持。”[136]我们认为,印象说中的“印象”这一概念确实不够明确,因而很难据以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这可能是它在日本影响不大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不能犯的学说,确实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提出有益的见解,但都有所不足。因而应当根据各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使之不断地趋于完善。
三、与不能犯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 事实的欠缺
事实的欠缺,也称构成要件的欠缺,历来与不能犯的问题相关联。所谓事实的欠缺,大体上指构成要件要素中,除关于因果关系部分之外的附随要素,即犯罪的主体、客体、手段、行为状况等要素欠缺,行为人误认为存在而实施行为的情况。它可区分为以下几种:(1) 关于犯罪主体的事实的欠缺,例如,不是公务员的人误认为自己是公务员而收受贿赂的场合。(2) 关于犯罪客体的事实的欠缺,例如,误认死人是活人用短刀刺杀的场合。(3) 关于犯罪手段的事实的欠缺,例如,意图使用安眠药使他人昏睡而窃取财物的人,错误地把砂糖当作安眠药使他人服用的场合。(4) 关于行为的状况的事实的欠缺,例如,不是火灾之际误认为有火灾的人将拉消防车的马赶进洞中的场合 (按: 日本刑法第114条规定: “发生火灾之际,隐藏或者损坏灭火用具,或者以其他方法妨害灭火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惩役”)。事实的欠缺被认为是不可罚的,因为其行为欠缺构成要件符合性,在这个意义上与不能犯同出一辙。所以作为形式的用语采用事实的欠缺的观点即使没有妨碍,但用作与不能犯相区别的特别的观念应当说不存在实质的理由[137]。
与上述大塚仁否认事实的欠缺这一概念具有独立的实质意义的观点相反,正田满三郎则肯定事实的欠缺这一概念具有独立的实质意义。他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中,除行为的因果关系外其他附随的要素——犯罪的主体、手段、行为情况等——有关的要件的哪个欠缺时,是事实的欠缺,与不能犯区别而认为犯罪不成立。不能犯问题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关于实行计划中意图实现的盖然性的认识与客观评价的不一致,根据其程度如何,是否认为符合构成要件 (未遂犯)这一点。所以,欠缺构成要件中所必要的关于行为主体的要件 (例如刑法第197条中的“公务员”)、关于手段的要件 (例如刑法第230条中的“摘示事实”)、关于行为情况的要件 (例如刑法第114条中的“火灾之际”) 的行为,从开始就欠缺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很明显的,无需讨论行为的危险性 (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在这里几乎没有不能犯成为问题的余地,也没有未遂犯成立的余地,是犯罪不成立的情况。与此相反,关于行为客体的要件 (例如刑法第235条中的“他人的财物”) 的欠缺,在其规范的方面 (前例中的财物的他人性),与构成要件的欠缺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在客体(前例中的财物本身) 是构成行为的因果的危险的不可分的事实的要素这个意义上,同样能以未遂犯或不能犯论罪。为了成立既遂犯,客体的存在虽然是必需的要件,但为了成立未遂犯,行为当时客体的存在并不一定是必要的。这样,能以未遂犯或不能犯论罪的,归结为限于刑法在构成要件上就犯罪实行的手段方法没有规定任何特别的要件的场合 (例如刑法第199条的杀人罪、第235条的盗窃罪等)。向人射击时,成为攻击的客体的人即使碰巧在射程之外,也不是事实的欠缺问题,已看作是未遂犯或者是不能犯的问题。这样,事实的欠缺与不能犯是不同的观念[138]。
如上所述,事实的欠缺能否成为独立的概念在日本还有争论。可是,在不能犯被规定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的国家如德国,则肯定事实的欠缺作为独立的概念。因为事实的欠缺是不成立犯罪的情况,与免除或减轻刑罚的不能犯自然是不同的概念。其实,即使在日本,正如正田满三郎指出的那样,事实的欠缺与不能犯也不宜等同。主张定型说的团藤重光教授主张,欠缺本质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承认作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这种场合不构成未遂犯而称之为事实的欠缺。欠缺行为的主体和行为的状况的场合就是如此。据此野村稔说: “这样在今日事实欠缺的理论被有限地肯定……”[139]所以,我们认为事实的欠缺虽然可能与不能犯有所交叉,似不宜否定其作为独立的概念。
(二) 幻觉犯
所谓幻觉犯,指行为人的行动本不构成犯罪,误认为构成犯罪而实施的情况。详言之,由于处罚规定从当初就不存在或被法律废止,行为时处罚这种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完全不存在,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从而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的、可罚的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叫幻觉犯。有的学者把事实的欠缺与幻觉犯混为一谈,认为事实的欠缺是一种幻觉犯; 有的学者认为,幻觉犯与事实的欠缺不同,指出: 幻觉犯“例如,自杀、通奸、近亲相奸、加入以否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结社等行为,因为现行法上不存在处罚规定……行为人误认为违法,即使所认为的事实被实现也是不罚的,不发生未遂犯的问题。与此相反,上述意义的‘构成要件的欠缺’的场合,即尽管构成要件要素的一部分不存在,误认为存在而实施行为的场合,从而行为人误想所认为的客观的事实如果存在,可罚的违法事实就能成立……”[140]可见幻觉犯与构成要件的欠缺 (即事实的欠缺) 存在明显的区别。
(三) 迷信犯
采用非科学的方法或迷信的手段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场合,称为迷信犯。迷信犯在日本通常作为不能犯的典型情况论述而未特别提出予以论析,但也有学者如夏目文雄、上野达彦在论述不能犯时将迷信犯作为专题加以论述。考虑到有的国家如瑞士、泰国在刑事立法中将迷信犯在不能犯中特别作出规定,应将迷信犯作为不能犯的特别情况看待,因而这里将迷信犯作为一个专题稍加述议。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所著《德国刑法总论》一书中将迷信犯称为“非现实的或迷信的未遂”,并说迷信犯不处罚,举例指出用咒文呼出恶魔杀人的是其实例。“在这个场合,作为原则已经欠缺故意,即使形式上能够肯定未遂,用咒文或与此类似的方法,对共同体不可能给予任何印象。但某一过激的宗派信徒的集团,由于妄想的理由用现实的手段杀人的场合,则另当别论。”[141]
对迷信犯能否以未遂犯处罚,虽然前述采主观说的学者,重视行为人的犯意,主张迷信犯应以未遂犯处罚,但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某些采主观说的学者如牧野英一、宫本英脩等均认为迷信犯不能以未遂犯论处。至于为什么不能以未遂犯处罚,所持理由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无犯意说。牧野英一认为,迷信犯所预见的结果本身虽然是犯罪事实,然而其所采取的方法并不具有所谓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就其方法的危险性考察,必须说欠缺符合实行行为的事实的认识。因此,应当解释为迷信犯是本来没有犯意的行为。(2)放任行为说。宫本英脩主张,迷信犯一般是由性格怯懦不敢采用自然的方法的人进行的,这样的人没有采用现实的手段实行犯罪的危险。因为基于这样的性格的行为也没有抽象的危险性,所以作为放任行为认为不构成犯罪。(3) 在夏目文雄、上野达彦看来,包含迷信犯在内的不能犯之所以不处罚,虽然可以说是因为它完全欠缺危险性,实际上必须注意在它以前其行为已不符合作为实行行为的类型性 (定型性) 这一点。即因为欠缺作为实行行为的类型性,不能认定实行的着手,从而也不成立未遂犯[142]。我们认为,上述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实质上看,迷信犯之所以不处罚,根本上在于行为人所采取的超现实的手段,不可能给法律所保护的现实的社会关系造成任何危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