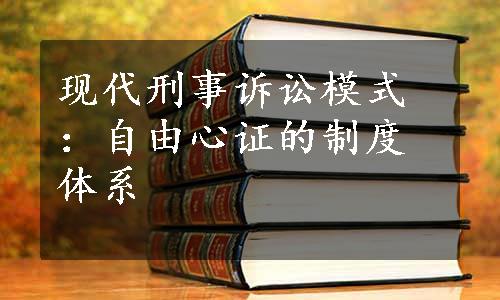
因语言翻译、法系差异以及理论误读等种种原因,自由心证存在严重的语义混用。中国学术界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自由心证”这一概念,包括证明标准、证明模式以及证明力评价手段,这种理解其实是模糊混杂的,且多有谬误。从根本意义上讲,自由心证[86]是探索事实真相的直觉感知模式,指法官通过证据自由评价实现从客观确信至判决责任伦理的跨越。故自由心证的核心目的是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完成法官本身所负有的判决责任伦理,而非解决证据资格、证明标准或者进行证明力的评价。但自由心证又必须以证据自由(la liberté de la preuve) 及证据自由评价 (l'appréciation libre de la preuve) 为前提。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证据自由评价”,则指法官通过理性推理对各种证据形式的证明力进行评断,以为判决提供客观依据。三者关系紧密,具有共生性(consubstantialité),构成了自由心证的制度体系,但不可混为一谈。
1.证据自由[87]
“证据自由”,指证据形式自由,即将证据能力与证据形式作一清楚切割,允许通过任何证据形式证明犯罪事实。欧陆刑事诉讼之所以确立证据自由原则,依据有四:刑事犯罪的特殊属性、自由心证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需要以及揭示案件真相的要求。
首先是刑事犯罪的特殊属性。刑事犯罪具有偶发性及不可预期性之特点。犯罪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无从预判,查证犯罪的证据形式亦难以预先确定(prédéterminer)。这与民事、商事或者劳动纠纷有着根本不同。例如,在民事、商事或者劳务合同中,当事人往往会事先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契约权利及义务,此一书面文件便是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所预定的证据形式。尽管纠纷未必发生,但如果发生且诉诸司法,则书证及“书证优先效力”原则便适用于此一民事、商事或劳务纠纷案件。当事人甚至可在证明手段上达成合意(学说上称为证据契约:Beweisvertrage)。[88]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具有很强的个案属性,每一刑事案件几乎都有不同的犯罪证据链条。任何类型的证据形式都有可能在个案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已在不计其数的案例、侦查报告甚至小说、电影中得以佐证,刑事案件的“戏剧性”及“猎奇性”很大程度上便源自于其无法预计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从证明的角度看,立法者几乎不可能从一般意义上预判在何种类型的刑事案件中某一证据形式对揭示真相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受害人、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亦不可能对证明手段或者证据形式达成合意(口供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刑事证据自由的设立,无疑是刑事犯罪特殊属性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自由心证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自由心证的证明体系要求法律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力不作任何预设,由法官自由判断。“不仅一个个孤立的证据能够证明何种事实以及证明程度如何,由法官自由判断,而且所有证据综合起来能否证明起诉的犯罪事实或其他有关事实以及证明程度如何,也由法官自由判断。在相互矛盾的证据中确定何者更为可信,同样由法官自由决断,不受其他限制。”[89]其裁判者必须通过证据调查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并达致真正的“内心确信”(certitude intime)。[90]
再次是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需要。刑事证据立法游离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两者不可偏颇,这与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的目标导向完全一致。面对“狡猾”(inventif)、“奸诈”(habile)、“危险”(dangereux)的罪犯,发现犯罪、查清犯罪行为实施者以及确定刑事罪责等便成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travaux),因为罪犯总是极力掩盖自己的罪行,消除犯罪现场痕迹,销毁所有可能与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误导侦查方向等。为有效惩罚犯罪,尽快恢复受损的社会秩序,司法职权机关必须拥有更犀利的手段以应对之。这在刑事证据立法上便体现为证据自由原则,即司法机关可通过各种证据形式证明犯罪事实。所谓“证据越难获得,越应降低证据调查的难度”,刑事追诉拟推翻无罪推定,这就要求对证据进行“最广泛”“最有效”的收集。[91]正如刑法学大家埃利(Hélie)所言,证据自由的功用便在于“有效证实犯罪分子所试图掩盖的犯罪行为,揭开其中的阴影,重新发现那些被几近擦拭的犯罪痕迹”。[92]近十余年来,随着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恐怖活动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各国刑事立法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多元化的侦查策略及手段以及配套的、更为宽松的证据自由俨然已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手段,且有不断增强之态势。证据自由之于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功用在此一极端的情况下一览无余。
最后则是揭示案件真相的要求。司法上的“真相”与历史学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及哲学意义上的“真理”等均有显著区别。如卡尔波尼埃(Carbonnier)教授所指出的,“在司法领域中,我们不能损害真实……但达致绝对的真实依然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价值诉求。”[93]拉伽尔德(Lagarde)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在司法领域中)真相便是“通过法定的程序达致不可撤销的结论”。[94]尽管立场和观点均有所区别,但有一结论毋庸置疑,即“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刑法对真相的要求更为迫切”。[95]“揭示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应是中立的,既适用于作为追诉者的司法职权机关,亦适用于被推定为无罪的被告及辩护人。梅尔勒(Merle)及维蒂(Vitu)教授在论及证据自由原则时曾深刻地指出,“证据自由自然为打击犯罪而设,但并不意味着被追诉者不得通过各种证据形式为自身辩护”,两者其实均服务于一个目标,即揭示案件真相。[96]考虑到在刑事诉讼的特定场景下,辩方之于控方在证据调查方面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再对证据形式加以严格要求,则“真相”极有可能沦为“单极的事实”(monopole),而非“客观真相”(la vérité objective),这显然与刑事诉讼“两造结构”的精神实质(essence)相悖。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证据自由在提高控方打击犯罪效率的同时,亦增强了辩方有效辩护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力量的均衡亦是揭示真相的必要前提。
2.证据自由评价
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评价包括两方面:一为批判性审查,二为事实推定。前者系法官理性的智识评价,后者则为法官的审慎认知。
(1)理性:批判性审查(l'examen critique des preuves)。对证据进行批判性审查,系法官在刑事诉讼中作出罪责裁判的核心任务。“在此一问题上,审慎的法官应如智者一般,首先应持不信任的态度或者临时的怀疑,仅将心证立足于对证据的充分审查之上。”[97]证据的审查过程虽涉及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但自然科学的方法仍然适用,包括演绎法、归纳法与逻辑推演。所不同的可能仅是证据审查程序立足于一套精心制作、高度形式化及制度化的程序规则,且最终将形成某一确定的诉讼结果,而自然科学则未有此一相应规则,也无需得出确切的结果。故法官如同自然科学家一般,在特定案件中自由地获悉各种证据,且基于理性的逻辑判断评价这些证据。以此为前提,法官会形成对特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推测。此后,法官将依程序规则听取其他证人或调取物证书证以验证这一推测。“把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理解为认识事实的进程,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测定实验——为了测定一个数值(经过数次测量),采用特定的方法进行数次测量(每一次测量产生一个稍微不同的结果)。它们类似于化学实验,为确定每个实验最后会获得相同结果而重复数次相同的过程。此类程序具有重大意义及证明价值。未有大量、重复的实验,则不能认为事实已为科学所证明。”[98](www.zuozong.com)
以证人证言为例。受中世纪宗教理念的影响,证人证言一直是职权主义国家刑事诉讼最频繁适用的证据形式。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并不以数量取胜,而主要取决于证人对事实的认知程度以及证人本身的品格。故对证人证言的批判性审查主要包括诉讼事实认知能力、证人品格以及证人与其他证据形式之间的印证。所谓诉讼事实认知能力,是证人了解及判断案件事实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事实认知能力不足将导致证人证言证明力下降。例如儿童作证,鉴于儿童的心智并不成熟,无法认知证人证言在案件事实查明中的重要作用,且容易夸大事实,法官在审核此一证据时应充分考虑此点。《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便规定,“不满16周岁的儿童,可以不经宣誓而提供证词”(第108、335-7、447、536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仅将儿童的证词作为辅助信息。证人品格则主要涉及公民道德意识。在欧陆刑事诉讼中,被剥夺公权、民事权或亲权的个人在出庭作证时无需宣誓,其所提供的证言亦仅具有辅助效力。证人证言还应与其他证据形式进行比照印证。证人证言具有相对性和脆弱性,“法官的心证要求证人证言更为明确、严谨,不能遗漏证据链条中的任何一环……但永远不要期待证人证言有着数学般的准确……法官可通过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对照填补推理的空白,以提高情感确定的程度。”[99]以1991年法国著名的奥玛谋杀案为例。1991年6月24日,法国南方小镇穆甘(Mougins)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富有的寡妇居斯兰纳·玛绍尔(Ghislaine Marchal)死于家中地窖,身上有一钝器伤及木制檩条所形成的若干打击伤。地窖的大门紧闭,血流满地,门上留下一段血句“OMAR M'A TUER”(奥玛杀了我)。经法医鉴定,血液系受害人玛绍尔所留下,宪兵队推断,血字应为受害人“临死前的信息”,故玛绍尔家中的园丁奥玛成为最大的嫌疑犯。奥玛系摩洛哥人,宪兵队因担心他逃逸,于6月25日将其刑事拘留。奥玛辩称案发时正在住所附近,有不在场证明,但宪兵队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控方证人米海依尔·毕利奥蒂(Mireille Billioti)。毕利奥蒂称,“6月23日11:30至12:45~50左右,我在阳台上一直守候着我女儿的到来,格拉斯路方向,但没有看到奥玛先生。”该证据最终获得采信,陪审团判处奥玛18年有期徒刑。但辩方律师雅克·维尔治(Jacques Vergès)在判决4年后重新向毕利奥蒂取证,这位证人无法解释如何一边做饭,一边守候在阳台。维尔治律师还发现毕利奥蒂曾得过大脑血管病症,注意力难以集中,认知能力也有问题。奥玛谋杀案因此成为法国20世纪90年代最具戏剧色彩的悬案。迄今依然有不少法国民众坚持认为,这是法国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见,证人证言的批判性审查极为重要,法官应认真判断。
(2)认知:事实推定。推定,便是“法律或司法官依已知之事实推断未知之事实所得的结果”。[100]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前者由法律明文规定,后者则立足法官认知,系证明力评价的重要补充。《法国民法典》第1353条便规定,“非法律上的推定,由司法官依其学识与审慎自定之,司法官仅应承认重大、准确、相互印证的推定……”从根本而论,对证据的批判性审查追求某种严格的客观性,而事实推定则属法官的主观认知范围之列,两者在司法实践中均不可或缺。事实推定以司法官的“学识”为前提,包括但不限于经验常识,还涵盖已证事实、相邻事实、职业思维以及专业研判等。[101]司法官在运用事实推定时应“审慎”,避免陷入主观臆测。例如在前述奥玛谋杀案中,控辩双方围绕犯罪现场的血迹展开激烈争辩。辩方认为,OMAR M'A TUER(奥玛杀了我)具有明显的拼写错误(正确的拼写应为OMAR M'A TUÉ),受害人玛绍尔受过良好教育,生前又喜好猜字游戏,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拼写错误,唯一的可能是:凶手用受害人的手写下血字,嫁祸于奥玛。但合议庭通过鉴定,发现血字的笔迹与受害人玛绍尔的笔迹一致,遂依“相互印证”原则,对辩护意见不予采信。而在另一起谋杀案中,被告T先生涉嫌于1997年3月21日杀害其儿子,控方向法庭所提交的证据仅包括T夫人通过录音所获得的被告认罪供述、数份证人证言表明T先生系其儿子的最后接触人以及T先生的暴力前科,但没有找到尸体,也未发现犯罪工具。但滨海阿尔卑斯(Alpes-Maritimes)重罪法院在排除了T先生儿子离家出走及被他人绑架的可能后判定T先生罪名成立,处20年有期徒刑。[10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实推定仅能达致某种盖然性优势的证明标准,需要其他证据进行补强。“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司法的,或者是技术的,或者是逻辑的,或者是心理的,只要必要,即便在不甚复杂的案件中,亦应发挥作用……每种证据适用不同的方法,但(法官)必须对证据的整体作出评价,予以系统化并抽象出所有证据的关系。(法官)正是立足这些关系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103]
3.判决责任伦理
法官的判决责任伦理既包括不得拒绝裁判的职责要求,也包括存疑有利被告的判决责任。
(1)裁判义务。法官不得拒绝作出裁判,这是近代法治国司法制度的通例。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裁判。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在刑事诉讼中,法官亦不得以程序性事项、实体性事项或者其他事由拒绝作出裁判,否则将违反职业伦理甚至构成犯罪行为(如《法国刑法典》第185条所规定的拒绝裁判罪)。
故刑事法官在对各种类型的证据进行证明力评价后,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形成心证,并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公正判决,以完成法官的判决责任伦理。为保障裁判者可通过证据自由评价顺利实现“从客观确信至判决责任伦理的跨越”,各国刑事诉讼普遍设置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程序原则:集中审理原则和合理期限原则。集中审理原则又称为连续审理原则(principe de continuation),指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应当持续不断地进行,一气呵成,至审结为止。该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迅速审判,保证裁判人员进行准确心证,以避免裁判人员因时间拖延而记忆模糊,从而加大心证难度;合理期限原则是指“所有人均有权在合期期限内接受审判”(《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否则须予以释放。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立即出庭程序中,法庭应在对被告采取临时羁押措施后1个月内作出实体判决,但可延长1个月。超过此一期限,法庭得依被告之请求予以释放(第397-3条);在轻罪案件中,如果对被告采取临时羁押措施,则案件应在移送的2个月内进行实体审理,否则应释放被告(第179条第4款)。在例外情况下,法院可以以载明理由之裁决延长羁押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如果被告在此一期限内依然未获裁判,则应立即予以释放;在重罪案件中,预审结束后的等待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但预审庭还可继续延长6个月(第215-2条)。[104]
(2)存疑有利被告。法官在心证过程中存有怀疑(la doute)的,应作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这是刑事法官裁判责任伦理的要求。但究竟何为“怀疑”?须达致怎样程度的“怀疑”?各国学说与判例有较大的争议。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相同。英美法系的主流学说以“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为依托,主要包括两种理论:其一,情感确信说。持此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系情感上的确信(moral certainty)。例如,证据学鼻祖吉尔伯特(G.Gilbert)在《证据法》(The Law of Evidence)一书中写道,“对证据完全的确信依赖于个人所产生的清晰明确的感知。”[105]此为“情感确信说”的重要理论渊源。判例将此一学说解读为,“陪审团如此确信,仿佛在处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时能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106]其二,量化比例说。英美证据学的另一大家摩菲(Peter Murphy)则主张用量化的比例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摩菲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控方的主张证明达到49%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51%的可能性时,辩方胜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达到51%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49%的可能性时,仍然是辩方胜诉,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只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远远超过90%的可能性之时,控方才能胜诉。”[107]而大陆法系国家总体采用更高的“怀疑”标准,例如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数次在判例中提出了“重大怀疑”(la doute sérieux)理论,“既然这些情况在本质上导致了对有罪的重大怀疑……(应予以无罪释放)。”[108]尽管《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最终未将“重大怀疑”写入其中,但正如冉-德尼·布勒丹(Jean-Denis Bredin)教授所言,“在司法实践中,所有人都知道,没有重大的怀疑,撤销(判决)绝不可能。重大的怀疑,是一个‘强化’的怀疑,一个能导致无罪高度可能性 (probabilité d'innocence)的怀疑,而不仅仅是无罪一般可能性(possibilité d'innocence)的怀疑。”[109]尤值一提的是,意大利于2006年引入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prova“al di là di ogni ragionevole dubbio”),将其写入《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6条。《意大利宪法》第25条第2款、第27条第2款及第3款亦规定,“只有在排除合理怀疑后仍能证明有罪才可对被告人宣告有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意大利职业法官的思维方式依然如故,大抵秉承“重大或高度怀疑”的心证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名存实亡。[110]
故“存疑有利被告”中的怀疑,并不是哲学意义上或怀疑论者(sceptique)的“怀疑”。皮浪(Pyrrho)所秉承的“不能肯定,亦不能坚信否定,应保持怀疑,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论在刑事司法中便是违背了法官的判决责任伦理。自由心证中的“怀疑”应是“方法的怀疑”(le doute méthodique)、“临时的怀疑”(le doute provisoire),法官通过理性与认知予以逐一排除,并达致“事实的真相”。可见,“要成为一位好法官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明智而有序地‘认知与把握’怀疑和自由心证方面”[11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