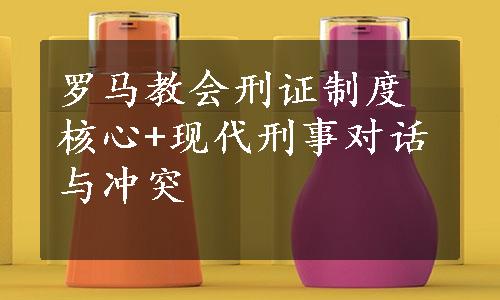
近代学者将罗马教会刑事证据制度[28]概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因为自13世纪起,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立法者相继在刑事证据立法[29]上确立了十分精确的证明力等级体系,详细规定了每种证据形式的可采性、不同种类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力以及证据间出现证明力冲突时的优先取舍问题。法定证据制度包括三项核心内容:其一,法定的证据形式;其二,法定的证明力规则;其三,也是较为特殊的,刑讯程序中酷刑的应用。
1.法定的证据形式
欧洲各国的立法明确规定了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形式,具体包括书证、证人证言、口供、推定、现场调查以及专家鉴定。
(1)书证。书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相对有限,仅适用于阴谋暴乱罪(complot contre l'État)、异端罪(hérésie)、伪造罪(faux)、暴力罪(usure)以及文书恐吓罪(menaces écrites)等。但在民事诉讼中,中世纪中后期的书证得到极大的发展,既包括公证文书(instrumenta publica),也包括私人文书(instrumenta privata),其证明力甚至凌驾于证人证言之上,即所谓的“文书优于证言”规则(lettres passent témoins)。
(2)证人证言。证人证言的适用须遵循如下规则:其一,证人应具有作证资格,即不在回避之列。回避事由主要包括证人的情感状况,如爱慕(l'affection)、恐惧(la crainte)、仇恨(l'inimitié capitale)等,证人的身体或名誉状况,如年衰(la faiblesse de l'âge)、精神衰弱(faiblesse de l'esprit)、失誉 (l'infamie)等,或者证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如个人利益 (intérêt personnel)、亲属关系 (la parenté)、穷困潦倒或乞食等。罗马法学家依《学说汇纂》总结了证人的作证资格:身份(Conditio)、性别(sexus)、年龄(aetas)、判断力(discretio)、声誉(fama)、财产(fortuna)、忠诚(fides)。其二,证人证言应具有“说服力”(concluante),严格适用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具体而论,证人须亲眼指控事实的发生,而不得转述或以听闻事实作证。证人在侦查、核实证据(les récolements)以及对质(les confrontations)过程中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其三,两人作证规则。即至少有两名证人对同一指控事实及情节提供证言,且在根本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在中世纪中后期,两人作证规则系铁律,如拉丁法谚所云,“仅有一人作证,即无证人作证”(testis unus, testis nullus)。这一规则甚至沿袭至今。其四,证人有作证义务。在智者法下,证人作证是公共职责(officium publicum),法官可以强制证人作证。日耳曼及中世纪一些国家的习惯法虽未规定此一义务,但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可能导致决斗。
(3)被告口供(l'aveu)。在罗马教会诉讼中,被告口供系极其重要的证据形式,长期被冠以“证据之王”的美誉。在侦查能力较为低下、取证技术较为粗糙的中世纪,这也是刑讯及酷刑制度设立并在后期盛行的基本动因。许多近现代的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批判中世纪刑事证据制度时时常以酷刑及口供为切入点,披露各种残暴的刑讯手段,以抨击旧制度刑事司法的黑暗和残忍。从现代人权法治的角度看,这样的批判自是成立,但回归历史背景,我们发现,仍有不少批判性的观点存有误解,系建立在对中世纪被告口供制度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之上。例如,在罗马教会诉讼中,原则上,被告的口供应自愿作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仅在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可能判处死刑)且存在证明力较强的不利证据指向被告时,法官方可裁定对其适用酷刑。即便在这一情况下,口供亦应在被告身体恢复后经重新讯问方可成为证据。
(4)推定(les présomptions)。推定即法官从一个已知事实得出另外一个未知事实的逻辑过程。18世纪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尤斯(Jousse)在论及刑事诉讼中的推定时写到,“如果就主要事实作证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身,而可证明其他事实,且这一事实与主要事实存有关联并可予以证明,则法官将依智识分析适用之。”[30]主流学说将推定分为法律推定(les présomptions de droit) 和事实推定(les présomptions de fait)。法律推定,顾名思义,即立法所明确设定的必然逻辑结果,通常具有不可反驳性(irréfragable)。例如,法律规定,一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也有一些法律推定是允许当事人提出相反事实予以反证,如立法在夜袭(attaque nocturne)案件中或者在暴力行窃(vol avec violences)案件中关于正当防卫(légitime défense)的推定。[31]事实推定又称为征凭推定(les présomptions des indices),指根据一定的事实(征凭)推断出某些结论,并据此判定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被告有罪与否的逻辑过程。在法定证据制度中,事实推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立法作了极其详尽的规定和分类。依证明力强弱,征凭(indice)可分为确实的征凭(indices manifestes)、强证明力的征凭和弱证明力的征凭。欧洲各国的立法、惯例及判例对三者作了详细的规定。例如在凶杀案件中,确实的征凭必须是两名证人看到被告手持利刃从发出尖叫或发现尸体的房间中逃出。已被证实的威胁则是强证明力的征凭。弱证明力的征凭主要指“那些与犯罪事实及犯罪情节无关,但涉及被告的个人状况,证明其可能实施被控之罪行的事实”。[32]立法者特别规定了如下数种弱证明力的征凭:被告实施犯罪可能获得利益、声名狼藉(sa mauvaise renommée)、装聋或假装健忘(l'affectation de surdité ou d'amnésie)。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即便不存在上述事实,但被告对于犯罪的调查显示出过分的热情,也可以作为弱证明力的征凭。缪亚·德·乌格朗(Muyart de Vouglans)甚至将“将被告相貌作为弱证明力征凭”,成为意大利实证法学家“犯罪人”(l'homme criminel)理论的先驱。
此外,立法者还通常以列表形式详尽地区分了可适用于所有犯罪的一般征凭(les indices communs)以及仅适用于某些犯罪的特别征凭(les indices particuliers),并据此确定证明力(la valeur probante)。例如《加洛林纳刑法典》便规定,下列征凭为一般征凭,可适用于所有犯罪:被告在诉讼外的供认(confession extrajudiciaire)、与被害人有深仇大恨、被告的威胁行为、逃逸、公众舆论(la voix publique)、与被害人的交易、被告犯罪的利益、被告隐匿、未揭发犯罪(la non-révélation du crime),甚至是共同犯罪案件中经证实的合意(l'approbation témoignée),等等。
(5)现场取证(la descente sur les lieux)和专家鉴定。现场取证主要用于查证法官记录中所载明的犯罪要件(le corps du délit)。专家鉴定则与现代的刑事鉴定制度并无太大差异。鉴定意见仅供法官参考,并无强制约束力。
2.证据的证明力
法定证据制度的核心特质便在于对各种证据形式的证明力作预先约定,以此约束法官在证据运用、事实认定及司法裁判中的专权。依证明力强弱,证据分为三类:确实的证据、半证据和不完整的证据。
(1)确实的证据(La preuve pleine ou manifeste)。在刑事审判中,法官仅可凭一份确实的证据便可作出有罪判决,甚至是死刑判决。依中世纪的立法、惯例及学说,确实的证据主要包括:
·无争议或者经公证的书证。(www.zuozong.com)
·两份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33]
·有确实征凭的事实推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6世纪前,理论界及实务界对推定的证明效力存有较大争议。但16世纪后,这种争议便不复存在,只要有确实的征凭,法官便可判处有罪判决,甚至是死刑判决。
·被告口供。被告口供是否为确实的证据,这在中世纪的理论界及实务界亦存有较大争议。尽管拉丁法谚云,“之于可判处死刑之人,不得听取其证言”(nemo auditur perire volens),但中世纪中后期的司法实践普遍将被告自愿的供述作为确实证据,法官可据此定罪甚至判处死刑。[34]学者们的意见也不统一。尤斯便认为,“在刑事诉讼所能获得的证据中,被告的供述是最具证明力且最为确定的。”布兰·杜·帕尔克(Poullain du Parc)则持反对观点,认为口供可能有悖于真相,“……尽管并未精神错乱,但一位心存悸意的无辜者在受到对其不利敕令的惊吓仍可能受到不利判决;恐惧可能使他承认了并未做过的犯罪行为。”因此,布兰·杜·帕尔克认为,口供需要强证明力的征凭(indicesgraves)或者证人证言等证据进行补强。[35]
(2)半证据(la preuve semi-pleine)。与确实的证据不同,法官不得仅凭半证据便作出死刑判决,而仅得作出刑讯判决(un jugement de question),或者更充分查明之判决(un jugement de plus amplement informé),或者作出低于所控刑罚的有罪判决。如果法官作出刑讯判决,则将对被告适用酷刑,依酷刑所得的供述作进一步的判决考量。半证据主要包括:单一证人的证言,或者强证明力的征凭。
(3)不完整的证据(La preuve imparfaite)。不完整的证据证明力最弱。法官不得依据此一类型的证据作出有罪判决,亦不得作出刑讯判决,仅可据此发布传唤令(un décret d'ajournement personnel)或者拘提令(un décret de prise de corps)。不完整的证据主要由弱证明力的征凭(les indices légers)构成。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时下仍有不少学者(既包括欧美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认为,半证据或不完整的证据可经过简单的算术叠加构成证明力层级较高的证据。[36]之所以存在这一误解,主要受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误导。1763年5月3日,伏尔泰在写给达米拉维尔(Damilaville)的信中描述了卡拉案件的判决情况。他写道,“图卢兹高等法院承认半证据、1/4证据和1/8证据,以至于8位传播流言者仅构成毫无依据的嘈杂声,但却成为一个(可定罪的)完全证据。”[37]但正如埃斯曼所言,“伏尔泰并不了解现行法,不完全了解法定证据制度在整个证明体系中的作用”,而这恰是“他攻击最猛烈的地方”。[38]事实上,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半证据并不意味着可推断出半个事实,同理,两个不肯定不能构成一个肯定,两个半证据也不能构成一个充分的证据。”[39]这是中世纪欧洲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通说,卡拉案件仅是极端的个案。
3.刑讯程序(la question)与酷刑(la torture)
酷刑产生于13世纪,系基督教会和世俗王权集权统治的重要手段。较之于神意裁判,这种取证方式更为合理、理性,故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40]适用,且持续时间极长,直至18世纪末期才逐渐消亡。中世纪中期欧洲的罗马法及教会法学者普遍认为,酷刑是一种正当的侦查手段,对于保障良好的刑事司法必不可少。[41]16世纪起,欧洲各国的刑事立法几乎均将酷刑作专章规定(如前所论及的《加洛林纳刑法典》和1670年法国的《刑事法令》,[42]以及1567年西班牙的《新法典编纂》等)。欧洲刑事法学者对酷刑的研究更是达到顶峰。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如13世纪的佚名作品《论酷刑》(Tractatus de tormentis,大约写于1263—1286年),13世纪末阿尔伯特·甘迪努斯(Albert Gandinus)的《论犯罪》(Tractatus de maleficiis),1484年海因里希·克雷默和耶科布(Heinrich Kraemer and Sprenger)所撰写的《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s),1580年冉·布丹(Jean Bodin)的《巫师的魔鬼附身狂想》(Démonomanie des sorciers),1588年意大利罗马的律师法里纳修斯(Farinaccius)所撰写的《刑事理论与实务》(Praxis et theorica criminalis),等等。此外,波伦亚学派在评注《狄奥多西法典》和《学说汇纂》时亦对罗马法中的酷刑理念作了较具深度的阐释。从根本而论,酷刑系中世纪刑事法学者最热衷的学术命题。
不同欧陆国家对刑讯及酷刑的适用细则规定有所不同,但机理基本类似。法国1670年《刑事法令》第19编便对刑讯及酷刑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可作为欧陆国家的典型范本加以研判。1670年《刑事法令》将“刑讯”分为两种:预备刑讯(la question préparatoire)和预先刑讯(la question préalable)。尽管名称类似,但两种“刑讯”程序的功能和目的完全不同:预备刑讯是在最终判决作出前,法官为获得被告口供、掌握更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被告有罪而下令适用的一种预审措施;而预先刑讯则是对已经判处死刑的被告所采取的预审措施,旨在“揭露被告的共犯”。前者由中间裁决决定,后者则由终局判决确定。两种刑讯程序本质上均属预审手段,但因方式严酷而纳入法令的刑罚编。而本文所论及的仅为预备刑讯。
1670年《刑事法令》第19编第1条规定了适用预备刑讯程序的三大要件:①被指控的罪名应判处死刑;②犯罪事实确实存在;③存在不利于被告的重要证据。司法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第三个要件,一如前述,法官仅在掌握对被告不利的半证据下,方可启动刑讯程序并对被告科以酷刑。此一半证据可以是经两名证人证实的被告庭外供认(la confession extrajudiciaire),也可以是一份证人证言且辅以征凭,尤其是证明被告声名狼藉的征凭,也可以是所有确实的征凭。“这些征凭与主要事实具有紧密直接的联系(……):例如,在盗窃案件中,如果发现被告持有被盗财物,或者发现被告在被盗地方拿走被盗物品(……),或者被告在尸体附近被抓且手中握剑,试图逃逸……”[43]如果法官未遵守前述条件而非法对被告适用酷刑,则应承担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被告也可对适用预备刑讯的中间裁决提起上诉。上诉一旦获得批准,则被告便不再交由一审法院的法官处置(巴黎刑事法院除外),上诉法院是唯一有权进行刑讯的法院。立法者希望通过这些程序机制以限制刑讯案件的数量。
预备刑讯存在多种形式,各地刑事法庭的做法有所不同。例如巴黎采用灌水(l'eau)或者夹棍(brodequins);在雷恩,受刑者应佩戴在火中烤过数次的脚镣,或者在被告脚上负重并将其吊起等;法兰德斯则同样采用灌水;意大利则采用悬吊(suspension)。15世纪的学者伊波利特·德·玛尔斯尔(Hippolyte de Marsiliis)便曾专门研究了欧洲的十四种酷刑模式。在预备刑讯期间,书记官应认真记录酷刑的进程及强度。如果法官在适用酷刑时超出必要限度而致使受刑人死亡的,则应承担责任:如果存在主观的欺诈,则法官将被科处死刑;相反,如果并非有意为之,则法官应依过错的严重程度接受惩罚。正如阿尔贝图斯·德·甘地纳所言,此举的目的在于保障被告安然无恙以便执行随后的免诉或者死刑判决。依惯例,预备刑讯还必须有医师参与。当然,审慎义务(devoirs de conscience)及怜悯之心(compassion)促使法官在刑讯中保持节制,这比“可能追究法官责任”更为有效:“刑讯中的节制或粗暴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考虑、裁量以及审慎。但是好的法官往往对受刑人怀有怜悯之心,并应充分考虑被告的年衰、稚嫩及精力。”[44]
刑讯结束后,被告将置于火旁的一个床铺上。1670年《刑事法令》规定,法官必须立即针对被告在刑讯中所承认或者否认的犯罪事实进行新一轮的讯问。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则在刑讯后给被告预留了一个回答新一轮讯问的期限,通常为24小时,这是因为,如果被告立即承认其在刑讯中所作的口供,则该行为被推定为因畏惧酷刑或者受疼痛的影响而为之。如果被告在刑讯中承认了被指控之犯罪,并在随后的讯问中确认了这一口供,则该口供补强了此前所收集的各种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法官可据此作出有罪判决;如果被告在刑讯后否认了之前的口供,并声称系由酷刑的暴力迫使其招供,则此一口供“不能作为证据”。除流刑外,被告不得科处其他任何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官在刑讯中所获得的口供十分精确和详细,以至于可判定“被告如若并未参与犯罪,绝计不可能了解得如此确切”,则法官可以宣判被告有罪,而无需考虑被告翻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依1670年《刑事法令》第19编第12条之规定,“即使出现新的证据,也不能对被告就同一事实适用两次刑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