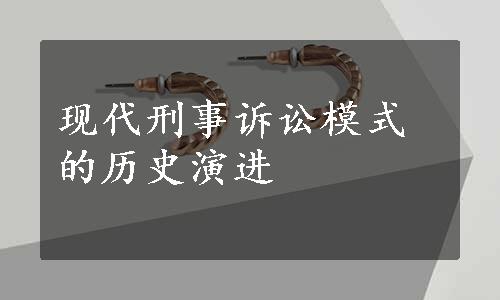
自19世纪起,“inqusitoire”(职权主义)开始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并与“accusatoire”(当事人主义)一起在不同时期学者的学术作品中出现,其含义也呈相同的演进史。19世纪的学者更多立足《重罪法典》的背景、制度与技术,以此审视1670年《刑事法令》以降“职权主义”程序运行的基本轨迹,而20世纪的学者则更多立足新《刑事诉讼法典》,在横向(比较法)与纵向(法史)的双重视角下剖析“职权主义”运行的内在规律及优弊所在,并有意识地构建更具“透明”“对抗”及“人权保障”色彩的新职权主义。
1.奥尔特朗与“次生效力”(effets secondaires)标准
一如前述,奥尔特朗在1839年所出版的《比较刑事立法教程》中首次对“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进行了区分。奥尔特朗认为,“当事人主义”系“双方当事人将争议送至法官前,由其居中作出判决”,“原告负责指控犯罪,并承担证明责任”,“受到犯罪指控的被告可自行进行辩护,驳斥原告所提出的各项指控证据”,“法官依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判”;[48]而“职权主义”则是“一名法官负责侦查”,“在侦查程序中讯问被告”,或者“由司法职权机构负责侦破犯罪、起诉、预审、收集证据、讯问被告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询问证人,并作出判决”。[49]据此,奥尔特朗认为,之于“当事人主义”诉讼,“原告和被告在程序中处于平等地位,他们围绕证据进行辩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对被告进行讯问并非从其口中获得对其不利的证据,而是允许其进行自我辩护。庭审和程序均为公开”;而之于“职权主义”诉讼,“被告的地位不如侦查人员(即预审法官)”,对“证据缺乏对席的庭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他的辩解,而是令其协助调查以获得对其不利的证据”,“程序是秘密的,侦查借由秘密的手段以获得最终的成果”。[50]奥尔特朗特别强调,前述要素并非“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专属特征,而仅是程序所产生的“次生效力”,即在程序“效力结果”层面进行区分,而非界定。[51]
2.密特麦尔与“混合形式诉讼”(les formes mixtes de procédure)
与同时代的刑法学者相比,密特麦尔的观点较为独特,他反对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截然划分。“我们给当事人诉讼赋予太多专属的内容……其中有些基本的特征源于基本的素材、适用于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截然对立,其后果便是将一些职权主义不具有的特质强加于当事人主义。”[52]密特麦尔驳斥了一些他认为极为武断的观点,例如“仅当事人主义诉讼方以证据为基础作出有罪判决”,“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特征是言词庭审”,“私人控告仅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以及“当事人主义诉讼和职权主义诉讼究竟何种程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当事人主义诉讼仅适用于民主国家,而职权主义诉讼则适用于专制国家”等。[53]密特麦尔认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并无优劣之分,“每条路径均可达到目的,仅是同一思想有不同载体罢了。”密特麦尔进一步指出,“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同当事人之间的自然诉求均逐渐演变为‘控告’和‘辩护’这两个程序的基本要素,侦查的目的便是探求绝对的真实。双方当事人各自抛出支持己方的、可能影响裁判天平的事实和论据,这才是诉讼程序中真正有用的要素”,“私人控告不仅仅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均以私人控告为基础,只不过功能有所差别罢了”,[54]不应据此将当事人主义诉讼和职权主义诉讼截然分开。
密特麦尔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在制度运作上有所差异,那可能是,“从本质上,当事人主义诉讼系对立当事人之间真正的战斗,各方当事人均提出己方的论断以揭示真相,确保在诉讼中获胜,而职权主义诉讼的首要且根本目的是通过各种法律所授权的侦查手段、由国家所任命的法官(其职权由国家机构明文规定)负责收集与犯罪相关的证据”。[55]在密特麦尔看来,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发现犯罪真相的方式,“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核心是在终审法官前进行完全的对抗,因为原告和被告将穷尽所有影响定罪的手段以掌控诉讼的结果……在此一诉讼中,只有人民或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可以成为法官……对证据的运用完全在法官面前进行,程序公开进行,庭审奉行言词原则,因为书面的指令与程序目的相违背,且没有必要,法官作出的判决不能上诉,并参与整个对抗过程”[56]。密特麦尔最后批判了意大利学者卡米尼亚尼(Carmignani)的观点,后者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包含两种完全不同性质、无法兼容的要素,两者融合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密特麦尔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交融不仅可能且必要”,从而构建了独特的“混合形式诉讼”学说。[57]
3.弗斯坦·埃利和“阶段型的混合式诉讼”
从履历上看,弗斯坦·埃利不仅是著名的程序法学者,更是《重罪法典》的直接践行者(担任法官数十年),故其学说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主要建立在对《重罪法典》所构建之刑事程序的评价上。在弗斯坦·埃利看来,“刑事诉讼总体而言包括两种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前者以控告为原则,后者以侦查为原则……所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必然归结于其中的一种,仅是或多或少,以及带有某些修改。”[58]但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区分并非仅以历史为线索,更不可能作“截然分割”。弗斯坦·埃利据此提出了“阶段型的混合式诉讼”理论,即在理想的刑事诉讼中,审前阶段应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国家公权力占据垄断地位,审判阶段则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由各方当事人主导诉讼进程。而此一理论的基本模型便是《重罪法典》所构建的刑事诉讼程序。弗斯坦·埃利反对给“职权主义”一个明确的界认,认为这是历史、语义或定义发展的结果,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存在对立,但可进行“分阶段”的融合。
弗斯坦·埃利所构建的“混合程序”理论在学界和实务界极具影响力,为当时《重罪法典》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导向,也使法国的刑事诉讼框架成为欧陆各国争相效仿的楷模。但也有不少学者持批判态度,比较著名的如法史学家杜·布瓦(Du Boys)。在1874年所出版的代表作《法国刑法史》第2卷(共6卷)中,杜·布瓦便指出,“言词、自由辩论以及程序公开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精髓所在”,而“职权主义则奉行书面、秘密原则”,两种程序均有其固有特征,南辕北辙,不可能融合。[59]
4.埃斯曼和“不同程序技术下的混合式诉讼”(www.zuozong.com)
埃斯曼秉承弗斯坦·埃利的论述思路,但从诉讼法史的角度作了修正和拓展,逻辑更为清晰明了,史料运用也更为详尽扎实。埃斯曼认为:“刑事诉讼是特定双方的争讼,没必要专门创设某种特别的程序形式。”[60]因此,他并不主张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上升到诉讼模型的对立,而仅是“某些程序特征的总括”。例如在介绍封建时期“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时,埃斯曼便指出,“程序是公开、言词、形式化的”,“通常情况下庭审完全公开”,“当事人仅能由代理人代表出庭”。[61]但埃斯曼进一步说明,这并不是当事人主义自诞生后便固有的特征,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埃斯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几乎均是“混合的”(la procédure mixte),所不同的是“职权主义”的成分多一些,或者“当事人主义”成分多一些。如《重罪法典》便是“妥协和交易的产物”[62],“一方面系1670年《刑事法令》的传统(职权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制宪会议所宣称的原则以及过渡时期法律(当事人主义)”[63]。受埃斯曼理论的影响,1901年出版的《法国学说汇纂》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进行了界定:所谓“当事人主义”,指“由受害人向犯罪行为指控者提起控告”,“法官在被指控者同阶层的人群中选拔,并被接受为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控告者直接传唤被指控者在法官处接受裁判”,“庭审公开、言词、对抗”,未有“书面的程序”;“职权主义”诉讼则为“设立常设的法官负责书面、秘密的侦查”,“公权力机构通过其代理人负责预审程序,以为刑罚做准备,其所任命的官员系常设的公职”。[64]
5.20世纪的主流学者与“新职权主义”
19世纪,以《拿破仑法典》颁布为节点,欧陆学界掀起了文本解释的热潮,注释法学派(l'École de l'Exégèse)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位置。这可以理解为何此前的代表性学者更多围绕《重罪法典》予以阐释。19世纪末,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使学界从对《拿破仑法典》的盲目崇拜中脱离出来,不少学者开始寻求走出注释法学派藩篱的路径,以比较法为代表的新兴法学理论呈井喷式发展。[65]故20世纪的欧陆学者不仅从纵向(法史)、更主要从横向(比较法)来审视并剖析“职权主义”运行的内在规律及优弊所在,并有意识地构建更具“透明”“对抗”及“人权保障”色彩的“新职权主义”。
总结主流学者及主流教材的观点,[66]我们可将“新职权主义”的核心特质描述如下:
(1)价值目标系社会利益优先型或者国家利益优先型,追求实质真实。
(2)机构设置集权化,裁判者通常为专业法官,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和行政性;侦查权、公诉权和裁判权由国家垄断,国家或社会利益由检察机关代表。
(3)诉讼阶段化,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系刑事诉讼的“两个核心”,前者更偏向传统的职权主义,如侦查秘密、较高羁押率、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权利相对受限,后者则完全透明、公开、对抗。
(4)证明模式奉行“自由心证”,法官具有一定的庭外调查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职权主义”的生成,并非仅仅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一些优点,而更多系随着近代人权保护理念的兴起而作出的调整。之于后者,“当事人主义”亦作出相同的改革(如上诉程序的设立)。故新时期下“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趋同性,既源自于两者间的相互借鉴和补充,更主要源自于基本权利及正当程序理念的兴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